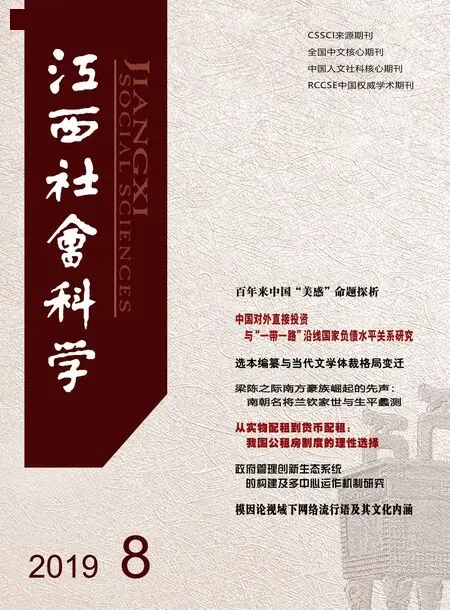钱锺书的“文心”及其历史意识
袁广涛
钱锺书屡次标举的“文心”概念代表其学术思想本质的两大特征:形式主义和心理学维度。这两个特征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批评实践和互通的文化观等方面。具体而言,钱锺书认为文学史是精神心理影响下文学形式的演化过程,与现实社会历史无关,他的批评实践多用语义分析法,重视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并习惯借助心理学概念,发掘普遍心理和事理,但追求普遍性和固守文本是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摒弃,而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因其立足于各类文本共有的文学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样忽视了历史。所以,虽然史学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的畛域之一,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具有反历史主义的维度。
钱锺书在《论复古》中主张一种涵盖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观念”[1](P330),强调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张力结构和互动关系,这种文学史思想体现出辩证的历史意识。除文学史外,他对历史和史学也有精妙阐发,对东西方的史学传统颇多洞见,并且致力于沟通中西,贯通古今,打通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本文通过总结钱锺书的文学史观、批评方法以及其打通的学术精神,试图说明钱锺书学术思想可由代表形式审美与心理学的“文心”一词所概括。但是,虽然钱锺书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辨析精微,“文心”也指明其学术思想和实践的基本立场是文学本体和普遍主义,这也导致他历史意识有局限的一面。
一、形式与心理主导的文学史观
钱锺书在《谈艺录》开篇即谓“诗分唐宋”,继而言明唐诗与宋诗相区别的依据是格调神韵等诗歌内在审美特征[2](P1-5),而非社会历史中的朝代分野,并且声称文学史是语言或题材的以故为新、使熟者生的过程[2](P29-30),这一文学演变中的陌生化原则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其核心原则是强调文学特殊性的文学本体论,而钱锺书认为文学自有其演变规律和内在价值,正是这种文学本体意识的表现。但他并没有固守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比如,在《旁观者》一文中他认为文学、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的形态都由心理状态影响和决定[1](P281-282),看似突破了上述形式主义文学史观的封闭性,但因为心理状态自在、自为,只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不为社会现实所决定,于是,文学史就脱离了社会历史。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他写道:“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其臆必目论,固置不言,而同时同地,往往有风格绝然不同之文学,使造因止于时地而已,则将何以解此歧出耶?”[1](P100)意思是不能“因世求文”,拿社会等非文学因素来解释文学。这是钱锺书对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学观的否定,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
钱锺书的这种基于文学本体与精神心理的文学史观应该有艾·阿·瑞恰兹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西文系读书时,瑞恰兹恰好在该系讲学(1929—1931年),瑞恰兹的语义学分析方法立足于文学本体论,对钱锺书的文学本体观念应有所影响;同时,瑞恰兹与其他新批评主义者又不同,他试图突破形式主义,把心理学范畴和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受其影响,钱锺书曾发表过《人为什么要穿衣》《美的生理学》等关于心理学的文章,并在《美的生理学》中对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极为推重,认为它借助心理学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钱锺书保持了这种对心理学的兴趣,他所征引的浩瀚文献中屡屡出现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著作,分析文本时也习惯借用心理学的概念。而从更宏观的文化背景来看,这种文学观也代表了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19世纪,源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被引入人文学科并泛滥一时,人文学者从不同立场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新批评作为现代主义的批评理论就是这场人文运动的一部分,其意识形态符合人文主义传承的内在精神,例如,在新批评的代表理论作品《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就反对把进化论用于文学研究[3](P307),而这一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传到了中国。除人文主义之外,主观意识与精神的概念也被用来反对实证方法在人文领域的滥用,钱锺书对狄尔泰、克罗齐、柯林伍德等多有征引,他拒斥实证主义,认为文学及其他文化现象由精神心理而非社会形式和物质环境条件决定,实质上反映了心理学思潮与上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强调格调审美也是中国传统诗论的显著特征,正如余婉卉在《〈学衡〉中的古希腊——以吴宓〈希腊文学史〉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吴宓所著《希腊文学史》的精神上属于《文心雕龙》所代表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体现为对文学作品的共时性鉴赏品评,背后是‘文章流别’的观念”[4],而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所采用的著作体例恰是中国传统诗话的札记体。这种体裁便于摘录和记载心得,但在连续性和整体性上有所缺失。余婉卉还引用了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整体历史观缺乏的观点来批评吴宓对希腊文学史的书写。但是,与吴宓不同,钱锺书却曾经主张宏观的历史视野,例如,他在《论复古》中提到过,有历史观念的人不仅要知道“文学的进化”,而且要明白过去与当下的辩证关系,“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1](P330)。《论复古》是钱锺书为批评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主张的文学进化论而作。文学进化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文学领域,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肯定“进化”“演变”“革命”,否定“落后”“陈腐”的旧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核心观念,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界。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认为正确的历史观念能够帮助我们辩证看待新与旧的关系,能让我们看到现代与传统是连续统一的整体。钱锺书的“历史观念”类似英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倡导的“历史的意识”,即:“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5](P2)但艾略特并没有把文学传统看作历时性的发展过程,而认为自荷马以来的所有的欧洲文学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存在。[5](P3)除了这一文学传统观之外,艾略特也以他的“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等诗学理论为现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主张文本中心论的英美新批评奠定了基础。综合来看,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其实抛弃了历史、社会和作家个人等文学外部机制,是在文学内部建构成的封闭系统。同理,钱锺书主张的文学传统观同样也是不同时代文本所构成的封闭系统,摒除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状况等非文学因素。
总之,钱锺书认为文学史是人类精神心理的表现形式,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发展,有社会历史现实无法涵括的维度,他同时强调文学在形式审美上的演变,认为这是机械的因果律难以反映出来的,这种文学史观对20世纪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无疑具有宝贵的补充和反拨价值;但另一方面,如刘锋杰在辨析钱锺书“史诗”概念时所指出的,“在文学史上,文学的审美性与其他社会特性是交流、对话与融合的。有意或无意地孤立审美论,就很难把握文学史的全貌”[6]。在此,我们也可以补充说,即使把审美论与超越社会历史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我们仍然无法全面认识文学史,而钱锺书所标举的“历史观念”实际上摆脱了历史的社会特征,反映出的恰是其整体历史意识的匮乏。
二、追求普遍性的批评实践
钱锺书主张避免“因世求文”,既指对文学史的考察,又指文学作品的评鉴:在面对具体文本时,强调细读和直接感受,发掘文本的内在价值,所谓“读者不必于书外别求宣泄嗜欲情感之具焉”[1](P99)。例如,解读《锦瑟》一诗时,他首先进行互文比较,认为首联中的锦瑟暗喻诗歌,颔联和颈联借物象揭示创作方法和诗歌风格,尾联引出乐极生悲的典型心理[2](P434-438)。这说明他采取的是文本细读法,通过分析意象、修辞以及诗歌结构,探究文本蕴含的普遍心理,反驳了历史上对《锦瑟》的几种主要解读,包括涉及个人际遇的悼亡说和仕途失意说以及反映唐代政治斗争的影射说。这种文学本体意识在钱锺书对杜甫的评论上尤为醒目。因为其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意义,杜甫的诗被认为具有史料价值,有“诗史”之誉。但据胡晓明统计,《谈艺录》《管锥编》这两部作品中所引述、考析的杜甫诗句多达两百余条,无一涉及杜甫诗载录的重大史实和杜甫的切身感受,着眼点皆在杜诗的风格、修辞、渊源以及心理学方面的认知等[7]。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曾经直接批评“诗史”观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法,认为文艺批评不等于也不能依赖于历史考据[8](P3),而近来周景耀梳理了钱锺书在该书中撰写的80余位诗人的小传,发现“小传的历史气息极稀薄,作者身世经历的介绍付之阙如,亦极少涉及诗人所处之时代状况”,属于“‘过滤’了历史的写法”。[9]
这种文学本体意识不仅体现在钱锺书的诗论中,而且体现在其对历史和哲学典籍的点评中。《管锥编》选评的两部史籍《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皆以叙事艺术著称。在《左传》的第一篇札记中,钱锺书就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文学性,把历史叙事与小说等文学叙事等同:“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0](P166)《管锥编》中论《左传》和《史记》的札记有125则,其中逾半数涉及文学,如《隐公元年》论“待熟”之喻,《庄公六年》揭示以空间喻时间的现象,《闵公二年》论语言风格,《昭公五年》引论章法句法,《史记会注考证》中《周本纪》指出求美人笑是中西文学共有题材,《项羽本纪》论人物刻画,《淮阴侯列传》归纳小说笔法,等等;而哲学方面,论《周易正义》的27篇中,19篇与文学有关,《焦氏易林》更是被推崇和《诗经》一样,是四言诗的典范,“《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10](P536),并从意象、修辞等方面详尽论证了《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另如对于佛典的广泛涉猎,不究佛理而往往专注于文辞。在散文《作者五人》中钱锺书品评五位哲学家的文章风格,并表达了想写一部讲哲学家的文学史的愿望。
除文学本体意识之外,钱锺书的批评实践往往以人的普遍心理经验为鹄的,即他在《谈艺录》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2](P1),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2](P286)。譬如在论杜甫诗“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时,钱锺书认为“望”字通“忘”,把该句解释为“丧精亡魂”之际“衷曲惶乱”的心状;与之相较,史学家陈寅恪通过考证唐代宫阙方位,认为“望”是指杜甫“回望”皇宫,“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7],也就是说,陈寅恪把杜甫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而钱锺书则捻出当此关头人所共有的普遍心理。探究普遍心理,必然以普遍的人性观和艺术的普遍价值为前提,这就可能压抑作家创作过程必然具有的偶然性和异质性元素。早在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赫尔德从三个方面否定欧洲从希腊文化到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思维:否定艺术和文化的普遍价值,否定普遍的人性观,否定人类的共同理想。赫尔德强调文化现象产生条件的特殊性,认为首先要知晓文化的社会语境,才能了解此文化:“一向在北海波涛中经受风浪打击的人,能够充分理解古老的北方吟唱诗人的歌谣,这是那些从未见过北方水手搏击风浪的人们所绝对做不到的。”[11](P40-45)时代不同,境遇各异,如果强行以普遍心理或人性作解释,难免会有误读或笼统之嫌。例如,《卫风·氓》写主人公和氓自由恋爱并结合,但终为氓所弃,归家后“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钱锺书把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拿来比较,认为主人公“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逢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10](P93-94)就文本内部而言,这确是诛心之论。但近来有论者考证,在《诗经》时代,周礼对于平民的婚姻还未有深入干预[12],还有人从地域出发,认为郑卫是殷商故地,承袭了自由开放的商族婚恋习俗[13],由此看来,钱锺书把兄弟之笑解释为“初不自重,卒被人轻”的讥笑,似乎值得商榷。
探求普遍的文理心理,钱锺书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阐释循环”。关于“阐释循环”,他在《管锥编》中有一个总结性的定义: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10](P171)
首先,如张隆溪所说的,钱锺书把西方阐释学传统和中国古代典籍相呼应,强调字句和全篇之间的“语言循环”,兼及作者的“宗尚”,时代之“流行”。在“语言循环”的基础之上,钱锺书的“阐释循环”进一步涉及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把文本与作者的时代之背景联系起来[14],但这里需要看到的是,钱锺书所指仍为“立言”“文风”“修辞”“题材”,于“作者”而言,强调的是作者所推崇、追求的风格,于“时代”而言,强调的是时代流行的审美趣味,所以,此处的作者、时代仍然是钱锺书形式主义文学史中所指的作者和时代,是缺少社会历史语境的作者和时代。其次,季进指出,钱锺书阐释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人类心理的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审美的共通的感悟,并援引了《管锥编》中的具体案例:钱锺书解读“萧萧马鸣”时,引出“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并点评历史上多位诗人对此意境的摹写,然后联想到英国诗人雪莱,指出这是中西诗歌共有的意境,进而说明其心理基础,并归纳出“有见无物”之理,最后据此返回文本,解读中西多位诗人的作品。[15](P82-84)但在这个交互往复的过程中,将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诗人放在同一个典型的审美语境中,或被标上普遍的心理特征,罔顾其具体社会语境,这种阐释策略具有显著的反历史主义特征。西方阐释学萌发于古典时期对荷马史诗、尤其宗教改革时期对《圣经》的阐释活动,一开始仅关注语言层面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到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提出阐释循环原则,并将之扩展到心理层面,主张文本即是作者心理表现和生命片段,但要理解文本和作者心理,须将之还原到作者的生活语境中。之后的历史学派明确地把阐释学循环的部分-整体关系转化成了历史事件与其所属生活的关系,狄尔泰更是把阐释循环看作“历史意识的普遍手段”[16](P330)。钱锺书虽然屡次征引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阐释论,但他的阐释循环论消解了他们的历史维度,否认了文本的历史性。20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历史意识上更进一步,通过“先见”“前理解”等概念说明阐释主体及阐释活动的历史性,主张通过“视域融合”,构成一种效果历史意识。钱锺书也曾提及现代阐释学的这些概念,但是,就像李清良指出的,钱锺书所强调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而不是伽达默尔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17],钱锺书阐释循环所建构的是一个封闭的共时性互文系统,既舍弃了古典阐释学的历史主义,没有回到作品的历史语境,也不具有现代阐释学的历史意识,没有涉及阐释者历史语境。
三、以文学为中心的“打通”观
李清良总结钱锺书阐释循环的基本精神在于打破界限、通观一体,而界之能破,一是因为文本本属一体,皆由语言构成,再者因为人类文化都有“心同理同”的一面[17],在指出钱锺书阐释论对其中西互通,古今贯通,学科打通的治学理路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同时,他还指出钱锺书打通精神的两大支点:文学性与普遍的精神心理。也就是说,要打通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钱锺书借助的是各学科共有的文学性与共通的心理表征。钱锺书认为经史子集都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2](P266),和小说、戏曲一样,“于心性之体会,致曲钩幽,谈言微中”[10](P227),这就拓展了六经皆史的传统文化观,认为六经皆史不仅是因为它们记录史实,汇编史料,更是因为它们承载了时代的精神心理,对钱锺书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心理状态比历史事件更能呈现历史本相,“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穷元佑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2](P266)。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钱锺书指出,一切文化活动都基于人类的心理意识,“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而心理意识又具有审美性和文学性,“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alsob)、诗意的认识”。[1](P131)既然人的心理是诗意的,那么,一切文化活动和语言建构都有文学性的一面。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申发刘勰“综观一切载籍以为‘文’”的观点:“文者非一整个事物,乃事物之一方面。同一书也,史家则考其述作之真赝,哲人则辨其议论之是非,谈艺者则定其文章之美恶。”[1](P102)任何文字篇什都可以有文学特质,即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文学性,都可读作文艺作品,这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学概念。所以其独六经皆史,更可谓六经皆诗:任何文化经典都可成为文学批评和鉴赏的对象,而这正是前文指出的钱锺书批评实践的显著特点,说明了钱锺书学术研究的中心场域仍然是文学,而他的基本立场是一个“谈艺者”。以文史关系为例,他在23岁时发表的《旁观者》中说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野蛮的事实和史家的事实[1](P282)。前者即历史事件或现象,后者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海登·怀特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一书中提出历史话语的三要素:素材、理念和叙述结构,素材即“野蛮的事实”,被史学家以一定的理念理解,塑造成一个故事的形式,并且赋予其一个结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18](P171),即通过叙事赋予历史事件关系和意义,所以,历史文本必然具有一个深层的“诗性”结构。这样,后现代史学的核心特征就成了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的剥离,客观性和真实性被虚构和审美所取代,不再是考证历史著述的依据。也就是说,早期的钱锺书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历史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与近半个世纪后的新历史主义主张的“历史的文学性”不期而同。20世纪40年代的《谈艺录》中有“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2](P38)的论断,20世纪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反复申言历史话语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但是,新历史主义还有主张“文学的历史性”的另一面,认为文学是渗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社会实践。而钱锺书并没有如新批评主义那般消解文史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他那里,文史之间也没有实现双向平等的“互通”,因为于历史方面,他看重的是历史叙事而非历史事实,于文学方面,他轻视文学的历史关联和政治意义,可以说,他是站在文学立场上来看待文史关系的。
从学术渊源看,除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之外,钱锺书的打通精神也有由吴宓主导规划、清华大学实行的博雅教育的影响[19]。无独有偶,吴宓的另一弟子张荫麟也以“通人”闻名。但正如张荫麟指出的打通立足于史学[20],六经皆诗代表了钱锺书的文学本体立场,文学性是他在面对文化典籍时的主要旨归。六经皆诗的前提是六经皆史,人文学科呈现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而人的精神心理本质上是诗意的,所以,各类文化文本皆可作文学观。钱锺书对“六经皆史”的深化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开阔视野与辩证思维,其很多洞见沟通中西,承接古今,甚至预示了学术发展走向比如后结构主义对历史话语的解构;但另一方面,六经皆诗意味着一种“泛美学主义”,正如刘康对诺思洛普·弗莱诗学话语的批评:“(弗莱的)文学的原型乃是人类意识活动(当然主要是情感与想象)最为本真的形式和结构。依此推论,人类意识活动本身便演绎成了审美活动。”[21]可以说,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背后的是对社会历史的忽视。
四、结语
钱锺书的学术视野囊括中西古今,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辨析精微,表现出辩证的历史意识,但纵观其学术全貌,他的主要着眼点仍是《谈艺录》中所标举的“文心诗眼”。但正如胡晓明所说的,“这个‘心’‘眼’,乃在心理、智慧、情感类型的审美情趣”[7],也就是说,来自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心”一词,除文学审美性质之外,被钱锺书赋予了心理学的内涵,而刘长华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也认为钱锺书诗学中的“心”融会贯通了中国“心学”和西方的心理学[22]。钱锺书曾经把美国学者马科斯·伊斯特曼一本专著的标题“The Literary Mind”直接翻译为《文心》,而这部书探讨的就是诗歌的心理学解读法。所以,“文心”这一概念恰好代表了钱锺书学术思想的本质,一方面是共通的文学审美;另一方面是普遍的人类心理,代表着钱锺书在审美和人性两个方面对文学研究的拓展。分而言之,“文心”之精神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念上,文学史是时代精神心理影响下文学形式演化的历史,但也就变成了与现实社会历史无关的封闭的“历史”;体现在批评实践上面,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等作品中,多采取语义分析法,在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循环往复,并时常借助心理学概念,发掘普遍心理和事理,揭示古今中外在观念与情感上的契合,寻找他们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但他对普遍性的追求、文学本体意识及其采用的阐释原则都忽略了文本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下,以中国传统学术智慧响应西学潮流,促成不同学科的相互关照,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后结构主义对史学话语的解构,但在“文心”精神的统领之下,立足点仍是文化文本共有的文学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样摆脱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定。总的来说,虽然史学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的重要畛域,他也未曾像后现代史学家那般激进地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他的文学史思想脱离了社会历史,其批评实践和学术精神呈现出普遍主义的特征,其“文心”精神的背后缺少了宏观整体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