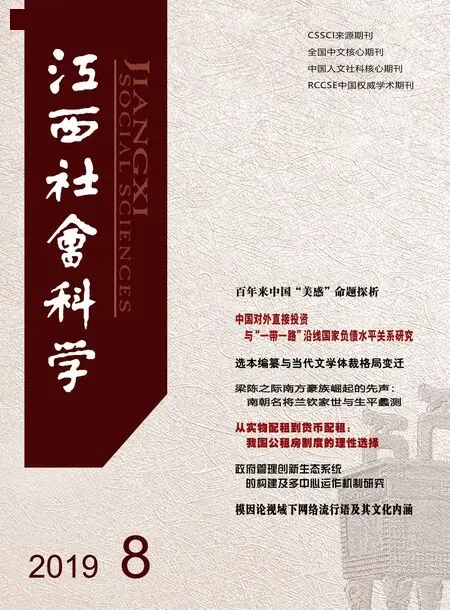选本编纂与当代文学体裁格局变迁
徐 勇
选本类型在选本格局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某一体裁在当时社会语境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就当代文学而言,诗歌选本和小说选本之间地位的演变,所涉及的主要有以下命题:“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选本的功能变迁,及其背后文学主体构成上的变化。选本编纂以“选”的方式自觉运用文学体裁或类型分类原则,既强化了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评价与看法。
虽然说文学在体裁上可以分为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几大类,但这些体裁在选本编纂的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并不总是对等。也就是说,选本类型在选本格局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某一体裁在当时社会语境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诗歌是核心文体,因而诗歌选本或总集最多,其次是散文。小说文体的发达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因而小说选本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版中所占的比重和数量整体上也最多。诗歌作为传统优势文体,虽然在近现代以来地位趋降,但因其情绪表达的便捷亦能在特定年代大放异彩,同时又因诗歌的形制偏短易于编选选集,常有一卷在手应有尽有的感觉,诗歌选本也是20世纪文学选本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构成部分。相比之下,散文则要逊色得多,而戏剧选本则又更少。
一
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小说和诗歌是一种彼此呼应和互补共生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可以借用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加以分析。如果说启蒙与救亡确实构成了20世纪中国互相补充和彼此竞争的两大核心主题的话,这样一种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文学各文类之间的变动关系。启蒙建构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救亡指向的则是广大民众。它们的侧重点不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决定了启蒙偏向于以故事的讲述说服他人,而救亡则倾向于以情绪的呼应动员民众。这样一种错位恰好对应了小说与诗歌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当启蒙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小说就可能成为主导文体,而当救亡成为主潮时,诗歌则又可能一跃而成为核心文体。这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得到印证。“五四”前后,小说是最为重要的文体,而到“抗日战争”时期,诗歌或通俗韵文文体(比如民间戏曲)则成为当时的主潮。20世纪50—70年代,最为活跃的文体,主要是新民歌、政治抒情诗以及各种民间戏曲(通常的文学史,多从小说文体入手叙述,对此类作品多有忽略)。20世纪80年代以迄,当启蒙再一次被重提的时候,小说重又占据了文坛主流的地位。
这样一种矛盾关系,还与当代中国另一个二元对立命题息息相关。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命题。毛泽东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命题,其实是凸显了普及的优先地位。这样一种对普及的推崇,某种程度上是与毛泽东设想中的文学动员大众的功能彼此对应。而这,也就提出了对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文体的改造问题。这首先是一种创作方式的变革。在这之前,文学创作(包括文学阅读)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20世纪50—70年代,则开始探索思考集体创作的可能。这样一种集体创作在话剧等戏剧文体中得到尝试,也最为成功。小说方面也尝试集体创作方式的可能,所谓“三结合”或写作组也主要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在这当中,确实诞生了如《红岩》之类的成功之作,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即使如此,小说也面临着阅读接受上的非大众化倾向。小说的阅读是一种个体行为,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这对于当时的广大民众而言,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不像诗歌,可以通过朗读或歌唱,成为一种阅读接受上的大众文体。从这点来看,小说本质上仍旧是一种精英文体。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当启蒙占据主导的时候,小说会成为核心文体。“五四”时期小说地位的提高,与其所承担的启蒙角色有重要关系,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地位的凸显和提升,就与彼时的“新启蒙”思潮有关。
相比之下,诗歌虽然很少有集体创作,虽然历史上也有过精英化和远离大众的倾向,但诗歌却是最具有大众化倾向的文体。中国自古就有民歌的传统,采风之说渊源有自。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特别注重诗歌的创作,所以才会在1958年提出古典加民歌的诗歌发展路径的设计:“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P322)显然,20世纪50—70年代诗歌选本的大盛,与毛泽东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思考有关。毛泽东提出新诗的出路在于古典加民歌以及因之而起的新民歌运动,都对彼时诗歌选本的大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一种文体思考,是建基于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构想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在其内容上的为人民服务,还体现在其创作主体的人民构成上。古典加民歌,恰好可以成为这种“人民文体”。而事实上,动员大众,很多时候主要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简明、鲜明而集中就成为其要求,古典加民歌某种程度上正好可以做到这点。
情绪表达和大众动员是诗歌的主要功能。这也决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诗大众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民歌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及“文革”结束后伤痕诗歌的流行。但大众动员终究不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更多的时候,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其文学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启蒙和提高上。小说正是充当了这种启蒙和提高的任务。这种状况,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选本中小说选本在总体上占据主要位置;其时,影响较大的,也多是小说选本,比如说《重放的鲜花》(所选主要是小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要是小说)《当代短篇小说43篇》《探索小说集》《探索诗集》和《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等。
具言之,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选本所占比例总体上较少,大众文体,诸如民歌、散文(这是广义上的散文,还包括通讯、回忆录、特写、报告文学等)和曲艺选本所占比重较多,只要翻阅中华书局编印的“全国总书目”(最开始是由新华书店编印,后改为中华书局编印)系列就可以明白这点。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当时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说,是对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的理解决定了这一类选本的大盛。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2](P861-862)虽然这里的“目前”特指的是1942年前后的抗战语境,但就文学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构成主要是工农兵而言,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70年代仍然有效,而事实上,彼时的人们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即是说,在人民的构成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占极少的部分,文学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状况,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编纂,不是为了经典的遴选或艺术追求,而常常意在普及。因此选本编纂中,是否合乎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其编纂的重要标准。之所以特别注重民歌、散文和曲艺,一方面是因为其读者面广;另一方面也因为人民大众能够参与这些文学体裁的创作中去,20世纪50—70年代盛极一时的《红旗飘飘》即是其体现。相对而言,小说要显得更具个人化与个人性了。这也能理解,在20世纪50—70年代针对现代时期诗歌的选本极少出现,其很大程度在于,诗歌在现代时期还主要是一种精英文体,不宜被重视或过多推崇。另外,还要看到,民歌、散文选本的繁荣,还表明另一个重要层面:这是真正繁荣的人民的文艺的时代,即所谓人民参与写人民。这是人民的文艺的表现形式。
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相关,决定20世纪50—70年代选本编纂的制约因素的,还有所谓文学大众化的诉求。在当时有所谓通俗文艺与非通俗文艺的区分。按照新华书店编《全国总书目》的区分:“通俗读物与非通俗读物的划分,还没有一个完全恰当的标准,我们现在大体上是按照语文程度来划分的,即凡适于小学至初中程度的人阅读的列为通俗读物,高于这一水平的为非通俗读物。”[3](P3)虽然说这一划分只是大略,但反映出一种趋势,即对通俗文艺的推崇和支持。文学的大众化,造成20世纪50—70年代中,通俗文艺的选本大盛和非通俗文艺的选本相比稀少,后者甚至可以说屈指可数。
以诗歌为例,20世纪50—70年代的诗歌选本中,关于“五四”以来现代时期的新诗,在当时主要以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56和1957年两个版本)为代表。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选本,在“百花时期”,有过年选系列,比如《1956年诗选》《1957年诗选》《1958年诗选》。还有关于建国十周年的诗歌选的编选以及《萌芽诗选》等。而像《萌芽诗选》,其实已经向通俗文艺靠拢了。即使是这些选本,其中很多已经表现出趋向大众化的倾向。里面的选诗标准,一些是倾向于进步或革命的主题,一些是倾向于工农兵作者。这一时期,工农兵诗歌选本或民歌选本数量甚多。
与之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选本构成中小说选本开始趋多。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选读》丛书中,小说选本占绝大部分。再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三十周年选本,其中短篇小说选有8厚本,诗歌只有3卷。这里,固然有诗歌体制短小,故而容量上只有3卷薄本,但其深层次上还与当时对建国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有关。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就体量而言,显然要远远多于小说创作。但为什么诗歌选本只有3卷,而小说选本有8卷呢?显然这涉及背后的评价问题。在当时看来,建国十七年时期,小说的成就要明显高于诗歌。建国十七年的诗歌写作,很多都是工农兵写作,而小说则主要是专业作者。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是,文学终究还是精英主义的产物,非专业作家很难写出好作品。
二
不难看出,20世纪50—70年代诗歌选本的大盛与选本的功能变迁息息相关。也就是说,通俗文艺和文艺的大众化趋向下,诗歌选本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普及上。这决定了诗歌选本的编纂,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经典化的产生和形成。即使是郭沫若和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其在当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实验色彩。“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4](P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重大变迁,文学的精英化倾向抬头。这一文学观的影响下,文学选本的编纂日益凸显其经典化功能。艺术标准日益成为文学选本编纂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文学的大众化倾向,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选本的另一重功能,即往往只具有汇聚和集中的功能。虽然说这一功能与经典化不无关系,但其侧重点不在经典化,而在集中展现上。选本的非经典化功能,某种程度上是与它的表现形态彼此对应的。很多时候,它不再是二度发表,而仅仅是首次发表。这在那些新民歌和工农兵作者那里更为明显,比如说《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这个选本的“选源”是小靳庄——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下面的一个大队。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的群众诗歌创作实践的集中展现。与一般的工农兵诗选或民歌选相比,其“选源”显然要窄得多,因而也更具有首次发表的特点。这一选本编纂形式,在这之前的民国时期,主要在那些民歌的收集整理中才会出现。但若仅仅看成是历史的隔代延续,则又是明显的误读。就像《小靳庄诗歌选》的“后记”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选本的编纂是为了回击所谓的“上智下愚”“天才论”。[5](P172)也就是说,这一选本编纂有其明确的所指和针对性。选本的出版,在当时有打破由精英知识分子占据的文艺界的格局的功能。那些原本不可能在精英所占据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很多直接就可以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关于这点,还可以联系毛泽东当时的一个重要判断。毛泽东在一个“指示”中曾表示了他对当前文坛被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统治(即“‘死人’统治”)的非常不满:“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6](P512-513)这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对精英控制下的文学发表机制的不满,也表明一点,选本编纂中的后退倾向并不是要回到古代或现代,而是对当前文学选本编纂实践中的精英化趋势的反拨与扬弃。
也就是说,选本出版也是一种重要的发表方式和渠道。这对现代意义的文学出版体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同时,也与古代民歌的收集整理不同。古代民歌的收集整理,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经过精英知识分子整理过的。而20世纪50—70年代的大量的民歌和工人诗歌,虽然也经过精英知识分子之手,但此时精英知识分子已经过了思想改造,其立场和态度早已转移到人民大众身上,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的且程度很高的民歌和工人诗歌。换言之,20世纪50-—70时代,工农兵写作的主要和重要发表渠道就是选本出版。这从当时盛极一时的《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系列丛刊,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到80年代)、《志愿军一日》(4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200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选其中部分,分成上下卷再版)等大型选本(或系列丛书)可以看出。
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裁格局与选本编纂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争鸣作品选入手。争鸣作品选是彼时影响很大的选本类型,但争鸣作品选是一种综合性的选本,里面集中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具言之,争鸣作品中,小说占据主要部分,其次是戏剧(包括话剧),很少有诗歌或散文的影子。以《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为例。其所选争鸣作品45篇(条)中,小说27部,戏剧12部,诗歌只占一首,即郭小川的《望星空》,另外就是条目“朦胧诗”。另外,像《争鸣作品选编》(2册,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1981年12月),其中所选作品24篇(条),小说17篇,电影文学剧本3篇,话剧1篇,诗歌3首。叙事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剧本和话剧也属于此类)之所以更容易引起争鸣,与叙事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现实问题有关。这是一些可以被称之为“问题写作”的文学作品,它们引起争鸣,不是因为其文学形式的创新,更多是因为它反映的内容上。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叙事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的地位的重要程度。
但这里也有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70年代,有的只是作品引起的争论而后遭致批判,比如说《武训传》《海瑞罢官》《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真正引起争鸣并成为繁盛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则开始衰退。与之相对应的,是争鸣作品选编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有争鸣作品选出版,但更多是带有总结性的,或者带有刻意构筑争鸣现象的倾向。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的争鸣作品选,带有制造话题以引起争鸣的倾向。比如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争鸣现象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作品的题材或内容引起人们普遍关注,进而形成争鸣讨论的空间。
就体裁而论,诗歌和小说形成争鸣的情形明显不同。诗歌创作潮流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某个诗歌作品本身却难以起到这样的效果。比如说关于“朦胧诗”引起的争论,其开始虽然与顾城的几首诗和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海南情思·夜》有关①,但争论发展到后来,实际上已经转移到青年一代的“思想感情”和“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7](P7)上,与某一或某些诗其实关系不大。小说争鸣现象则相对复杂些。其中既有因某些具体作品,比如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等引起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就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及其与此相关的某一类社会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就作品引起的争论,很少会关注文学表现的形式本身。即使是朦胧诗的争论,其涉及的也多侧重于“精神状态”[7](P5)的不健康情绪上,比如说“失望”“迷惘”“彷徨”和“虚无”[7](P6)或“心灵上的阴霾”[7](P38)等,表达上的懂与不懂(即“朦胧”“隐晦”等)首先是相对于情感的健康与否而言的,即是说是次要的。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小说的争论往往针对表现内容,而诗歌引起的争论则多聚焦情感表达上。这种不同,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争论,更多是在小说(包括其他叙事文类)这一块。这是彼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启蒙(即新启蒙)所决定了的。“新启蒙”时代关注的焦点是表达什么,而很少是怎么表达。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偶有作品出现但难以形成潮流的原因或在于此。
同样,也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选本中,还有获奖作品选。关于这点,从这些获奖作品选的印数和销量可以看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印刷数是10万册,同年10月第二次印刷10万册。这些获奖作品选中,诗歌获奖作品选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蓝棣之选编《当代诗醇——获奖诗歌名篇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另外《诗刊》社编《1979—1980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也收有部分获奖诗歌。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诗歌奖。而只是表明小说获奖的影响程度较高。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文学奖项主要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争鸣作品选和获奖作品选的出版及其影响走向式微。另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选本开始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是追求商业热点,一是学院化和体制化。各种文学史选本,或者总结回顾性的综合选本有规模的出版。回顾和总结新时期,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选本编纂的一大特点。此时,小说选本虽然仍占据主要部分,但其影响力早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所能比了。
三
在选本编纂中,篇幅的长短是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决定了长篇小说通常不被收入选本,选本的种类按体裁划分大致分为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包括杂文、报告文学)和戏剧(主要是独幕剧),其中占据主要地位或核心位置的是短篇小说选和诗歌选。就此而论,选本之“选”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展现,其次才是“精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选本的现代性问题。就古代选本而言,其选本编纂还肩负另一重功能,即保存的功能,所谓“网罗放轶”[8](P278),其“总集”之“总”名,与此不无关系。但对于现代以来的选本而言,“总集”之“网罗放轶”的功能有所减弱。随着现代印刷业的发展,通过选本编选来保持作品,似乎已不如此前重要,而通过选本来“选”,即“删汰繁芜”[8](P278)的功能则有所加强:出版物急速增多,通过“选”来引导读者阅读就成为必须而必要了。选本之“选”起着延缓或对抗现代性时间维度上的速朽和易逝功能。此时,所选作品的篇幅长短就是选本编选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了。选本之“选”,如果其所选作品在数量上有限,“选”的意义不能得到很好体现。而如果“选域”范围很窄,也不能体现其“精选”的价值。这都要求所选作品篇幅上要相对短小。但这也造成选本编纂实践中一个永恒的难题,即篇幅的相对较短与作品的代表性的问题:篇幅较短的作品,是否具有某一作家的艺术水平或某一潮流流派的典型的代表性?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篇幅短小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多高?最能代表文学史上艺术成就的高端的,是长篇还是短篇?这些问题,都在选本编纂实践中集中体现出来。
就诗歌而论,诗歌形式的体裁较短,诗歌作品的好坏,与篇幅的长短没有太大关系,这也决定了选本构成中,好的诗歌选本最能集中反映一个时代或某一潮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水平。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选本,大多都是诗歌选本,与此有一定关系。古代自不用说,现当代以来也是如此,比如说《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3个版本)《九叶集》《中国新诗选》(臧克家编,3个版本)等。对小说创作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小说选本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短篇小说选,而不是中篇小说选,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年选,其销量总是要高于同期的中篇小说年选。但年选的编选标准相对保守,年选的独特性欠缺,主体性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年选编选越来越趋向于各人编选,选家的主体性很强,但因为每年的年选品种很多,如果把所有年选入选作品集中起来,与当年度的发表作品比较,年选之“选”的功能在总体上看并不明显(这与单个年选的“选”的功能显著程度,恰成反比)。短篇小说选本中,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流派或思潮作品选。这是因为,虽然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最能代表其创作成就高低和文学史地位的,通常是长篇作品,但就文学流派或思潮论,短篇或中篇亦具有思潮流派的代表性,甚至可能代表性更强。
作品的长短不仅决定或影响其收入选本与否,同时也决定或影响其收入选本的方式。中篇和短篇一般是全选,而长篇小说、多幕剧或长诗,即使偶被收入选本,其收入的方式则分为“全选”、“节选”或梗概几种。以长篇小说为例。长篇小说被收入选本中,在选本编纂史上与《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关。其一般的做法是列入长篇小说篇目,这在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比较常见,陈思和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也是采用这种方式。长篇小说很少被收入选本,当然有篇幅的考虑,还与读者的阅读有关。长篇选本中只能选择为数不多的几部,这样一来,其选本的“选”和“集”的功能就不能得到很好体现。另外,读者完全可以去买长篇小说的单行本,而没有必要买这一选本。选本中收入长篇小说,往往只具有建构文学史秩序的意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及其后)是如此,《陕西文学六十年代作品选》《建国50年四川文学作品选》《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等地方省市长时段综合性文学作品选也是如此。中短篇小说选本则不同了。中短篇选本中凸显了选和集的功能,可以免去读者的选择之苦和选择之功。相对来说,长篇小说选本在这方面的功能则严重不足。虽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的编选中,创造了全选和节选的方式,但终究其所选择的数量不多,而且节选也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其《长篇小说卷》卷一和卷二,都是全选,《长篇小说卷一》收录有王蒙的《感受昨天》、梁斌的《红旗谱》和杨沫的《青春之歌》;《长篇小说卷二》收录的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孙犁的《风云初记》和赵树理的《三里湾》。《长篇小说卷三》是节选,收录的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王蒙的《青春万岁》、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里,关于全选和节选两种方式,体现的其实是两种态度和评价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全选和节选,代表的是文学史秩序中位置和地位的不同。被全选的,一般是高度肯定的作品,而被节选的作品,虽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长篇,但总因某些原因,难免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即节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编选者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和犹豫:“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前十七年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出现过不少佳作、大作、力作,但这些作品,除了积极反映时代主旋律、题材重大、主题鲜明、正面人物突出以外,往往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又打上了负面的时代烙印,主要是指受‘左’的思潮影响和时代烙印。”[9](P687)
这样一种全选和节选的编选方式,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有延续和发展,其中长篇小说卷中,前三卷是全选,后两卷是节选。而在节选的《长篇小说卷》卷五中除了节选的部分外,还增加了“存目”部分。至此,长篇小说收入选本中的编选方式及其格局最终确定下来,即全选、节选和存目。三种编选方式,代表了三种评价态度:高度肯定、比较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梗概这一编选方式,则更多与选本的篇幅有关)。而之所以在长篇小说卷中全选、节选和存目的做法,除了评价上的不同态度外,还与编选者们对此一时段的长篇小说及其文学总体的评价。比如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中,长篇小说有3卷,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只有1卷;所选数量,长篇(包括节选)有19部,中篇只有9部。这样一种比例说明,在编选者看来,建国十七年时期,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长篇上。再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中篇小说卷有4卷,收入52篇作品;长篇小说5卷,收录(包括全选和节选)有32篇作品。显然,就小说作品的数量而言,中篇在总量上要远远多于长篇,但在进入这一大系中,它们的比例却只是1.63∶1。这样的比例说明,《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对此一时段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总体评价上要高于中篇小说。进言之,就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的历程来看,编选者的潜在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文学创作越来越成熟,长篇小说的成就相应也越来越高,也最能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学成就。
此外,还要看到,带有文学史性质的大型系列选本,在编选作品时因为有大致趋同的文学史观的限制,其选择作品时可以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即使选择了长篇,也是在综合权衡下的产物。这也决定了文学史性质的选本,或带有教材性质的选本中,选家的主体性不强,选家也不可能发挥自己独到的编选标准。从另一个角度说,选家要想发展或凸显自己的主体性,就必须舍弃长篇小说,必须编选教材选本之外的个人选本。谢冕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就是立足于编选者自己对文学经典的理解,而展开的选本编纂。但不管如何发挥自己的独创,小说的核心地位都是不被编选者质疑的。
四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本编纂格局中文学体裁的分类及其配置,并不仅仅是选本编纂格局所内在决定的,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症候。就当代文学而言,选本编纂的体裁格局变迁,涉及当代文学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命题,诸如文学功能定位、文学的大众化倾向、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文学的“人民性”内涵、文学主体的构成,等等。选本编纂作为首次或二次发表(有些选本在经过选刊二次发表后,属于三次发表)方式,其所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选”的姿态,更是时代主题及精神的表征,在这当中,选本编纂以“选”的方式自觉运用文学体裁或类型分类原则,既强化了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评价与看法。
注释:
①参见顾工的《两代人》(《诗刊》1980年第10期)和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