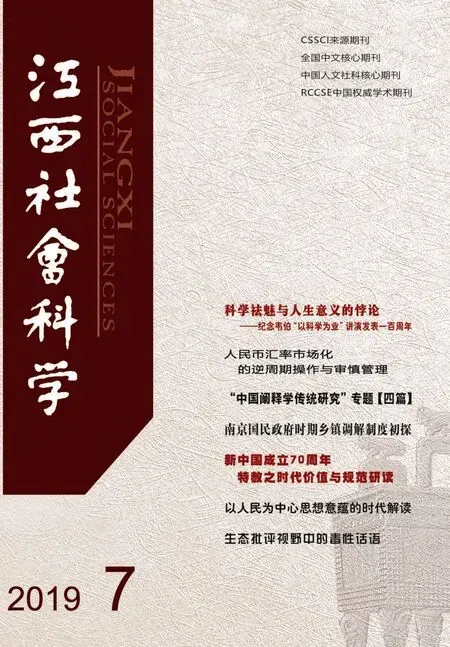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的缘起
自古以来,民间纠纷往往由宗亲、中人、保人、士绅等主持调解。由于调解制度的历史惯性,这些解纷主体在近代社会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调解主体日趋多元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乡镇调解委员会,专司民间调解事宜。以调解委员会为调解主体的乡镇调解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产物,也是对法院调解制度推行不力、成效不彰的一种补救措施。
(一)乡镇调解制度是地方自治的产物
清末推行“新政”期间,“地方自治就作为宪政之基被清政府寄予厚望”[1](P168),其模仿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先后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按照上述章程,府厅州县所在地为城,其他镇、屯、村等满五万人口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城镇乡均设自治公所,自治事项除了卫生、学务、农工商务、公共事业、慈善事业和道路交通等外,还有“全城镇乡诉讼及其和解之事”[2](P661)。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的开端,也是近代城镇乡作为一级自治组织承办调解事项的开始。
民国初年曾一度停止推行地方自治运动,乡镇作为一级自治组织也不复存在,区作为一级新的基层政权开始出现。区长开始参与到基层事务中,“除承担调查户口、侦查匪盗、禁赌、禁烟等职责外,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职责,即调解(或称评解、评议)各种民事纠纷”[3](P340)。1923年,区村制实行后,调解成为区长的一项重要职责。有学者对民国初年区村制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后认为,区长调解制度“是民国初年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展的产物,它代表着调解制度的一种制度化、组织化和官僚化的趋势”[3](P361)。这种调解的组织化、制度化趋势以乡镇调解的形式被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下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是当时推行乡镇地方自治的产物。1929年6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县组织法》。根据该法,1929年9月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乡镇公所均应附设调解委员会,办理民事调解事项以及依法得撤回告诉之刑事调解事项。[2](P700)该立法之本意系息事宁人,固然值得称道,但仅凭这一粗略规定,能否收到实效,是否会违背立法本意,尚不可而知。因为“惟当此自治萌芽之时,一般人民尚无行使政权之充分能力,倘乡区镇坊各调解委员会滥用职权,把持讼案,不问法律上是否许其调解,亦不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一任己意,不独侵及法权,抑且转为民累,况调解委员会各委员均由公民选出,即各委员自身亦未必全具法律知识而能依法调和毫无违误,若不明定标准,严加限制,流弊所底,讵堪设想”[4](P48)。因此,1931年4月31日司法行政部颁布《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严定调解委员会职责,以免侵越,以杜流弊。各省根据这一规定,纷纷另行制定规章,以资推行,如1933年青岛市颁行的《青岛市乡村调解委员会规则》、1935年浙江省颁行的《浙江省各县乡镇公所办理调解事项暂行办法》等。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是当时推行地方自治的产物。对于乡镇调解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时人已有明确的认识:“我们谈地方自治,乡镇调解制度的建立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而且我们还可以强调的说:乡镇调解制度不能建立,根本就谈不到地方‘自治’了。”[5](P14)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仿制药对比原研药治疗冠心病的疗效、安全性与经济性的系统评价 ………………… 边 妍等(21):2980
(二)乡镇调解制度是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的补救
为了解决近代以来案件积压给法院造成的压力以及诉讼迟延给当事人带来的讼累,在吸收传统调解文化并借鉴西方各国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以“杜息争端,减轻讼累”[6](P9)为宗旨的法院调解制度。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事调解法》和《民事调解法施行规则》,对法院调解制度做了专门规定。1935年新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调解法的相关内容纳入“简易程序”中,并根据民事调解法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从而使法院调解制度趋于完备。
然而,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瑕疵、法院执行不力、法官敷衍以及当事人的不重视,法院调解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20世纪30年代初法院调解制度开始正式实施至40年代,民事案件调解成功率仍徘徊在20%上下,这与司法当局最初的设想有着较大的差距。1942年,司法行政部在咨文中对此表示出极大的遗憾:“是以十载以还,本部虽曾三令五申,督促各司法机关厉行调解,亦未达到预期之目的,鉴往察来,实有另辟途径之必要。”[7](P26)这里的“另辟途径”实际上就是要大力推行乡镇调解制度,这从司法行政部在《区乡镇坊公所实行调解与宣传公证说明》中可以得到明证:“虽法院在起诉前亦可进行调解,免使成讼,但人民狃于积习,事入公门,每多忌讳,形禁势隔,收效实难,其最有效之方法,莫若使人民遇有纠葛发生,即由区乡镇坊各公所或其调解委员会就地实行调解。”[8](P17)可见,在法院调解制度成效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司法行政部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自3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但未受到重视的乡镇调解制度上来,并对其寄予厚望,“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系由当地公民选出,多为地方公正士绅,与人民既属接近,而区乡镇坊所辖区域范围不广,其境内人民发生争端,亦知之甚悉,如在人民未兴讼之先,即由区乡镇坊公所调解委员会负责秉公调解,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7](P26)。于是,司法行政部把乡镇调解作为中心工作。1942年7月1日,内政部也把“调解纷争”列为乡镇应办事项之一。
二、乡镇调解的制度设计
基于对乡镇调解工作的重视,1943年10月9日内政部、司法行政部会同公布了《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9](P102-103),对乡镇调解主体、调解程序、调解结果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正式完成了乡镇调解的制度化设计。
(一)调解主体的专门化
与民间调解中的士绅、乡邻亲友、中人、村长等个人调解不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乡镇层面成立了专门的调解组织——乡镇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事宜。
乡镇调解委员会由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于乡镇公民中选举乡镇内具有法律知识之公正人员充之。调解委员会初由三人至五人组成,后来扩展为五人至九人。调解委员属于自治人员,乡长、副乡长或镇长、副镇长等公务人员非辞去职务,不得被选为调解委员。
调解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调解委员推举产生,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得委托其他调解委员代理。主席及委员概属无给职,任期均为一年,任期届满时,得连选连任。当选之乡镇调解委员,由县政府颁发证书,并在县政府备案。调解委员有违法行为时,除送请该管法院依法惩处外,得由乡镇公所呈请县政府批准,先行停止其职务,并提经乡镇民代表会或乡镇务会议罢免之。
乡镇调解委员会附设于乡镇公所内,如所属人民有请求调解时,应请乡镇公所通知调解委员,依法调解。调解委员会在办理调解事项时,得随时调用乡镇公所附属人员,费用由乡镇公所承担。
(二)受案范围的法定化
传统社会中,国家对于民间调解不作干涉,完全任民自便。因此,民间调解的纠纷范围非常广泛,小至家长里短、口角纷争,大至财产债务纠葛、打架斗殴,甚至殴伤人命之类的重案,都有民间调解人参与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则严格限制在《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所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与具有较大随意性的其他民间调解形式相比,乡镇调解委员会须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调解权限。
关于民事案件,乡镇调解委员会受案应受下列限制:第一,已经法院受理之民事案件,经调解后须依法定程序向法院申请销案;第二,依民事诉讼法正在法院调解之事项,不得同时另行调解。
关于刑事案件,乡镇调解委员会所能受理的案件范围主要有如下十类:妨害风化罪、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伤害罪、妨害自由罪、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妨害秘密罪、窃盗罪、侵占罪、诈欺背信罪、毁弃损坏罪。[10](P250-257)上述十类案件中,凡属于告诉乃论之罪,调解委员会方可受理;凡非告诉乃论之罪,调解委员会则不得受理调解。例如,伤害罪中,伤害他人之身体或健康者、施强暴于直系血亲尊亲属未成伤者、因过失伤害人者,调解委员会均可受理,其他伤害罪,调解委员不得受理。又如,妨害风化罪中,以诈术使妇女误信为自己的配偶而听从其奸淫者、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相互和奸者,调解委员会可受理,其他妨害风化罪,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再如,妨害自由罪中,意图使妇女与自己或他人结婚而略诱之者、无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筑物或附连围绕之土地或船舰者、无故隐匿其内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滞者,调解委员会可以受理,其他妨害自由的行为,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
(三)调解程序的规范化
一般情况下,民间调解没有严格的程序可言。纠纷发生后,调解人或者奔走于纠纷双方,进行说和劝导;或者召集纠纷双方,采取摆宴席、“吃讲茶”的方式,使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中规定了比较严密而规范的调解程序,初步实现了调解程序的规范化。
1.当事人申请。当事人申请调解,须向乡镇公所陈述其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调解事由等,并应附送该事由的关系文件。乡镇公所接受申请后,将其移送至调解委员会。当事人申请调解,既可用书面,也可用言辞。用言辞申请调解者,应先由乡镇公所作成书面记录后,再移送调解委员会。
2.开会调解。调解委员会接受申请后,应决定开会调解的日期,经由乡镇公所通知当事人亲自到场。开会调解时,调解委员会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可开始调解。调解委员对于调解事项有涉及本身或其同居家属时,应即回避,以保证调解的公平。民事调解事项须得当事人同意,刑事调解事项须得被害人同意,始能进行,调解委员会不能有强迫及阻止告诉各行为。办理调解事项除勘验费由当事人开支外,不得征收任何费用或报酬。
3.制作调解书。《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第5条规定:“调解委员会,于调解成立后,应本两造之意旨,书立调解字据,以资证明。”这里的调解字据,即为调解书。因此,调解委员会已调解成立的事项,应叙列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及事由概要,并调解成立年月日,制作调解书,送由乡镇公所呈报县政府及该管法院备案,其不能调解事项,并加叙不能调解原由,分报备案。调解书的格式,可比照民事调解笔录制定,由全体调解委员签名盖章,加盖乡镇公所图记后,调解书即告完成。
乡镇调解委员会调解成立的案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调解双方当事人不得随便反悔,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就原请求继续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对于乡镇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然而,对于调解结果,如果一方当事人拒不执行,乡镇调解委员会则无能为力,因为乡镇调解委员会本身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也没有请求法院协助执行的权力。因此,在调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反悔,另一方却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向法院提起确认调解成立并给付之诉,而调解委员会所制作的调解书只能附呈法院作为参考之资料。可见,乡镇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从效力上看,远远逊色于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法院调解。
三、乡镇调解制度的成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乡镇调解的相关法规颁行后,一些乡镇召开公民大会,开始选举调解委员,组织调解委员会。40年代开始,司法行政部把乡镇调解作为中心工作。在司法部的倡导下,各地纷纷成立乡镇调解委员会,制定调解委员会办事细则,开展调解工作。在基层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在解决争端、排难解纷、和邻睦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的推行并没有实现司法行政部弥讼息争、便利民众的立法本意。换言之,当时乡镇调解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如下。
(一)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
近代以来,地方制度变更频繁,这不能不说是导致乡镇调解制度成效不佳的一方面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训政初期,倡导地方自治,在各县之下的区乡镇坊推行自治。然而,由于地方自治效果不佳,尤其是在维持地方秩序方面作用不大,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制度之中,以自治之名推行保甲之实,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随着保甲制度的推行,一些地方的自治运动无形中停顿下来,作为地方自治组成部分的乡镇调解制度虽然没有明令废止,却难以有效实施。例如,1935年,江苏省民政厅根据嘉定县县长许次玄呈请解释保甲制度、自治法规疑义等情事,声称该县正在举办保甲,区乡镇调解委员会,应一律暂缓设立,将来应否设立,应候另令通案办理。[11](P5)可见,作为乡镇调解主体的乡镇调解委员会的设立随着保甲制度的推行被无限期推迟,而那些已经设立的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察哈尔省政府公报中记载:“本省自区长取消,乡镇改组后,监察、调解委员会,大半无形停顿,即尚未停顿者,率皆敷衍从事,徒具虚名。”[12](P28)其他各省区类似情况也不少见。
(二)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几部有关乡镇调解的法规,都规定了调解不得征收任何费用,立法本意虽好,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因为缺乏必要的调解经费影响到制度的成效。如果调解委员属于乡镇公所的公职人,有基本的俸禄维持生活,情况或许会好一些,问题是调解委员均无给职,在旷日费时的调解工作中,调解委员如果没有足够的奉献精神,难免会觉得厌倦,调解热情不高,积极性欠缺,调解成效自然会大打折扣。当时也曾有多人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予以解决,如南海县县长李海云曾向广东省民政厅呈文称:“查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规程,对于各级调解委员会经费,并无明文规定,所有各级调解委员,似应酌量支给夫马费,兹拟区调解委员每员月支夫马费不得过八元,乡镇坊调解委员每员月支不得过四元,均由各该区乡镇坊公所筹拨。”[13](P46)这一建议,未得到明文批复,最后不了了之。由于缺乏必要的合理的调解经费,以至于各地调解委员会往往违反规定,擅自收受调解费用,如山西省晋城周村调解委员会沿用旧时的习惯,遇有村民请求调解事件,先由申请调解人员到镇公所缴纳打钟钱5000文,方为受理,无论申请人有理与否,打钟钱必须缴纳。其他各村也均有缴纳打钟钱之陋规,以致一般贫苦百姓往往无钱打钟,即含冤了事,不再请求调解。[14]另外,山西还有一些地方要求申请调解人缴纳灯油若干斤之陋规。甚至一些地方制定的调解规则中就明确要求缴纳调解费,如《湖南省乡镇调解委员会调解规则》第14条规定:乡镇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除当事人确系赤贫应免收费用外,得斟酌案情及当事人财力,决定收取调解费金元五角至一元。[15](P7)
对调解委员的任职资格要求不够明确,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调解效果。无论是30年代颁行的《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章程》,还是40年代颁行的《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都没有明确规定调解委员的资格条件,这必然导致大量素质较低的人员混杂于调解委员队伍之中。按照规定,调解委员由乡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民意。但问题在于,被选举人没有资格限制,未免存在纰漏。如果被选举为调解委员的人员不具备必要的调解素质,如公正的品质、良好的操行以及必备的人文和法律素质等,那么调解结果可想而知。河北省临榆县县长代本县公民请求司法院解释调解委员“如有不通文理目不识丁者,是否有应选资格”,即反映了时人对于不具备一定素质的人当选为调解委员的一种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试想一些不通文理甚至目不识丁的调解委员,对于调解双方的法律诉求以及国家的法律条文能否真正领会并予以很好地理解,必然存在问题。当时的内政部对于不通文理、目不识丁者能否承担起调解事项也心存疑虑,然而,司法院却认为自治施行法对此并无限制,这些人应具备候选资格。[16](P33-34)有学者曾撰文指出,如果让没有丝毫法律知识的调解委员,担负起调解纠纷的重任,无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险将不堪设想。[17](P33)个别地方政府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鼓励乡镇内具有法律知识的公正人士,应选调解委员,并由县市政府会同法院召集各委员举行短期讲习会,予以法律知识的训练,这种做法值得效仿,但却并未得到推广。
乡镇调解效力不高也是制度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之一。按照规定,乡镇调解委员会对于所办理之调解事项,不得为财产上或身体上之处罚,也就是说,乡镇调解委员会没有处罚权,这样做出的调解结果往往对当事人没有明显的拘束力,即使结果是合理的,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履行,乡镇调解委员会也无能为力。因此,人们发生纠纷后,要么请乡邻主持调解,要么到法院起诉,而不愿意赴乡镇调解。为了提高乡镇调解的能力,时人曾提出解决办法:第一要规定民刑事轻微案件,在提起诉讼之前,必须经过区乡镇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未经调解而起诉者,法院得批令调解;第二要承认区乡镇调解委员会之调解,经过向法院备案手续后,有与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而执行之责,亦可由区乡镇公所负之。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建议未得到司法部门的认可。
此外,乡镇调解与法院调解、民间调解之间缺乏有效对接,且分工不够明确也是乡镇调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也是造成乡镇调解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
(三)调解制度执行中的敷衍
尽管当时司法行政部三令五申,要求各乡镇公所成立调解委员会,但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设立调解委员会,一直到1946年广东省政府代电中仍然在督促各乡镇要尽快成立调解委员会:“查各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自公布施行以来,迄已数载,各省市县政府已按照规定督促各区乡镇公所,成立调解委员会者固多,而以民智未开及种种困难,迄未成立或徒具虚名者亦不少。”[18](P13)
此外,各地对于办理调解委员会并不热心,往往敷衍了事,有些地方虽然设置了调解委员会,但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如山西中阳县、石楼县、宁武县、方山县等即是如此。[19](P87)对于这种情况,各省也往往发出训令,督促各地尽快成立调解委员会,认真办理调解事项,如山西省政府村政处多次发布训令,要求每个县要经常派稽查员下乡,对于调解委员会认真查勘指导,以免各地再行敷衍。
按照规定,调解委员会不能对当事人做出财产上或身体上的处罚,否则,即属违法。事实上,各地调解委员会在进行调解时,常常超越权限,做出类似于判决的一些处罚。如湖南省桃源县第三区调解熊花生与熊会臣等一案中,调解结果除由熊会臣等酌给药资洋五元外,并交由该族人拘押五日。[20](P3)拘押属于刑事处分之一,非依法判决,绝不能任意拟处。又如,湖南省桃源县第九区调解聂益记与黎大儿一案,将黎大儿拘留三日。[21](P3)再如湖南攸县第四区调解陈善才等与陈明仔等一案,也做出罚做苦工五日的处罚。[22](P4)这些无视禁令、非法越权的行为在各地的调解委员会中并不少见。
四、余 论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传统社会中,充当民间调解人的主要是乡约、宗亲、中人、保人、士绅等,这些调解人的调解活动带有自发性和随意性的色彩。近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乡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出现的村长、村政等利用自己对村民事务的熟悉以及自己在村民中的威望,在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一人之力有限,且易受个人主观情绪的影响,纠纷解决中难免会出现偏私。随着近代地方自治的倡导,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效力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弊端,制度实施效果也不够理想,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
其一,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矛盾和纠纷也日渐增多,传统的解纷手段已不敷使用,乡镇调解委员会作为新的解纷主体,依法承担起调解之责,这对于及时化解纠纷,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防止矛盾的升级和扩大,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促进基层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中国司法近代化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现象严重。乡镇调解制度的实施,把矛盾和纠纷化解于诉讼程序之外,减少了流入法院的案件数量,无疑会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使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力量解决重大刑事犯罪问题。
其三,推动了中国调解的法制化进程。古代调解多属于民间的自发行为,缺少制度化内涵,更不具备法制化色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颁发《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法律法规,对乡镇调解的组织机构、人员构成、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结果及效力等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使乡镇调解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是基于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从总体上看已经过时了,但其所蕴含的某些精神和价值却可以借鉴。乡镇调解委员会作为一个专司调解的组织,在发挥团体调解的优势、保障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等方面值得肯定。更为重要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