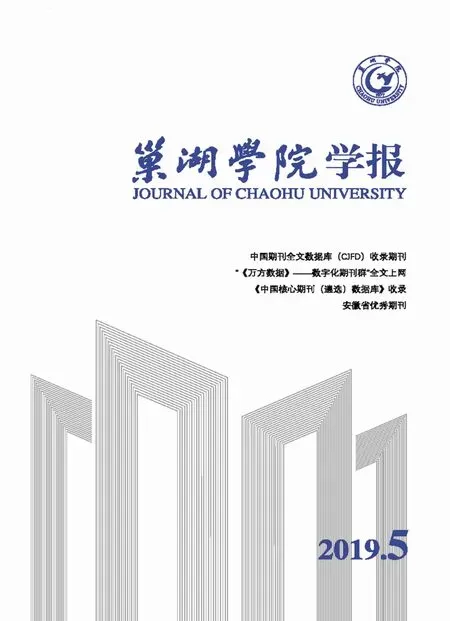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驻外使节的政治任用与外交使命研究(1931—1945)
汪秋菊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自1931年起,中、日关系就较为紧张,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中日情势便急剧恶化,“当时,两国之间未解决的所谓悬案,据说只东北地区便有五十三件之多。”[1]“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处此民族存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显得尤为重要,其国家之安全实有赖于外交之折冲樽俎及外交人才之冲锋陷阵。但在此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却大量任用从未办理外交事务之军政要人,充任驻外使节,对外交涉。
目前,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军政要人充任使节的情形颇有研究,研究既包括对外交官的个体分析,也包括将其看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人事的新变化而进行的宏观分析。石源华教授是对外交官进行个案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持的《世界知识》“民国外交人”系列曾发表一系列文章简短地论述这些驻外使节的外交活动。例如,他专门撰文分析了蒋作宾[2]、程天放[3]、杨杰[4]等人的外交事迹,称赞蒋、杨二人为临危受命的“军人外交家”,并对他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外毛吉康[5]、关培凤[6]、徐惊奇[7]等人也曾撰文介绍刘文岛、魏道明、邵力子等人的外交经历。在宏观研究方面,山西大学的岳谦厚先生将其与此时期外交官的人事制度结合起来分析,并在其《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一书中专设一节探讨此时期外交官的党派结构,经分析他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以党员出任外交官,其实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8]。而南京大学的申晓云教授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驻外使领馆的建设时,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她认为正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以党治国”的原则,才致使其对大使、公使的派遣更看重政治背景[9]。但总体来看,以上研究都较为零散,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任用军政要人的缘由也仅从宏观上进行了分析,许多问题仍缺乏深入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上,聚焦于此时以政治身份介入外交界的特殊使节,并具体分析其被任用的缘由、特点及其特殊的外交使命,以期全面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交官队伍的新变化。
一、任用缘由
(一)外交人才标准的变更及驻外使节作用的弱化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便大举侵华,国际局势较为紧张与复杂,国际交往的范围及内容也日益扩大,民国初年那种只注重外交知识而培养起来的人才已不适用。1933年徐景薇便发表《外交人才训练与培养》一文,对于应该建造什么样的外交人才,他称:“外交官固应熟谙国际政治,法律,经济等科学,固应明白世界大势,固尤应通晓外国文字,惟我国在国际间之立场如何,国内经济政治国防等等之状况如何,对外贸易之实际情形如何,以及历来吾国外交上种种失败之教训何在,均须一一熟稔,而本国政治情形,国民心理,以及国民革命之重大意义,尤须有彻底的明了。”[10]岳谦厚先生也曾明确表示:“现代国际社会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范围正在不断拓展,业已渗透至国家间文化与教育及政治党派、军事等专门领域,这些事宜绝非职业的外交官所能完全驾驭者。”[8]正是由于外交人才标准的此种变更,导致了处于国际交往进程中的南京国民政府更为需要的是既熟悉国内政情又善于办理交涉,从而能更好地统筹国内国外两方事务之人。也正因如此,其对于大使、公使等重要职位,开始就部内的高级人员,予以破格任用。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驻外使节的作用开始弱化。据顾维钧回忆,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非但不屑于征求中国外交代表的意见,而且常常在作出决定时除通知那些驻在直接国家的外交代表外,对驻在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甚至连通知都不给。他表示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公使降为了外交部长的代理人,外交部甚至常常在不完全了解国外反应的情况下作出决定[11]。确实,因科学进步,世界交通较前便利,各国外交领袖本身就可随时交换造访,而电报的发明,更使各驻外使节的地位及责任较前下降。到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急需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元首外交、特使外交乃致民间外交都异常活跃,更加导致了驻外使节作用的弱化,其日益成为本国政府的名义代表,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使选择那些从未办理外交事务之军政要人来充任使节,办理外交,也未尝不可。
(二)国民党奉行“党义外交”的结果
北京政府时代向来是以陆征祥、顾维钧、颜惠庆等职业外交官执掌外交舞台,这些职业外交官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外交思想及实践上又追求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孤立于党派纷争之外,但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以党治国”的原则,在外交上亦奉行“党国外交”“党义外交”,因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及国民政府的政策,都不够了解,并时常与国民政府领导人发生矛盾。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朱家骅就针对当时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了批评,他谈到:“此事发生后的第一天,国联理事会开会时,是日本代表首先起立说话,希望东三省就能恢复秩序。第二天,也是日本代表首先说话,被人家占了先着!施公使的答话,只说不是中国挑衅,何不把日本数月以来对中国之种〔种〕侵略情形,完全说出?而仅仅以未接训令为词,便算了事……”[12]其后,汪精卫在主持外交部时,也认为施肇基在华盛顿过分消极,跟他合作不够,并认为由国民党制定,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施总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13]。对国民党领导人而言,这些职业外交家并不是可望合作的好伙伴。因此,为更好地推行其外交政策,办理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直接任用党内要人担任使节,以作替代。例如,甄选中国首任驻德大使时,汪精卫便向从未办理过外交事务的程天放发出邀请,征询其同意,汪精卫更是直接表示:“现在中国还在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你是党的中央委员,可以代表党,也就可以代表国家”[14],积极鼓励程天放担任此职。
(三)国民党内各派系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上的人事任免问题十分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党内各种派别与团体较为繁杂,且其在政治上相互倾轧,争夺权力。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党派关系延伸至外交,最终导致了刘文岛、程天放等人直接以政治身份投身外交,出国就职。例如,刘文岛之所以出使外国,乃是因为刘在任武汉特别市长时与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等人矛盾尖锐。刘文岛的妻子陆继劭便谈到:“当时湖北省省长何成濬(浚)是吃喝玩乐之徒,刘文岛与他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夏斗寅,何成濬,杨永康等人对刘恨之入骨。……他们捷足先登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刘的各种编造的罪状,建议把他调职。蒋受到群小的包围,接受群小的意见,让刘出使德、奥、意等国。”[15]贺耀祖担任驻土耳其公使,与蒋介石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人对凯末尔主义及土耳其的复兴十分感兴趣,国人更是表示:“中国之于今日,已由老而衰,危险之大尽人而知。土耳其之在欧战末期,情势之险,远我甚矣。而竟有凯末尔之起,复兴士邦,一躣为强者之流。使民族回复少壮时代,颇值吾人钦仰与仿效者也!”[16]蒋介石更是直接表示土耳其这个国家跨欧、亚两洲,地位颇为重要。因此,当中土两国签订友好条约并首次互设使馆时,蒋介石选择了与其交好的贺耀祖,出任驻土公使。
程天放出任中国首任驻德大使一职,也与其党派身份密切相关。中德使节升格之时,正值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主持外交部,而程天放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关系甚好。1923年程天放在加拿大多伦多主持《醒华日报》时,陈璧君为执信中学募集资金,到达加拿大,在此期间,程天放不辞辛劳陪其奔走大半月,因而私交甚好。同时,程作为“CC”系骨干,素与陈果夫交好,因而在推荐大使人选时,“果夫先生就说天放同志是研究国际公法国际关系的,他可能胜任”[14],此时汪精卫正深感国民党内外交人才缺乏,用人困难,因而也十分赞成程天放担任此职。驻美大使魏道明与其夫人郑毓秀同为留法学生,其二人留法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关系密切,更被喻为“李氏系统的核心人物”。当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文矛盾频发,而宋欲以施肇基代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想法破产时,李石曾便积极活动,向蒋介石推荐了魏道明,“魏道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对各方情况比较熟悉,他为人谦和、灵活,何况还加上一个擅长交际的活动家郑毓秀,蒋介石对魏道明的印象也远比施肇基要好得多。”[17]正因此种复杂关系,魏道明才得以继胡适之后出任驻美大使。另外,驻苏大使邵力子、驻比公使张乃燕也都因私人关系,受人力荐而被委以重任,当时更有人直接批评张乃燕称其人于外交上无丝毫经验,此番出任公使,纯系凭借其阀阅之积势而已。
二、任用特点
正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党义外交”,在人才选拔上以能否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第一要义,因此,其对驻外使节的选拔更看重其政治背景,也多以政治人才出任外交使节。但对于大使、公使的具体人选,国民党政府并不随意拟定,其任命始终优先选择相对具有外交素养之人,并带有鲜明的针对性。
(一)优先任用有留学经历的军政要人
外交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除需具备专业的外交知识与训练外,更需要通晓外国文字,但当时国内较为缺乏这种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学校,因此,北京政府时代多吸纳海外留学生来充实外交队伍。“这支职业外交队伍的主要成员,不仅基本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且多数具有博士头衔,其中不少人还有着某一方面的渊博知识和造诣”[9],正因如此,北京政府时代外交官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办理国际事务时也赢得了许多赞许与好评。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多以军政要人充任驻外使节,但这些被特殊任命的驻外公使及大使,从其教育背景来看,相较而言,也并非完全外行。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以政治身份出任驻外使节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国外留学经历并精通外语,刘文岛、张乃燕等更是精通多国文字;另外,除邵力子只有留学考察经历,蒋作宾、杨杰、贺耀祖、张惠长等4人属于国外专门学校毕业外,其余5人均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所学专业多为政治、经济、法学等专门学科,且多获博士学位并著有较高水平的专门著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国际素养。也正因娴习外国文字,明达国际公法,因而他们对于世界各国的民风政俗、外交历史都了然于胸,例如,作为驻德大使的程天放在未出使德国前就已多次发表公开演讲论述德国历史,并盛赞德意志人民好学深思,坚忍沉寂。另外,岳谦厚先生曾对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中重要外交官领事官的学历结构进行考察,经统计,86名外交官领事官中留学国外者高达73人,约占总数的84.88%[18],这足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人才选拔上相当偏重留学国外经历者。因此,在急需办理外交事务,迫切需要外交人才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即使开始任用其党内要人担任使节,办理外交,也仍是优先考虑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又精通外国语言、且具有良好素养的人士。

表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驻外公使及大使教育背景一览表
(二)有针对性的确定具体人选
在驻外使节的政治任用情形中,南京国民政府常针对某国具体情形决定使节人选,其特以其党内某位政要专驻此国,办理外交,更多体现的是“专人专用”的外交原则。例如,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任命蒋作宾为驻日公使,乃是因为其自济南惨案时便洞悉日人之残暴与野心,并极力主张对日交涉。至1931年奉召回国,途径东北三省,见日本军人气焰更为嚣张,蒋作宾乃 “至南京向当局力言,对日交涉之不容忽略,并建议仿德对俄例,速设中日交涉委员会”[19],而国民政府也试图以外交路线消弭在东北的危机,因此以其充当公使,设法补救。另外,据与刘文岛相识、并曾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工作过的汪正本回忆,刘文岛在德国时常到法国巴黎度周末,并在玩笑场合中结识了一位意大利朋友,而此人正与意外长齐亚诺有深交,经其牵线搭桥,刘文岛与齐亚诺结识并取得联系。因此,刘文岛在中、意间积极活动,并条陈蒋介石“亲德不如先亲意”,主张效法法西斯衣钵。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蒋特调刘出任驻意公使,积极活动,以增进两国邦交。
而驻苏大使杨杰,在未获大使职位之前,就曾赴苏联进行军事考察,其归国以后更时刻关注苏联情况,并特意学习俄语。1937年更是率领军事代表团,赴苏洽谈苏联对华物资援助事宜;其后继任驻苏大使的邵力子,一直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一贯主张对苏友好,时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与苏方人士多有接触,是合适人选。”且其“1926年曾以‘友好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受到斯大林接见,与苏方领导人联系比较方便,有助于争取苏联对华援助。”[7]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特以二人出任驻苏大使。
三、外交使命
整体来看,自1931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是较为复杂与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虽于国内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不断,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亦百废待兴,这使其亟需进行工业及国防建设,从而增强国力,同时镇压国内各反对势力。国际上,中日两国关系较为紧张,其后两国间战争亦是全面爆发,这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围绕对日关系而展开,除需极力谋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冲突外,为抵御侵略,亦急需争取列强援助。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些以政治身份充任使节、办理外交事务的军政要人往往带有国民党政府所赋予的特殊外交使命。
例如,为更好地进行国内各项建设,南京国民政府亟需借鉴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之经验,因而程天放、张乃燕、贺耀祖等人带有观察与研究所驻国家状况,以供中国取法之特殊任务。程天放在赴任前便表示:“德国在欧战后之环境,较我现时尤劣。但历时仅十余年,其国势之蒸蒸日上,几已恢复战前之强盛,其民族精神之伟大超卓、艰苦奋斗,殊足为吾人效法。本人此去,当时彼邦情形详为介绍,并将吾国实情,随时向友邦宣扬。”[20]而驻比公使张乃燕在担任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时,就曾赴法、比考察,此次荣获公使头衔,更是受令利用赴欧履新之机会积极考察欧洲各国的建设事业。另外,驻土公使贺耀祖也坦言,其出使土国带有三项积极研究之目的:一、土国介于共产与法西斯两主义中间,何以能够不偏不倚,屹然树立自己的文化中心;二、土国政治上形似独裁,及一党专政,何以议会仍能够继续存在活动;三、土国的经济建设,为日无多,何以能够达到经济复兴的途径,提高了一般国民的生活水平[21]。贺耀祖更表示此去土国必将实际研究之结果,随时供给国内各有关机关与团体,以作参考。正是带有此种特殊任务,他们在返任归国时,常常就其调查研究结果发表演讲或报告,以供借鉴。例如,程天放归国后谈及他对德国人的认识一节时,将德国国民做事切实、严守纪律等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还表示在此最危险最紧要的生死关头,德国国民性之优点应成为今日中国的“他山之石”。
在谋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冲突方面,蒋作宾一直积极主张对日交涉,并谋求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亦期望通过外交路线消弭东北的危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特以蒋作宾为驻日公使,令其持节东行,缓和中日间的情势。而为了改善双方紧张关系,蒋作宾在日也是积极活动,多次与日本外相晤谈,其外交努力甚至被误认为亲日行动,遭致不满。
正是鉴于国内外各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急需列强之经济及军事援助,为更好地办理求援事务,乃特以刘文岛等人充任使节,并密令其向驻在国积极交涉,以期顺利获得援助。例如,针对日本不断侵华,刘文岛特奉蒋介石命着意增强中、意两国关系,以期获得意大利的帮助,而在刘文岛多方活动下,意大利也确实积极援助中国的国防建设。据刘文岛回忆,中意关系升格前后,“有义(意)人空军顾问之效忠吾国,有义(意)人秘密海军顾问之效忠吾国,有义(意)人财政顾问之效忠吾国,有义(意)国以工厂设备贷助吾国:在四川南川海空洞建立吾第一空军制造厂。”[22]除此之外,中国还派有数百位陆海空军警察、航空机械学员、文学生等,前往意大利学习文化与技术。程天放在赴任前,也曾专门前往成都谒见蒋介石,聆听其关于中德邦交的指示,其出使德国的重要任务即在于增聘德国军事顾问及大量采购德国军火。杨杰在担任驻苏大使时,“蒋介石给杨杰布置的任务是:最高目标为 ‘促进苏联参战,即是促成中苏互助条约’,最低希望为‘俾苏方源源接济我军用物品’。”[4]为使其完成任务,蒋介石多次拍电杨杰令其就军事援助事与苏方洽谈,杨杰也始终与苏方积极接洽,成功的完成了任务。据统计,其共争取到苏联2.5亿美元的对华援助。其后,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逐步停止,南京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苏联援华,认为必须积极促进两国邦交,从而首先需要改派真正对苏友好者继任大使。在此情形下,邵力子被特任为驻苏大使,继续担负起向苏联求援之重务。邵力子更是直接表示他在呈递国书后,便马上 “忙于接洽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中国“当时急需的是飞机。 ”[23]
这些被特殊任命的驻外使节虽被赋予了种种重大的外交使命,但其出使结果却往往不那么令人满意。有如蒋作宾、程天放等,受所驻国外交政策之影响,无法真正促进两国邦交,外交活动难以开展,最终不得不匆匆回国。蒋作宾坦言经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政纲日益不振,军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无人敢负责解决中日之事,其四年心血付诸东流,最终返国。程天放亦是如此,因德国调整其远东政策,逐步放弃中德传统友谊,开始弃华亲日并做出承认伪满、停运军火等一系列损害中国政府利益及中国人民感情之事,中德关系开始恶化,作为驻德大使的程天放在外交上“无事可做”,只能被迫请辞归国,程天放对此结局亦表示始料未及。另外,也有因自身缺乏相关外交经验与训练,主持外交工作时手段生疏且状况频出,最终不得不被召回,甚至成为外交界笑柄者。例如,驻比公使张乃燕在任期内就常闹笑话,“一次,张访比国国务总理,至于认错了人,被比京某报披露出来;一次,比王之丧,因张不知带通过证,致为警兵所阻,席次座位亦被撤。”[24]更有甚者如驻苏大使杨杰,他曾对苏联国防部长表示:“在中国,他的职责是服从蒋委员长,但是在苏俄,他的责任是听从并永远追随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于杨杰此种大胆言行,顾维钧便表示:“这也是派一个完全外行的军人到国外去当外交代表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 ”[25]
四、结语
综上,南京国民政府直接以政治人才来充任使节,办理外交,既是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做出的特殊任命,也是国民党“党义外交”的具体体现。这种特殊任命既能使南京国民政府行之有效地推行其外交政策,又打破了北京政府时代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舞台的惯例,从而构成了外交人事上的重大突破。从现代外交的视野来看,这一变化其实是现代外交的发展趋向。因为外交是国家内政的延续,一国的外交也始终要为其国家制度及代表此制度的统治阶级服务,这决定了外交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工作,“政治第一”也始终是所有国家选拔外交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外交工作还是一项事务性、技巧性极强的工作,外交事也从无小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些被特殊任命的驻外使节,往往缺乏专业的外交知识,在外交博弈的舞台上亦缺乏相关技巧,因而主持外交工作时常感吃力,外交生涯也就较为短暂,不得不画上遗憾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