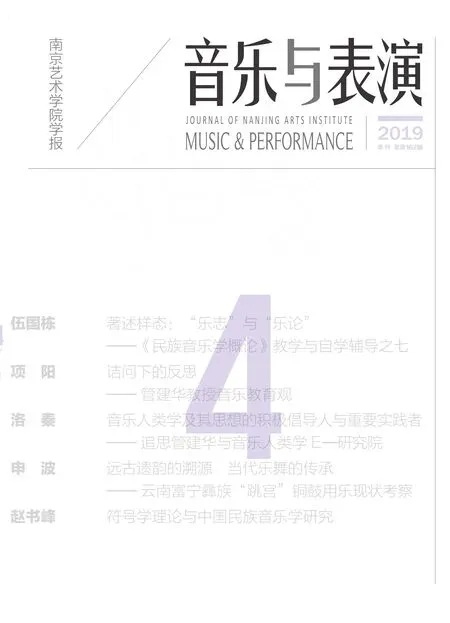“秧歌”的渊薮与汉族民间舞的文化体征
于 平(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1986 年10 月,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会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在沈阳组织召开了“北方秧歌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上述两个部门主编的内部刊物《民族民间舞蹈研究》编辑了《北方秧歌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陈冲《秧歌研究的坚实一步》作为专辑的“代序”指出:“关于什么是‘秧歌’,大家认为存在两种概念:一种是广义的,即把汉族年节中的‘舞队’统称为‘秧歌队’,把‘舞队’的活动称为‘闹秧歌’或‘秧歌会’;因此,‘舞队’中的节目、形式都可以泛称为‘秧歌’……另一种是狭义的,即专指在民间舞蹈中哪一种是‘秧歌舞蹈’……研究这种狭义概念的‘秧歌舞蹈’,就不能为当地的习惯称呼和习惯概念所约束……经过讨论,对北方秧歌的特征和属性,有了一个初步的但比较明晰的概念轮廓……有的认为应着重从舞蹈形态上来看,认为‘北方秧歌’的共同特征主要是一个‘扭’字,或者是‘扭、唱、逗、耍’的综合表演。这是面宽一些的看法。有的认为除形态特征外,还应加上表现程式上的特征,一、具有广场民间舞队的表演特点;二、具有固定的表演规范——如歌舞并举、大小场结合;三、具有各种人物、扮相——如领舞者(伞头、老杆、膏药客等)和其他属于生、旦、丑等行当的角色;四、具有结构上扭、逗、唱的特色。这是面窄一些的看法……”[1]2-3显然,我们对“秧歌”的探讨首先是指向狭义概念的“秧歌舞蹈”;进一步说,我们还认同这个概念中“面窄”一些的看法,即“除形态特征外,还应加上表演程式的特征”。
一、“秧歌”是汉族民间舞的根脉所在
为什么要举办“北方秧歌”的学术研讨会?因为“秧歌”是我国北方的民间舞,基本上是北方的汉族民间舞。鉴于当年的“民舞调查”涉及“214 种不同形式的秧歌舞蹈”和“包括约700 个左右的秧歌节目”(参见上述陈冲文),我们的探讨要择其硕、择其特而论一一从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作为“传统舞蹈”的“秧歌”入手。所谓“国家级非遗名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下称“非遗法”)的一个立法内容,即“国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个“国家级非遗名录”,自2006 年-2014 年,公布了四批共1372 项;其中“传统舞蹈”类约占10%左右,有131 项。列入“国际级非遗名录”的“传统舞蹈”,明确称为“秧歌”的共有13 项:它们是山东的鼓子秧歌、济阳鼓子秧歌、阳信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河北的昌黎地秧歌、乐亭地秧歌以及居于河北地块中的北京小红门地秧歌;山西的临县伞头秧歌、原平凤秧歌、汾阳地秧歌;陕西的陕北秧歌和辽宁的抚顺地秧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通过“秧歌”的考察,旨在把握汉族民间舞的文化体征;因此不列入作为满族民间舞的“抚顺地秧歌”。与考察的目的相关联,未标明“秧歌”的“海城高跷”,作为“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舞蹈”,其实也就是“海城高跷秧歌”(也即我们常称的“辽南高跷秧歌”);它是我们今日“东北秧歌”的一个直接文化根源。因此,对汉族民间舞视域中的“北方秧歌”,我们可以分四个文化区块来把握,它们分别是齐鲁文化区块(山东地区的秧歌)、燕赵文化区块(河北、北京地区的秧歌)、晋陕文化区块(山西、陕西地区的秧歌)和关东文化区块(主要是“辽南高跷秧歌”)。为什么要通过“北方秧歌”来把握汉族民间舞的文化体征?因为“北方秧歌”主要播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正是汉民族得以融聚并凸显的发祥地。相传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交锋并逐渐交融后,在黄河流经的中原一带形成了统一的华夏部落,此后中原地区的先民便以“华夏族”自称。“华夏族”是汉民族的根脉所在,所以至今仍称“炎黄子孙”。后来的尧、舜、禹、汤,作为历史的延续其实也是两大部落在不断交融中的不断交锋——尧、禹代表着黄帝族裔的诉求而舜、汤体现着炎帝族裔的主张;到有周一代“武王伐纣”,自称“我姬氏出自天鼋”的周族,明确标榜是黄帝族裔再一次的文化整合。这一次更为加固了华夏族群从血缘到疆域上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后来被尊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这种血缘认同和疆域维系(由黄河流域“流”成的经济模态)的内在要求;但真正的文化认同的实现,是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至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才逐渐清晰的。随着汉王朝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先进性凸显和影响力扩张,王朝的国民对外宣示为“汉人”,同时也被域外族群所指认。汉族作为一个硕大族群的形成,与汉王朝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而从其华夏族的历史根脉来看,本身亦有“舍氐羌而无华夏”之说,此时更是与东夷族、百越族文化交锋与交融的结果。
二、齐鲁文化区块“秧歌”的“推、拧、抻”
考察作为汉族民间舞根脉所系的“秧歌”,我们从齐鲁文化区块入手。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重要源头之一。它有两个历史文化高峰:一是东夷史前文化,即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二是春秋战国时期,鲁、齐两国先后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产生了诸多文化巨子,仅被后世称圣者便有孔丘、墨翟、孙武、孟轲等。也就是说,齐鲁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来认知之前,在此地发生的儒学,事实上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开放地融汇各家学说,历两千年而不衰——不仅从未发生断裂,甚至也从未出现次生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主体性和凝聚力。但既称“齐鲁文化”,其文化就有齐、鲁的差异性:齐都临淄一带既具有沿海工商文化的特点,也具有内陆农业文化的本色,被认为是一种海陆兼备的“重合边缘文化”;邹鲁地区及其毗邻的西部平原,是内陆的延伸,农业发达,与黄土文化相连相通。就这一地域的“秧歌”文化体征而言,“海阳秧歌”和“胶州秧歌”属于前者,各类鼓子秧歌属于后者。
同是山东的秧歌,“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更贴近齐文化的体征。如果说,鼓子秧歌的突出特点是“跑”不是“扭”,那胶州秧歌的突出特点恰恰是“扭”——胶州秧歌女角的动态甚至有“扭断腰”的俗称。胶州秧歌主要在胶县流传,张浔、魏三多曾以《“三弯九动十八态”浅析》为题,论述了胶州秧歌女角的动态特征。文章写道:“女角的演出在胶州秧歌中占主导地位,有翠花、扇女、小嫚三类人物……翠花是壮年妇女,动作开朗大方;扇女是少妇形象,动作温婉淑静;小嫚是年轻女孩,动作活泼俏丽;但她们有共同的特性:比如姿态上的‘三道弯’,动作时的缓行快收,以及力量上的推、拧、抻等。在运动的全过程中,她们始终要保持腰、胯、膝三个部位具有适当的弯曲度;头、胸、大臂、小臂、手、腰、腿、膝、脚等九个部位同时向不同方向作弧线运动;而九个部位的左右两侧又有不同的动向和运动……由此构成‘三弯九动十八态’的动态特征”。文章以“翠花扭三步”的主干动作为例,强调“每一步动作开始先用‘推’劲(包括手推和脚蹬),在‘推’(蹬)的同时让两膝、腰胯向反方向扭拧……全身的扭拧力感延续下去,就出现一种‘抻’的力感,直达舞姿造型的各部位……(这一动作)在节奏变化上慢行快收,也即身体各部位推、拧、抻过程速度较慢,占一拍的四分之三时值,而收势须在四分之一拍时值中完成……”[3]95与之相关联,同处胶东半岛的“海阳秧歌”也贴近齐文化的体征,这在鞠春山《海阳秧歌初探》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文章写道:“海阳秧歌素有‘大架’与‘小架’之分。前者指舞姿、造型具有武功架式,后者指动作自如的即兴表演。人们多喜欢前者。代表海阳秧歌风格特点的也正是流行在凤城、东村、城阳、盘石一带的‘大架’秧歌……舞队由乐大夫在前领舞;依次是一对霸王鞭、一对花鼓、一对舞扇;然后是渔夫与樵夫一对、货郎与腊花一对、相公与闺秀一对、锢炉与王大娘一对、丑婆与傻小一对……海阳秧歌舞蹈动作的特点:一是节奏动律讲究‘起步踩点,出手赶点,扭转迎点,收在重点’;以‘十字步’为基本步伐,以手在胸前左右上下的摆划为基本招式……二是人物动态讲究个性——如腊花和王大娘,同是以舞扇为基本动作,但前者是村姑,扇不离胸半遮面,表现出少女的羞涩;后者是农妇,运扇过顶大闪腰,突出其泼辣性格……三是男、女对舞中的配合,讲究‘男右女必左,交错需擦背;对脸分高低,迎送有进退;聚散多照应,回转找核心’。”[4]65-70
三、燕赵文化区块“秧歌”的“拉骨抻筋”
由齐鲁文化区块西行,我们需要考查的是燕赵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燕赵文化主要是指古冀州、今河北的文化。在地理学家眼中,绵延的燕山、巍峨的太行架起了河北的脊梁;蜿蜒的长河、浩渺的大淀润泽着广袤的平原,提供着鱼米之养;而在历史学家眼中,从秦统一至清末的两千多年来,燕赵大地战争频繁,行政区划亦随着王朝的统一、分裂而分合聚散。也就是说,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内部的差异性可能大大超过统一性。就地貌的形态类型而言,今日之河北可分为坝上高原区、冀北山地区、冀西北间山盆地区、冀西山地区和河北平原区。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昌黎地秧歌”“乐亭地秧歌”均属于河北平原区。就燕赵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言,最初与生存资源的争夺密切相关。黄河中、下游一带广布水系,且又交集着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部落之间为生存资源的争夺就在所难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促成了一种剽悍的民风并积淀为族群性格。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和“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都发生于此,当然战争的结局是促成中华民族进一步的交融与增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燕赵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同族群文化的异质碰撞和深度交融。
关于河北的“秧歌”文化,黄济世与王月玲两人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在《论地秧歌》一文中指出:“地秧歌最普遍的主题是表现爱情。在封建礼教和旧的道德观念桎梏下,这个主题是以‘调情’和‘逗趣’的方式间接反映出来的。丑角是地秧歌表演中的核心人物,他在鼻梁中间涂上一个白色豆腐块后,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抒发感情,明确表达对异性的追求。‘看秧歌,就看逗,没丑没逗没看头’……”[5]82-83进一步说,该文总结了地秧歌在表现形式上的显著体征:“一、灵活、自由、应变性强;在相对稳定的传统形式中,表演具有极大的任意性……配合默契的即兴表演是地秧歌产生戏剧性效果和抒发激情的主要手段……扭起秧歌来犹如用整个身体在‘说话’,就像冀东人说话那样,绘声绘色,生动感人。二、舞蹈动作把表情、手势、哑剧融合在一起,丰富多彩,运用自如。地秧歌在不同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扇花与动作之间的配合上……是靠艺人的技艺、靠‘小法儿’来完成动作之间的转换和达到动律、节奏、力度、重心方向上的协调自如……三、动作强调全身各部位的有机配合,主要由肩、胯、膝、手腕这四个部位的特殊形态构成它独特的‘味道’……四、形成地秧歌独特韵律的主要因素还有:身体各部位动律上的差异(动律差)、节奏上的差异(节奏差)、身体各关节和肌肉的控制和张弛、动作的反作用、以及在运动过程中对力度的改变起决定作用的呼吸和运气等……”[5]82-83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肩、胯、膝、手腕这四个部位的特殊形态构成的独特“味道”,如文章具体描绘道:“首先,肩的运动和变化最活跃、最鲜明……调动身体各部位的功能,是靠内心节奏起支配作用的;而地秧歌内心节奏又多是通过肩的动作变化和肩部肌肉的灵活运用来突出体现的——不论是端肩、错肩、绕肩、抖肩、转肩、扯肩,都是为了表达人物的内心感情,那种耐人寻味的情趣也是通过肩的变化来显示的。其次,胯的运动和变化也非常丰富生动。无论是提胯、掀胯、坐胯、转胯、绕胯、拧胯、蹶胯、错胯、揉胯,都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单一的运动,而要求有一种由里到外的肌肉感觉和反作用,用艺人的话来说就是‘拉骨抻筋’……再次,膝部屈伸运动是通过脚掌为支撑点和原发力的一种节奏性很强的弹性起伏,膝和脚掌的配合使全身的感觉犹如在跳绳一样,又似骑马和坐轿那样美滋滋、飘飘然……最后,手腕的转、翻、扣、塌和手指小关节交替辗转是控制扇花变化的关键……地秧歌扇花的多变和难度在汉族民间舞中佼佼者。它的握扇方法是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交替灵巧地配合,再结合手腕的力量做各种翻、转、端、抖、颤、克、开、合的动作;使扇在周身上下团团飞舞,同身体姿态融为一体,成为表达细腻感情的重要手段。”[5]82
从历史文化着眼,我们把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北京小红门地秧歌”也视为燕赵文化区块。作为北京“秧歌”的代表,我们可以通过丁良欣、董敏之《北京秧歌浅谈》一文来加以把握。文章开门见山:“北京古称幽州,自元代起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幽州地区从古以来就是中原与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经济联系及文化交流的桥梁。”这其实也是燕赵文化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关于北京的“秧歌”,文章指出:“秧歌是北京民间花会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花会’解放前叫‘走会’‘过会’‘杂耍’‘玩艺儿’,‘花会’这个名称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以前,北京民间的‘走会’分文、武两种:‘文会’是不表演的,在‘走会’活动中给茶棚和寺庙提供一些物质或服务……‘武会’在‘走会’中进行表演,又分‘会规以内’和‘会规以外’两种,行话叫‘井字以里’和‘井字以外’的。‘井字以里’的‘会’有‘幡鼓齐动十三档’之说,这‘十三档会’按顺序排列是:一、开路(即飞叉);二、五虎棍;三、秧歌(分高跷秧歌和地秧歌);四、中幡;五、狮子;六、双石头会;七、石锁会;八、扛子会;九、花坛会;十、吵子会。秧歌排在第三位。为什么这‘十三档会’算‘会规以内’的呢?据会中老人讲,是因为它们表演所用的道具都是由娘娘庙里的一些设备和器物发展演变而来的……”[6]5而关于北京“秧歌”的表演特点,文章归纳道:“一是动作整齐,潇洒大方,刚劲有力,节奏鲜明。基本动律非常明快,既‘扭’又‘跳’,既‘哏’又‘跳’,既‘哏’又‘俏’;脚下踩地要有力,抬腿双膝像弹簧,既有韧劲又有了弹性,在紧凑的节奏中扭着前进。二是人物个性动作突出,性格鲜明;而这些个性动作又是弹性,在紧凑的节奏中扭着前进。二是人物个性动作突出,性格鲜明;而这些个性动作又是在共性动律中发展的,因此风格十分统一。如每一对人舞表演的‘起范儿’,均由‘骑马蹲裆式’发展而来……三是吸收了戏曲表演动作之长,将其发展、融合在地秧歌的动律之中。如渔翁的‘捋髯’‘甩髯’‘吹髯’,都是吸收戏曲表演动作,又按地秧歌的节奏风格加以发展……从以上三种表演特点中,可以看到北京‘秧歌’具有北方秧歌扭、逗、耍、扮、唱的共同特征:‘扭’是指基本动律。以腰部的扭动带动双肩的前后摆动与脚下‘进退步’‘十字步’的结合;膝部稍有屈伸,节奏有缓有急,情绪热烈时全身自由扭动,膝颤带肩耸,活泼开放。‘逗’是指表演技能。如‘武扇’或‘膏药’与其他人物的‘逗场’表演,要会逗趣调情,诙谐幽默;动作细腻,眉目传情。‘耍’是指不同道具的运用。如锣、鼓、棒、鞭、扇、绢等,每个人物都要有自己耍动的方法。‘扮’是指各种人物的扮相,都有一套传统的脸谱和服饰要求。”[6]10
四、晋陕文化区块“秧歌”的“走、摆、扭”
我们所提及的晋陕文化区块,历史上主要是三晋文化。周代分封,建晋国于汾水之滨;晋人开土拓疆,逐渐占据山西大部,故山西自古便简称“晋”。至战国时三家分晋,韩、赵、魏统辖山西全境及相邻地区,“三晋”遂成为山西的别称。历史学家们认为,三晋文化中的“晋南”,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也即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和主要根系。“三家分晋”的战国时期,儒、墨盛于鲁,道家聚于楚,兵家出于齐,而“三晋”则与法家、名家、纵横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韩非便是三晋之中韩国的公子;以公孙龙为代表的明辩之士(名家)则是赵人;以张仪和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专事口舌,通过游说诸侯来追逐功名,以至《史记·张仪列传》直言“三晋多权变之士”。当然,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出生于赵国的荀子,他以超群的学识吸收百家之说,建立起博大宏富的思想体系。关于三晋文化还必须提及两点:其一,作为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部,这里在不同民族文化冲突中逐渐实现民族和解,民族文化交融成为三晋文化的一个主旋律。其二,“经商至上”成为晋人普遍遵奉的准则,由此而形成了三晋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如节俭朴实,富而不奢;精明机巧,经营有方;以义制利,讲究信誉;以及顽强开拓,应时而变,等等。
属于晋陕文化区块“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秧歌,就山西而言有“临县伞头秧歌”“汾阳地秧歌”和“原平凤秧歌”。乔瑞明《概述山西民间舞蹈——秧歌》一文对此多有介绍。比如提及“伞头秧歌”,文章说 :“伞头秧歌是以歌为主的秧歌,主要活动于吕梁山区的临县、柳林、离石等地,其中尤以临县最为盛行……在临县较大型的一班秧歌队,表演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仪仗队——由若干彩旗和标有秧歌队名称的门旗组成;二、乐队——由锣鼓家伙及唢呐组成;三、伞头——伞头一手持伞(伞的边沿缀以红绫),一手拿‘虎衬’(俗名‘响环’),是秧歌队的指挥(‘伞头秧歌’亦因此而得名);四、拉花子与打鼓子——这是秧歌队的基本队伍……‘拉花子’也叫‘包头’,身穿彩衣,腰系百褶裙,肩披花绸斗篷,头上插花,左手拿绢,右手持扇……‘打鼓子’的腰挎花鼓,扮相为农村男青年,分为‘文鼓子’和‘武鼓子’……前者舞动幅度较小,轻松潇洒;后者舞动幅度大,气势威武。在一定场合表演时,男角‘打鼓’,女角‘戏鼓’,加之‘扇公子’(丑角)组成一架‘鼓子’……五、由旱船、竹马、狮子、龙灯、高跷、大头娃娃等传统的民间舞蹈和民间武术组成……六、文会子——一般由3-5 人表演带有简单情节的民间小戏或传统戏曲中的片段……还会表演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小歌舞、演唱和活报等……临县伞头秧歌的表演,一是突出伞头的唱;二是突出拉花子和打鼓子的‘扭’;通常扭时不唱,唱时不扭,二者交替进行。”[7]19又比如提及“地秧歌”,文章说“汾孝地秧歌是以舞见长的秧歌,它因流传于吕梁地区的汾阳、孝义而得名……汾孝地秧歌分为以舞为主的‘武场秧歌’和以唱为主的‘文场秧歌’,一般唱时不舞而舞时不唱。每一班秧歌队由15 人组成:其中4 个女角手拿镟子(小锣),身着戏曲中小旦装束;4 个男角双手各持一根长约30 厘米的枣木花棒,武生扮相,着英雄头冠;另有4 个男角身被长33 厘米、直径15 厘米的花鼓与腰间,身穿戏曲中丑角的青装,头戴尖顶毡帽。12 名舞者敲击各自的乐器,随着花棒一张一弛、时上时下轮换舞动……与场外的一面锣、两副铙钹和谐配合,形成一种紧锣密鼓、重锤急敲的场面和氛围。”[7]20还比如提及“凤秧歌”,文章说:“凤儿秧歌是流传在忻州地区原平县北贾村一带较为稀有的秧歌,亦名‘份儿秧歌’;它与‘踩圈秧歌’‘轱辘子秧歌’组成一个表演整体。第一部分‘凤儿秧歌’,主要用于‘过街’和‘大场’时的表演。整个队伍由水镲指挥;表演队由野太医和疯公子(或傻小子)、领头,后随4-6 对男女青年及丑婆。男角戴一种特制的竹圈帽子,帽子用细竹条盘旋制成,丈余长的竹条末端缀一红绒球,盘在帽子正顶中心,竹圈则可以伸缩;男角还腰挎花鼓,手执鼓锤,双手轮换击鼓时伴以上身有节奏地前俯后仰,使头顶的竹圈有弹性地甩出、弹回……竹圈不时地伸、缩、晃、摆、绕圈,形成了一种慢慢悠悠、颤颤巍巍的舞蹈韵味;女角左手拿小锣,右手持锣签,边敲边舞,头部随身体或扬或俯,胯部亦随之扭动,与男角在行进中交错向前……第二部分‘踩圈秧歌’,是在‘凤儿秧歌’把场子打好后进行表演的,主要是演唱……第三部分,‘轱辘子秧歌’,是继‘踩圈秧歌’之后表演的具有人物和一定情节的小戏……”[7]21需要提及的是,山西民间舞中的“踢子鼓秧歌”也是极具影响的,特别是其最具特色的“拔泥步”;但鉴于它未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此不赘述。
属于晋陕文化区块的还有“陕北秧歌”,其在北方秧歌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自明的。据海海《陕北秧歌概述》一文介绍:“陕北秧歌是以舞为主的一种群众自娱性广场集体表演的民间歌舞活动,长期流传在陕北黄土高原(主要包括榆林、延安两个地区的25 个县)……陕北秧歌分布区域很广,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的南部和延安地区的北部山区;其中以榆林地区所属的绥德、佳县、清涧、子洲、吴堡等县,以及延安地区所属的子长、延川、志丹、吴旗、安塞、延安、甘泉等县为主要区域。榆林地区南部以传统的民间秧歌为主,延安地区北部山区则是‘新秧歌’比较活泼;但二者基本表演形态、风格以及律动特征则完全一致……陕北秧歌每逢春节进行表演活动。表演时参加人数不限,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秧歌队在会长的组织下从农历正月初七左右开始活动,俗称‘起秧歌’;在过去,传统秧歌队成立后,要先到当地(或附近)的庙里敬神,俗称‘谒庙’。其后的第二天,秧歌队开始挨家逐户拜年,俗称‘沿门子’;‘沿门子’结束后,则进行村与村之间的互访互拜,俗称‘搭彩门’;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秧歌闹到了高潮——这一天从秧歌队的踩大场以及各种文艺节目——一登场献技献艺,一直到夜晚全体群众的‘转九曲’……至此,春节‘闹秧歌’活动基本结束。”[8]52除前述“谒庙”“沿门子”(又称“排门”)“搭彩门”“转九曲”之外,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还有“扭大场”“小场子”和“闹灯彩”,这都是北方秧歌均有的表演形式。文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陕北秧歌舞蹈特点”的阐述:“尽管陕北各地民间秧歌的扭法和步履不尽相同,但‘扭’‘摆’‘走’是其基本的规律和特点。正如秧歌艺人所说:扭秧歌讲究‘走得要轻巧,摆得要花哨,扭得要活泛’。一是关于‘扭’。‘扭’是陕北秧歌动律变化的关键……要将秧歌扭得活、扭得美,首先要抓好人体腰、胯部位的运用和变化,使腰胯随着音乐节奏左右扭动自如,做到力度、幅度有机的和谐统一……二是关于‘摆’。‘摆’是‘扭’的延伸……摆动要以肩、胸带动双臂和双手,有大摆、中摆、小摆之分,亦有上摆、下摆、平摆之别。榆林北部秧歌属‘大摆’,有时双手摆动比肩高,形象粗犷舒展;南部米脂、佳县、绥德等地区的秧歌属‘小摆’,双手多在腹前左右摆动划圆弧形,给人以欢乐、活泼之感;还有部分地区的秧歌属‘中摆’,双手架起大臂与肩成平行状,然后摆动小臂和手腕,其形象生动有趣,稳健幽默……三是关于‘走’。陕北秧歌粗犷豪放的风格,主要是通过‘走’来表现——‘扭’是在‘走’的基础上发展的,而‘摆’则是在‘扭’的节奏上将基本动律加以美化和夸张……陕北秧歌的基本动作变化和形象塑造,皆是从基本的‘走’开始的:‘三进一退步’是在向前行进中步履节奏的变化;‘二进二退步’是‘走’的过程中一种幅度和力度的对比;‘十字步’则是在原地踏步基础上加以美化而形成的。人们在表演秧歌时,通常是从‘走’开始的;随着节奏的起伏、情绪的高涨,逐渐增加律动变化的力度和强度,把‘走’发展为‘跑’,发展为‘跳’,并进而发展为‘转’……”[8]54
辅导员是学生“第二课堂”的直接组织者与引导者,辅导员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开展好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第二课堂”。可通过“每日品读”,将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日常行为规范等融入早自习,以学生讲、展、评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文化、学习理解文化,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可开展“全民学习、全民阅读”计划,鼓励学生多走向图书馆,走进书籍,走入文化;可开展“中国梦.礼仪行”,形成人人知礼、人人行礼的校园文化氛围等。
五、关东文化区块“秧歌”的“稳中浪”
对“北方秧歌”的关注不能没有“东北秧歌”,但目前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东北秧歌”,就汉族民间舞而言只有“海城高跷”。事实上,“海城高跷”也即“海城高跷秧歌”,它是“东北秧歌”的直接文化根源,也是关东文化区块的汉族代表性“秧歌”。在中国古代史上,定都于陕西的汉、唐王朝,通常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近代以来的“关东文化”,因山东、河北两地“流民”的“闯关东”之举,而将山海关以外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一体的地域文化称为“关东文化”。论及关东文化的特征,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一地域独特的人口构成:其一,古代多民族的共居相融与人口的流动,形成了文化形态的流动性;其二,山东、河北“流民”潮水般的“闯关东”的行为方式,造成了文化形态上的融合性;其三,以俄、日、朝鲜为主流的多国移民的迁入,产生了文化形态上的变异性。由上述人口构成而逐渐生成的关东文化,其精神特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古代“尚武”精神的遗风。“尚武”精神作为关东文化的根本,首先在于险峻的自然环境的砥砺以及在其前提下形成的“精于骑射”的生产方式的演练,当然后来也因为各族之间屡屡征战的军事斗争的搏击。二是近代勃兴的“开发精神”。这包括力辟榛莽的土地开发精神、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精神和启迪民智的文化开发精神。三是寒带黑土意识的深层积淀。这种意识包括质朴、粗犷、豪放、带有野性的性格,以及因得天独厚而靠天吃饭的依赖心理。四是求“大”尚“侈”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由辽阔广大的生态环境所陶冶的,从“大锅乱炖、大盘码菜、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宴饮便可略见一斑。五是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这与清初、中期禁止汉文化传入有关,当然更是近代以来东北实业开发精神的内化。
考察关东文化视域内的“东北秧歌”,英力《辽南高跷与东北秧歌》一文说得比较透彻。文章写道:“人们习惯把辽宁的秧歌冠以‘东北秧歌’之称,这既反映了事实又不十分精确。其原因可能与五十年代东北人艺歌舞团以‘辽南高跷’为素材,改编、创作了一台名为《东北大秧歌》的节目而广传开来有关……由于辽宁的‘东北秧歌’主要是在‘辽南高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从‘辽南高跷’入手,才可以了解‘东北秧歌’的一般特点……辽南高跷按传统习惯常由七幅架(14 人),多者八副架(16 人)组成。常扮的人物有头跷、二跷、丑公子、青蛇、许仙、白蛇、肖恩、肖桂英、傻柱子、老㧟,余者皆扮成上装(旦)和下装(丑),上装和下装的最后一对俗称‘压底鼓’——他们在大场表演中和变换速度、‘叫鼓’时,起指挥乐队和统一演员动作的作用。‘叫鼓’是由音乐‘鼓谱’沿用的术语,完整的舞蹈术语称为‘叫鼓亮相’。‘叫鼓亮相’是辽南高跷独有的一大特点。顾名思义,即‘叫鼓’是为了‘亮相’;这种‘叫鼓’有一至五鼓等五种,每种‘叫鼓’的最后一拍都要‘亮相’……尽管称谓是统一的,但具体的‘亮相’因地、因人及表现内容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使辽南高跷除‘扭’之特点外,又平添了风格各异的‘叫鼓亮相’,从而拓宽了表现生活和表达人物感情的手段——包括各种‘回望相’‘单指相’‘扣腰相’‘展翅相’‘搭肩相’等造型,还有在每段舞蹈中突然穿插出现的‘愣神’‘卖俏’‘挑逗’‘躲闪’等一闪即逝的小舞姿造型,或者在各个段落之间及每段情绪转换处所使用的相对较为静止的各种小亮相动作。由于‘鼓谱’较长,从‘叫鼓鼓’到‘亮相鼓’之间的‘过程鼓’,就可以为舞蹈动作的发挥提供充裕的时间……可以说,每一‘叫五鼓’的结构,就是一段较为精彩的动作组合。”[9]63
接下来,文章论及东北秧歌动律特点和“扭法”特点。文章指出:“有人说东北秧歌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很容易掌握;其实也有较难的方面,那就是对风格、韵味的掌握。必须把几个主要部位的动律特点先弄清楚,扭起来才能形似神似。一、腕的动律特点。由于原来高跷的上装、下装经常是借助扇、帕、鼓、棒、板、小袖等道具来完成动作,素有‘浪在腕上’之说……其特殊动律为‘腕是主导,臂是配合,臂与腕走,腕带臂动’……必须做到腕是臂动的前导,甚至给人一种只见腕动不见臂张的感觉。二、腰的动律特点。这个‘腰’指的是胯上肋下的部分。乍一看,扭秧歌时好像腰和全身一起动作,其实它是‘扭在腰眼上’——即每一步都要突出腰的主导作用。要做到上身挺拔,必须要用腰来带动,上身才能显出既不乱晃又呈自然摆动状,决不能故意突出胯而造成臀动。三、肩的动律特点。肩的动作在东北秧歌里也比较丰富,如单抖肩、双抖肩和交替抖肩等,必须把肩练活,能上下自如才行……四、膝的动律特点。膝的屈伸可以归纳为‘顿屈伸’和‘柔屈伸’两类:前者要求脚抬起时要形成向后抽踢势(脚呈自然状),同时另一腿膝部要顿挫鲜明地屈伸一次,见棱见角……后者从节奏上看是屈、伸时值相等,同时要求屈伸的线条圆润并略带韧性……”[9]65-66文章在论及秧歌“扭法”特点时说:“‘扭’是秧歌动作的通俗称谓……在诸多‘扭法’中,‘交替里挽花’的舞法(双臂动作)和‘后踢步’的步法(双脚动作)的结合,应视为东北秧歌的基本扭法……其基本要领是:臂松弛,腕有力,腰先摆,脚后踢,身要稳,微提气。这十八个字再概括一下,实质上就是要掌握好‘稳中浪’三个字……‘稳’在表情上的要求是似笑非笑、含而不露;在动作上的要求是‘出脚步要匀,双臂不呼扇,步法有力感觉轻,臂活全靠腕子功,上相微动似未动,全身都在音乐中’。‘浪’在表情上的要求是‘风流潇洒,眼能传神,笑会说话’;在动作上的要求是‘脚有韧劲,臂有弹力,抖肩、晃身做得哏,闪腰、愣神逗得俏,鼓相、亮相有风韵,显得锣鼓也有调’……归根到底,‘稳中浪’就是东北秧歌动律美的高度概括。它不仅仅是对秧歌‘上装’扭法优劣的评价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东北劳动群众所持有的审美情趣和心理情态。”[9]65-66
六、秧歌“大场”世俗情趣后的“象数结构”
无论是哪个文化区块中的秧歌,其主要的表演都是在“跑场”之中(“行程”的动态已包含在“跑场”之中或者可以说是“跑场”的预热),而“跑场”的表演又主要分“大场”和“小场”两类——前者是整个秧歌舞队在领头的带领下,跑出各种“场图”;后者则是由上装(旦角)、下装(丑角、有时还有生角)表演的带有简单情节的“二人场”或“三人场”。观众历来有“大场看阵,小场看逗”之说。实际上,相对于吸引当下观众的“小场看逗”而言,“大场”跑出的“场图”才积淀着更深的文化意蕴。这一点,张华《秧歌“场图”与宇宙象数》一文做了深入的研究。文章指出:“秧歌场图,很少静态摆出,大半是流动的轨迹;在舞者足下,随舞者的流逝而展开。所以,于旁观者几乎是不可直观。有图谱,艺人能绘之,舞者心中共同默记。届时,伞头率领,舞队鱼贯而行,循谱式跑一图算一场。一般秧歌队都能跑上十数场,场场翻新。各地场图不尽相同,搜集起来,浩如烟海。无论就其图式的丰富,还是就其图式内在结构的精致与系统,秧歌场图,皆无疑堪称世界民间舞中一大奇观……是什么因素,促使秧歌不厌其‘繁’地去创造场图,以致形成了如此发达的场图奇观?为何跑大场,会被当成秧歌的精魂所在?”[10]46通过研究,张华认为:“浩若烟海的秧歌场图中,其最大的部分显然与中国民间庄户日常生活的事象物象,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比如豆角蔓、编篱笆、双蒜辫、线框子,等等,形象概括又传神,象形表义,更配上泥土气浓郁的名字。这类场图往往各地有各地的创造,互不雷同,总括起来,自然最具量的丰盛。习惯了反映论的思维,很直观地就易从这里得到充足论据,说明秧歌场图是对庄户日常生活的反映……然而有些深层的问题并未就此得到合理解答。为何秧歌场图浩若烟海却博而不杂,各地在其基本构成方式上竟如此一致,并有相当部分场图在所有的地方反复出现?如果说这种近乎体系化的蔓衍有某种内在规律从中统取,那么这规律是什么?它们又从何而来?……因此,了解‘法儿’,知悉秧歌场图那些内在的基本的讲究,应当更重要些。”[10]48
在进一步的分析后,张华发现:“跑场图,为了不乱阵脚,流畅好看,当然要有讲究。这些讲究,各地大体相同。如:一、要讲规矩,成方圆。跑出的图案通常是外要圆,内要方;转角要圆,交叉要方。方,层次才分明,不拖泥带水;圆,运动才流畅,不滞涩唐突。二、因为要圆,行进路线的转角处,就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小圆圈流转。每个小圈,常被称为一个‘菠花’(山东叫法)。跑菠花的技巧,有人概括为‘定桩替位’。定桩,指转折点由伞头确定。伞头定桩而后转奔向新的路线,后来者须相继追随伞头,过其所定之‘桩’而后转向新方向,如此一个追一个,就叫‘替位’。定桩替位,跑出了‘菠花’,使直线的冲击化解于圆曲,使图式的变化处得到强调,使场图的履行井然有序。三、大半的场图显示出严谨的对称平衡。四、跑一个场图必须一气呵成。图谱中给予每个伞头的路线均是一笔到底。很显然,秧歌场图的内在讲究,原本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着一脉相承之趣。大约正是从这里,场图获得了展开去的自然规定……可是,别忽视了根性的问题。在那些反复出现于各地的基本场图中,有相当一些是在一个主题下呈现系列化发展的,比如‘四门’的系列、‘八卦’的系列,按数序排开的系列,等等。从场图本身的图式进行研究,还将发现,其由简而繁的衍生亦相当系统化,这里面当然还另有规律的……恰恰是在这点上,当事人亦茫然不知。‘民日用而不知’,深深地承担着某种文化蕴奥,却并不自知这种蕴奥,莫非更是文化深层之味?”[10]49-50由此,张华开始破解秧歌场图的“象数结构”了。他从古老的“圆圈场图”入手说:“一个单纯的大圆圈,可以说是最古老最常见又文化积淀最丰富的舞蹈场图,其意义远非美学范畴能全部囊括。它大约起源于原始的篝火舞蹈,也许仅仅因围着篝火自然形成。然而,一旦有了拜火意识,一旦地上的篝火与天上那周流运行……的天火——太阳发生了联系,成了太阳的一种象征……它可能已是日之圆的象征,是宇宙运行的象征……一个古老的圆圈场图能够如此寓意深远,一个展开的象征性场图符号系统,又将如何呢?以‘圆’为母题,在秧歌场图中,有围着‘火塔塔’的篝火舞式之圆;进而有了更普遍的‘卷白菜心’,单纯的围绕之圆中引入了向心周流又回旋而出的意绪;再进一步,一个伞头变成两个伞头,周流回旋成了两个相反相成的要素的互动——由这些场图联想到的阴阳二气的宇宙观,绝不会是牵强附会。阴阳摩荡,回旋往复,天地运行万物消失无不在其中。这种意会也许早就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生成了。早在它得到理念表述之前,它就有意无意地在各种各样的感性形式中不断浮现?”[10]51
张华进一步认为:“秧歌的场图,除了其直观的‘象’,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东西——构造一个场图的菠花的‘数’。每个场图菠花的‘数’,和一组系列化的场图中各场图菠花之‘数’间的关系,往往直接影响着对场图命名的吉词……菠花的‘数’与菠花连接的不同方式所造之‘象’,共同构成了秧歌场图内在的象数结构。其‘象’,同场图之名呼应;其‘数’,使各场图的象与名被有序地组成一个祝福意义系统……秧歌场图的象数结构,并非只零星地为支撑某个一般性的祝福意义系统而设,也并非仅解决着场图生成过程的自律机制问题;事实上,它是要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宇宙的象数结构形成同构呼应。场图自身的生生不息,仿佛是应和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造化之道本身;场图系列的象数秩序,总也暗暗扣着一元二仪三才四象五方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的天地象数秩序……的确,秧歌场图象数结构的意义,就是要通过同构呼应,象征性地进入天地造化的结构中去,企求达到参造化谐阴阳和人神的目的。因而实际的操作过程,就是亲身投入去履行场图的轨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并无太高直接观赏价值的场图,人们却总是不求其解地偏将它视为秧歌的‘精魂’,并总在其中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和力气……综上所述,尽管秧歌充满世俗欢乐情趣,尽管秧歌场图绝对有许多纯粹世俗的、即兴的创制;但是,秧歌场图最基本最必然的东西,应是植根在参天地谐阴阳和人神的文化精神中的,应是同农耕信仰的祈禳祭仪态度紧紧纠缠在一块儿的,应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来历的。”[10]52-54在此文中,张华提出了史籍中“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的“履迹”之说,认为:“秧歌跑大场无非是‘履迹’的另一种说法”;这让我联想起许慎《说文》释“礼”为“履也”——这个“履”不是作为名词的“鞋”,而是作为动词的“践”,是“履行”或者“实践”。这也是“秧歌跑大场”的文化底蕴。
七、秧歌“小场”情、逗、丢、气的表演模态
如果说,秧歌大场的“场图”潜隐着传统文化的“象数结构”;那么小场的“场趣”则紧贴着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在大场的“热闹”过后,观众更期待的是小场的“情趣”。许多小场,取自戏曲的片段,往往是戏曲精粹“折子戏”中更为“点睛”、更具“一招鲜”的绝活;但这类尤为看重现编现挂(紧贴当下、紧贴现场)的小场,也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了规律化的“场趣”模态,这在辽南高跷秧歌中表现得较为完备。英力《辽南高跷秧歌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分析说:“辽南高跷秧歌的‘二人场’,是一‘上装’、一‘下装’为一组表演爱情的单场。智慧的高跷艺人在常年演出实践中,创造了大量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构成生动的‘二人场’。一些有经验的艺人,尽管从未合作过,但只要一说下‘情场’或下‘逗场’,再简单约定一个路子就可搭配下场;下场后主要靠即兴表演和临场发挥。因而使这些本来就各有特色的‘二人场’,更突出了风格情调以及舞蹈语汇上的千差万别。”[11]129通过“简单约定一个路子”便可“搭配下场”,如同民间戏曲表演时的“幕表戏”,说明秧歌艺人已通过常年的演出实践,建立了与观众互动的表演模式,或者说形成了一种表演程式——英力在文章中为我们介绍了四种“二人场”的表演模态(我认为称“模态”比“程式”更为贴切),这其实对我们民族舞剧中主要叙事手段的“双人舞”也是大有启迪的。
首先是《情场》。文章指出:“通常是用慢板开始,以抒情的曲调、稳重的动作,抒发着各自的内心情愫和相互的爱慕之情;速度由慢转快后,情绪逐渐高涨,感情步步深化,场面愈加火爆——两人动作配合默契,无论是搂腰转、切身、掏灯花、对望以及各种‘鼓相’、小亮相,皆做得纯熟流畅,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两人感情交流得自然,无论是扯襟、碰肘、拉手帕、推搡以及各种拍、指、闪、望、娇羞、媚眼等小动作,无不含而不露、落落大方……给人以和谐自然的美感。”[11]130其次是《逗场》。英力说:“这属于诙谐型的爱情场,但绝不是男会逗、女会撩的双双都在逢场作戏的‘恶作剧’。一般说它在人物性格刻画上与《情场》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对有情人多属性格开朗、感情外露型;他俩活泼中含诙谐,温情中见泼辣,诙谐而不轻薄,泼辣而不放荡;喜怒哀乐情绪起伏变化大,转、跳、扭、相的舞蹈动作变化多;浪起来动作有神儿,逗起来风格有哏儿,场面上气氛欢腾而不喧嚣,安排恰当得体……给人以健康、轻松、活泼的幽默感。”[11]130
文章介绍的第三个“二人场”是《丢场》。《丢场》“是表现一对小夫妻逛庙会或赶集,由于留恋商贩摊铺的南斋北味,或贪看琳琅满目的金银首饰,不觉被潮水般的人流冲散,于是演成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寻觅戏’——两人东瞧瞧、西望望、南顾北盼;男的急得直跺脚,女的愁得干搓手;你丧气,我懊悔,正在惶惶于绝望之时,一转身忽然(一身冷锤),两人撞了个满怀,于是眉开眼笑双双并肩而去。《丢场》的情节中心是个‘找’字,但两人同在一台转却碰不着面;所以表现得越急、越慌,就越引人发笑,耐人寻味……”[11]130关于第四个“二人场”《气场》,文章写道:“这是描写一对青年情侣的假纠葛——佯装生气的情节。《气场》表现小两口约好去赶集或逛庙会,一大早女的兴致勃勃地先走到院内,在一系列的望天、摸鬓、抻袖、提领、掸襟、看鞋等整装动作后,男的仍磨磨蹭蹭出不了房门;于是女的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并意图要报复……果然,待男的出门来招呼时,女的扭脸旁观不加理睬,和甩帕顿足表示责问——一个好‘上装’在这里常常能表现出‘怒’中含有几分娇嗔,‘气’中露出几层疼爱;‘下装’表演配合更富戏剧性,明知对方假生气,偏装成认真的样子赔着小心、看着脸子、百般自责;终于,女的掩面一笑解决了矛盾。这是‘单《气场》’。‘双《气场》’则表现男的在几番相劝之后不见成效,便用‘激将法’,也假装生气的样子,把头扭向另一边;实则两人都在用窥探的动作摸出对方的虚实。几经周折之后,或男的沉不出气,或女的失去耐性先赔出笑脸,最后两人同时运用‘掩面一笑’表示和解……”[11]130-131“二人场”的表演有许多相应的曲牌如《柳青娘》《大姑娘美》等供选择,而艺人选择的曲牌与其舞蹈的搭配,情绪的渲染都十分默契,以至于让人感觉所表演的舞蹈就是依据所选择的曲牌编排的。这种状况其实也与包括“二人场”在内的秧歌“小场”的总体表演特征有关,即“小场”表演虽有简单情节,但重在借事言情,以事逗趣,用事宣舞。
八、近代汉族民间舞是宋、元以后一种“畸形发展”的结果
可以认为,“秧歌”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汉族民间舞,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汉族民间舞的文化体征。在诸多对此加以研究的文章中,王元麟的《汉族民间舞蹈几个特点》一文(载《舞蹈》1987 年第4 期)是最为深入的。在切入正题之前,王元麟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当宋代的新儒学——程朱理学产生后,从孔孟之道发展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同时强化了‘宗法制’的社会制约机制……‘灭人欲’首先就是去男女情欲,要求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而‘宗法制’则起着监督作用。这样,古代桑间濮上‘男女会聚’的民间舞蹈就难以存在了……再加上女子被裹为小脚,自给自足经济的家庭分工使女子固定在家庭纺纱织布;那种人人能自由跳的、体现男女感情交往的‘民间舞’就逐渐从社会消失了。事实上,宋代以后,我国大部分人(主要指汉族——引者)也就不再会跳舞了。但是,舞蹈作为一种人体运动的审美表现,却又不是能完全被消灭的;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汉族民间舞蹈,大都是宋元以后一种挣扎的畸形发展的结果。”[12]7王元麟的这种“基本判断”隐含着“民间舞蹈”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其重要动因在于“男女会聚”,而这的确是许多少数民族舞蹈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因此,王元麟自认为所论“汉族民间舞蹈特点”是“宋元以后一种挣扎的畸形发展的结果”。
在此前提下,文章谈到了汉族民间舞的六个特点,现摘要如下:“一,其表现形态披着宗教迷信外衣,联系着祭祖、迎神、求雨、祈丰收、治疾、逐鬼之类仪式,图形也常是联系着走四门、踩八卦、转九曲之类。大都在宗教性节日演出(春节闹元宵也是源自道教上元节),这是宋以后汉族民间舞蹈所能争取到的一种存在方式。二、半自娱半表演性。不是完全的‘男女会聚’的自我娱乐,具有表演性质,因而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舞’(Folk Dance)。但又不是专业剧团的演出,也含有自我娱乐性……舞者虽不是专业的,但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常有师徒承继和家传性质。这使得汉族民间舞蹈具有较高的技巧性。三、由于具有较多的表演性,舞者常联系着大众熟知的故事表现许多生动的人物,形成了民间舞蹈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特征。许多民间舞蹈是分行当的,这是世界各国民间舞所不具有的……四、许多表演经常男扮女装……民间舞蹈本来就具有男女情感维系与交往的调节功能,而‘男扮女装’正是我国特定封建社会下的畸形表现。五、人体美的体现受到抑制。宋以后妇女开始广泛地裹小脚。自然人体美、特别是表现具有女性特征的人体美,被看作伤风败俗;女性人体大多被裹在层层装饰着亮片、描金、飘带、绣花的舞服之中。六、普遍使用道具。汉族民间舞蹈从云南花灯到东北秧歌,几乎离不开扇子、手绢。外国民间舞蹈也有使用道具,但只是一种装饰而不规定动作……花鼓灯的‘兰花’去掉扇子、手绢,许多动作就失去了意义;西班牙舞(弗拉门科——引者)也有拿扇子的,但换掉扇子不影响动作表现……汉族民间舞蹈常常是通过对道具的运用来表现感情,而对人体自然美的表现却是次要的……以上特点都是由特定的中国封建社会诸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作为人民创造的形式,也正是一种历史的美的积淀。它是封建时代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情感的体现。它特定风格动作的美,它的表现方法将会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存在而存在下去;但是它又不可能是完全形态意义的存在,而更多是作为一定的基因遗存在各种新形式中。”[12]7-8应该说,王元麟对于汉族民间舞蹈的认知是深邃且具有前瞻性的。
九、秧歌作为“村田乐”源自祈年的“御田祖”
作为汉族民间舞蹈最为重要的构成方面,秧歌是汉族农耕文明在乐舞文化中的积淀与体现。这不仅因为“秧歌”从名称上就暗示着与农耕生产的某种关联,也不仅因为它在汉族分布的广大区域中普遍存在,而且因为它所积淀的文化心理所张扬的人生情态,都与汉族农耕文明相契合。“秧歌”一词,最早可能见于南宋诗人陆游的《时雨》,诗曰:“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秧歌长……”尽管诗中的“秧歌”并非后来作为一种民间歌舞、或作为一种综合表演艺术形态的“秧歌”,但却道出了这个名称的本源,即与农耕生产,尤其是与插秧劳动紧密关联。请看以下几段史料:清·吴锡麟《陕南巡视目录》载:“陕南西乡县沙河镇田间农民有系彩于首扮戏装者,歌唱舞蹈,锣鼓喧天,盖为插秧助兴,俗名‘秧歌’本此。”清·姚燮《今乐考证》中有“山歌”条,在摘录前人有关论述后加按语道:“按今又有秧歌,本馌妇(往田野送饭者)所唱也。《武林旧事》元夕舞队之‘村田乐’即此。江浙间扮诸色人跳舞,失其意,江北犹存旧风。”清·李调元《南越笔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槌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谓之‘秧歌’。”《巴川直隶志》载:“春田插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鉦于垅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和,纚纚可听,使耕者忘疲,以齐功力,有古‘秧歌’之遗。夏耘亦如之。”《帝乡纪略》载:“泗州……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湖南晃洲厅志·风俗》载:“岁,农人连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拔……疾徐前却,颇以为戏。”
上述史料,北起陕南,南至南越(粤),东自江浙,西到巴蜀……由此可见“秧歌”是整个汉族分布区、或曰以农耕生产为其主要谋生手段的汉族分布区普遍存在的民间歌舞文化;同时可见“秧歌”本身的内涵十分丰富——有馌妇所唱,有妇子群歌,有歌郎迭和,有农人为戏……但总体而言,“秧歌”的发生,其时在插秧季节,其地在垄上塍间,其人为农夫馌妇,其意为插秧助兴;而其结构:必击鼓为节,必更唱迭和,亦有“联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拔……疾徐前却”的舞蹈。
如果对“秧歌”一词的考索确实不会早于陆游,那我们就自然会追问:南宋之前难道就没有与农耕生产密切关联的民间歌舞活动吗?如果有,那么何以相称?清·项朝棻在《秧歌诗序》中已点明:“秧歌”即南宋民间舞队中的“村田乐”,说“秧歌”是“南宋灯宵舞队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花和尚、花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妇、装态货郎。杂踏灯街,以博观众之笑。”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谈到灯节之际的“村田乐”,说:“斗野年丰屡,吴台乐事并。酒垆先叠鼓,灯市早投琼……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映光鱼隐见,转影骑纵横。轻薄行歌过,癫狂社舞呈(原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乐),街市管弦清(街市细乐)……旱船遥似泛(原注: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旱船’),水儡近如尘(水戏照以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舞”和“村田乐”,正是今日“秧歌”一词之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前者指“秧歌会”,是节日歌舞活动的统称,如陕西《米脂县志》所言:“春闹社伙,俗名‘闹秧歌’,村众合伙于神庙立会……由会长率领,排门逐户,跳舞唱歌,悉中节奏,有古乡人傩遗风。”后者则指“秧歌舞”,是指上元之节日歌舞活动中的一种形式,如《京都风俗志》所言:“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
元·朱凯所著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第二折中有模仿“社火”的表演,曰:“禾旦云:‘伴哥儿,我打从东庄里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吹的吹,舞的舞,擂的擂,不是我聪明,我一般般都记将来了也!’正末云:‘伴姑儿,我恰才打那东庄头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我也都学它的来了也。’禾旦云:‘伴哥儿,我不曾看见,你试学一遍者。’正末云:‘试听我说一遍者。(唱)【叨叨令】那秃二姑在井口上,将辘轳儿(气笛曲律的)搅。’……正末唱:‘瞎伴姐在麦场上,将那碓臼儿(急并各邦的)捣。’……正末唱:‘小厮儿他手拿着鞭杆子,他嘶嘶飕飕的哨。’……正末唱:‘那牧童儿便倒骑着一个水牛呀呀地叫。’禾旦云:‘俺庄家好快活也。’正末唱:‘一弄儿快活也么哥,一弄儿快活也么哥!’禾旦云:‘俺庄家五谷收成了,甚是安乐。’正末唱:‘正遇着风调雨顺民安乐’。”从其“搅辘轳儿”“捣碓臼儿”“拿鞭杆子”来看,正是“村田乐”的内容。其实,作为与农耕生产相依存的民间歌舞文化,“秧歌”最初不是为插秧者助兴而是祭祀田祖以祈丰年的活动。明·刘世瑞有诗曰:“秧歌唱共趁霄晴,客岁中秋夜月明,我道祈年还祝雨,入春阴雨最宜耕。”这种祈年的活动,早在《诗经·小雅·甫田》中便有记载,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这里说得很清楚,“琴瑟击鼓”的“农夫之庆”,乃是“御田祖”的;而“御田祖”又是为了“祈甘雨”“介稷黍”和“谷士女”。这种民间的祈年活动被规范为一种礼仪,即古已有之的“蜡”礼。如《礼记·郊特性》所载:“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伊耆氏即神农,说神农“始为蜡”,可以看出 ,“蜡”礼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蜡”作为“郊之祭”也体现出与“御田祖”的某些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帝尧之时有壤父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击壤”之讴,可能是后世“秧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渊源。
十、“秧歌”名称的北上及其义涵的泛化
关于“秧歌”源流的考索,薛亦冰《秧歌源流辨析》一文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文章指出:“要探讨‘秧歌’的历史源流,不能不涉及各种类型的‘秧歌’。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各种类型的‘秧歌’,更不是被泛称为‘秧歌’的各种民间歌舞艺术,而是‘秧歌’的一种类型,即至今仍广泛流行于北方农村乡镇的歌、舞、戏综合形式的一种传统秧歌。在这类‘秧歌’中,以‘陕北秧歌’‘冀东秧歌’‘东北秧歌’(包括‘辽南高跷’)、‘胶州秧歌’‘胶东秧歌’等影响较大,其表演形式和音乐在同类秧歌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秧歌中的各种节目,按其艺术形式可归纳为歌、舞、戏三类:其中的‘歌’是指穿插于舞蹈之间用于清唱的民歌小曲;‘舞’一般包括‘过街’(队列舞)、大场(图案舞)和丰富多彩的‘小场’表演;‘戏’是一种有人物有情节,歌、舞、说、做兼备的代言体民间歌舞小戏。秧歌的歌、舞、戏诸艺术形式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对独立。其‘相互统一’表现为:有统一的组织形式——秧歌队;歌、舞、戏诸节目均由秧歌队员统一分工兼任;有一套特定的表演程序等。正是在‘统一’的意义上,歌、舞、戏不同艺术形式的联合才有了特定的体裁意义,构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艺术整体,因而我们才把这类‘秧歌’作为汉族民间歌舞艺术中的一个独立品种。其‘相对独立’表现为:歌、舞、戏诸形式的各个节目之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并无本质联系,基本上是不同内容、不同艺术形式的各种节目的混合穿插表演。三类艺术形式中,尤以‘歌’同‘舞’(这里主要指独立的舞蹈节目,不包括小戏中的舞蹈成分)联系最少。舞蹈时不唱,歌唱时不舞,这是自古就有的传统形式,所谓‘舞毕乃歌,歌毕更舞。’从各艺术形式之间‘相对独立’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又可把‘秧歌’看作是三种不同艺术形式在同一组织内(即‘秧歌队’)和同一名称下(即‘秧歌’)的一种联合体”。[13]123-124这段分析很重要。它使我们更清楚了传统民间舞蹈“载歌载舞”的特征并非全指“歌舞同步”,而是有着“舞毕乃歌,歌毕更舞”的“歌舞穿插”形态。这也使我们把“秧歌舞蹈”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得以成立,并大有深意。
《秧歌源流辨析》一文有专节辨析了“秧歌舞蹈的来历”。文章指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被称作‘秧歌’的舞蹈,当然也同插秧劳动有关……从今天各地秧歌的舞步来看,基本上都是表情作用下一种自然步态的夸张,完全看不出同‘插秧步’或稻田劳动有什么联系。舞蹈的动作、舞者的道具以及表现的内容等,基本上都同劳动无关。因而,不必因名附意,将秧歌舞蹈同稻田或者插秧劳动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从有关秧歌舞蹈形式的早期记载中去寻找秧歌舞蹈的来历,也许更为可靠一些。有关秧歌表演的较详细的记载,见于较早的有清人杨宾《柳边纪略》一书,书中记述了约康熙年间黑龙江宁古塔表演秧歌的情形,所谓‘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嘎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旁边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而已。’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当初秧歌舞蹈的表演形式、人物和道具等,同田间劳动并无关系,而同有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却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此外,清代文人曾有‘秧歌即南宋《村田乐》’之说。南宋灯宵民间舞队中的《村田乐》,其表演形式现已无从确定;不过直到明代仍有这一名目,据朱有燉《黄钟醉花阳》散套‘贺贺贺,一齐舞起《村田乐》’所说,明代的《村田乐》大概是一种舞蹈。清人将‘秧歌’同《村田乐》联系载一起,反映了清代秧歌舞蹈有可能继承或吸收了《村田乐》的某些因素。从以上各种现象可以看出,清代出现的所谓‘秧歌舞蹈’,实际上是在广泛吸收古代各种传统舞蹈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应该说,古代多种传统舞蹈是秧歌舞蹈的源头,秧歌舞蹈是多源的汇聚。”[13]126-127对于文章的这段辨析,其实也大有可商榷之处。其一,以黑龙江宁古塔表演秧歌的情形来辨析“秧歌舞蹈的来历”,路径上可谓“南辕北辙”了。因为“秧歌”作为最典型的汉族民间舞蹈,主要播布区和可能发源地都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地区,出现的秧歌舞蹈乃是“闯关东”的关内移民输入,必然发生“因地制宜”的变异——这种变异以“地秧歌”向“高跷秧歌”的转变最为显著,其原因也是很值得探究的。其二,说“古代多种传统舞蹈是秧歌舞蹈的源头”,不能排除、甚至可以指认南宋的《村田乐》也是秧歌舞蹈的主要源头。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帝尧之时的“击壤”之讴,有周一代的“田祖”之御,应该与今日的“秧歌”文化都是一脉相系的。
实际上,该文中“秧歌的流传与变迁”一节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文章指出:“秧歌由以得名和形成的重要因素是稻田‘秧歌’;因而,秧歌产生并流行的主要区域应该是大面积栽培水稻并盛行稻田‘秧歌’的稻作生产区……然而,从现状来看,正是在不种水稻的北方广大地区秧歌最为盛行;南方稻区虽仍流行着稻田‘秧歌’,但作为节日歌舞形式的秧歌却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会出现稻田‘秧歌’同歌舞秧歌的地理”分布不相一致的这种异常现象呢?这需要从秧歌兴起之后流传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去找原因。秧歌初兴之时,主要是流行于南方稻区的。从康熙以后的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广东、湖南、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等地表演秧歌的记载,可以秧歌早期在南方的普及面是相当广泛的。至于后来秧歌没能在南方继续繁荣发展,恐怕有以下一些原因:其一,明朝发迹于江南,清人必然对江南诸省严加防范。在清政权取得初步稳定之后,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可以允许秧歌这一新兴的民间艺术的存在,但当秧歌在南方各地真正兴盛、成为一种广集游人聚众观赏的艺术活动时,就必然遭到统治者的警觉和干预。康熙以后江南一些地方官府以‘秧歌有伤风化’为借口,曾多次颁布法令查禁秧歌并残害秧歌艺人,从而遏止了秧歌在南方的进一步发展。其二,‘秧歌’这一名称在南方稻区原有特定含义,即特指插秧时所唱之歌;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或者更有可能是为了避当局之嫌,即使它在节日娱乐场合发展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也难免会改名易姓或隐姓瞒名。再者,南方自明代就盛行的‘花鼓’‘花灯’等许多艺术形式早已发展成熟,‘秧歌’节目自然会被其吸收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13]130-131这种说法有点勉强的是,为何清政权在南方查禁“秧歌”,却又能放任“秧歌”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北方盛行?而事实是,许多南方的民间歌舞如“花鼓”,传到北方反倒称为“秧歌”。清人袁启撰《燕九竹枝词》云:“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说凤阳。”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在满清统治者眼中,将汉族主要聚居区“南方”的民间歌舞在大概念上都称为“秧歌”。因此在其入关后,为了发展“柳边”经济而向关外大量移民屯垦,这些与汉族移民同行的民间歌舞自然也被称为“秧歌”。换一句话说,“秧歌”一词最初确实是针对南方稻区的民间歌舞而言的,比如南宋之时陆游的歌诗。但后来应该是被清朝政权及其文人士大夫用来指称汉族的民间歌舞,以区别其他边疆民族的歌舞。这时“秧歌”的义涵已经泛化,已经无关于那稻作文化的“插秧之歌”了。至于南方汉族仍然自称的“花鼓”“花灯”之类,可以将其类比于“秧歌”(也即汉族民间歌舞)而不必强求名称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