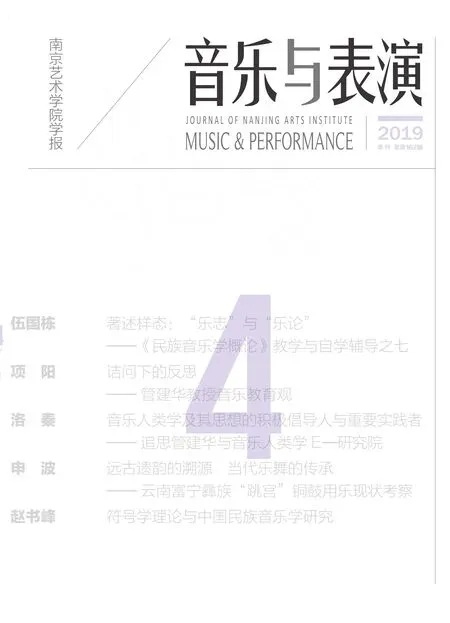从文学到影像:“中联”创业作《家》与巴金原著的比较研究①
张 燕(北京电影学院 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北京 100088)
赵 媛(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对于20 世纪的香港粤语电影来说,1953 年,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创业作影片《家》的横空出世,具有影史上举足轻重的意义。《家》改编自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次改编五四新文学的影片,尽管原定的1953 年元旦档期被不看好的院商压制延迟至1月7 日才上映,但上映之后“戏院连日爆场,售票处的窗口一直排上了长龙,蜿蜒不绝”,“收入比较元旦期中上映的歌唱片还要加倍”[1],“成功开创了粤语片的新路,是粤语片和香港电影的里程碑作品之一”[2],并一举奠定了“中联”公司作为 “香港电影光荣旗帜”的重要历史地位。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在50 年代初与香港电影产生联系,这同香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势、文化氛围等都有着很深的联系。就创作而言,尽管影片《家》力求“忠于原著”,但在原著文学框架基础上,编导还是进行了自觉地现代性改编择选,表达了因应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香港电影主体性,从而产生了有趣且有效的文化化学作用。本文旨在将1953 年电影《家》与原著小说进行细致的文本比较,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蕴藏其中的内涵。
一、“中联”成立
从1949 年底到1966 年,是香港电影业蓬勃兴起、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是香港电影史上粤语电影的辉煌年代。据统计,这一时期香港影坛总共生产了4000 多部影片,年产量平均200 多部,其中粤语片总共2800 多部,占全部产量的70%以上,国语片才750 部左右②。作为“光艺”创办人的著名粤语片导演秦剑曾把20 世纪50、60 年代的香港粤语片发展划分成“中联”成立之前、“中联”成立之后、“光艺”成立之后等三个阶段[3],尽管有些主观色彩,但客观来说,这三个分期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中联”的成立,改变了之前香港粤语片粗制滥造、唯市场化、毒素成灾的样貌,转向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进步意识、本土文化表达的优质电影生产,而随后的“光艺”则更自觉彰显了香港的都市文化与南洋市场的文化链接。因此,“中联”的成立具有香港粤语电影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一)成立背景:粤语电影清洁运动
20 世纪50 年代初,“长城”“凤凰”“新联”等电影公司相继成立,香港左派电影全面启动。这些左派电影公司的产生,深受之前三四十年代香港进步电影潮流的影响。30 年代中后期,因为抗战爆发,夏衍、蔡楚生、黎莉莉等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推动香港拍摄了《血溅宝山城》等进步电影。40 年代后半期,在国共内战的乱世格局下,夏衍、欧阳予倩、蔡楚生等进步影人再次南下香港,推出了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创业作《珠江泪》等严肃创作、反省时代、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电影佳作。
20 世纪1940 年代末到50 年代,战后复苏繁荣的香港电影因东南亚市场的供不应求,而出现了为追求利润而投机取巧的问题。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纷纷建立戏院,并投资香港电影制造业,对粤语片的需求量很大。当时很多小公司采取“卖片花”①“卖片花”,指在电影开拍前先向院商或发行商收取订金,用作电影的制作费。的方式筹备资金,一旦获得拍片基本费用后,便草草完成电影,这造成了“七日鲜”的粤语电影行业危机。面对粗制滥造、制作媚俗的创作状况,蔡楚生于1949 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关于粤语电影》的文章,“我们之勇于承认电影是‘商品’,并不等于电影是纯‘商品’……电影还应该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希望我们的粤语电影工作者能立即振作起来……希望大家能在合作之下面对现实,迎头赶上,给予广大的粤语电影观众以优秀与良好的教育意义的精神食粮。”[4]随后1949 年4 月8 日,吴楚帆、卢敦、莫康时、苏怡、李铁、黄曼梨等160 多位粤语电影工作者积极响应,联合发表《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倡导“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宣示“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愿意重新检讨,深自反省,今后加倍努力,团结一致,坚定立场,坚守岗位,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2]21
为了更好地贯彻推进清洁运动,众多粤语影界有识之士合作推出了《玉楼情劫》(1948)、《满江红》(1949)等优质影片,激活了原本比较被冷落的文艺片潮流。为继续这种“团结协作”的粤语电影理想与实践,1949 年7 月10 日,“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为“华南电影工作联合会”)宣布成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香港粤语影界团结的组织,是传播进步意识、电影理想与新文化思想的组织,成为“中联”公司后续成立的重要基础,也是粤语电影的新起点。
(二)成立动力:伶星分家
战后香港电影失去了内地的广大市场,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市场逐渐兴盛起来,当地华侨在粤语戏曲片中感受到家乡的文化,此类电影常能获得不错的票房。因此50 年代的香港粤语片常以“卖片花”的方式获取资金来源,戏曲片中的红伶成为海外市场的保障。各制片商各出奇招,采取双生双旦等“大堆头”(多明星)制作,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后采取“伶星配搭的新桥”,以时装搭歌唱,风行一时。1951 年,粤语片空前高产近300 部,文艺片、剧情片等均比较卖座,粤剧电影也大量增加,除了传统的榜黄、小曲谱曲外,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国语、粤语、外语歌曲,这些歌曲作为插曲丰富了电影内容,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因此出现了粤剧歌唱片形式。[5]大批粤剧戏曲演员涌入电影行业,粤剧歌唱片多形式简单、创作粗糙,对原有的粤语电影创作格局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在“伶”(粤剧老倌)“星”(粤语影人)合作的过程中,因为粤剧老倌的轧戏、迟到、大牌,而且片酬过高、态度傲慢、工作散漫,引起包括吴楚帆、黄曼梨等众多影人的不满,拍戏中产生了很多矛盾。正如有粤语影人所言,“为了替影星打一条出路,我们商量着集体组织一间影片公司,自己拍摄自己喜欢的电影,不受制片家的控制”[6],再加上1952 年,新加坡等南洋市场对粤语片的兴趣骤减,粤语片的海外卖埠价大幅跌落,这样原本推崇“伶星合作”、多明星、大堆头影片的院商也难以承受。于是,1952 年,香港粤语影坛出现了“伶星分家”运动,即粤剧老倌与粤语影人分开工作。
(三)成立宗旨:提高粤语片质素
“那个时期,粤语影片非常蓬勃,在产量上,可以说是战后的黄金时代,年产三百部以上,但是……因为由于产量增加并不正常,供需不平衡,相对形成了市场的困难,就只好力求制作成本的减低,必然影响到产品质量上的粗糙与简陋……眼看着粤语影片面临危机,我们为了不想辜负观众们的爱护与期望,也由于自己艺术良心的驱使,为了巩固和提高粤片的艺术水平,在群策群力之下,在社会人士和亲爱的观众们的鼓舞支持下,‘中联’就组织成立了”[7]。在“伶星分家”的背景下,吴楚帆和一众粤语影界翘楚影人,多次共商联合影界志同道合者、贯彻粤语电影理想、成立公司的主张,而后以自身的卖埠实力赢得了海外市场片商的支持, 1952 年11月,“中联”正式成立。
从1952-1967 年,“中联”延续了15 年,总共推出了47 部电影。“中联”标识上的21 颗星,就是吴楚帆、白燕、张活游、容小意、李晨风、吴回、黄曼梨、秦剑、王锵、陈文等明星演员、导演、制片人组成的21 位股东团队,也就是团结协作的象征。“电影不单是一种新兴企业,而且是一种对社会人心影响极大的艺术”,“中联” 旨在“提高粤语片的质素——艺术水平,繁荣我们的事业,并且更大力去满足观众的需求”[8],由此经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明星薪酬的合理分配,“中联”推出了《家》(1953)、《春》(1953)、《危楼春晓》(1953)、《秋》(1954)、《大雷雨》(1954)、《父母心》(1955)等众多香港粤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佳片。
(四)创业作《家》与市场状况
“中联”成立后,股东们共商筹拍创业作,经过大量资料搜集、分组审阅、合伙讨论和反复推敲,最终选择将主题积极、戏剧性强、容纳角色众多的曹禺改编巴金的《家》作为剧本。“中联”重视创业作《家》,拍摄成本约为12 万多港币,远超过当时粤语片一般3-8 万的投资规模,除了著名导演吴回,采用吴楚帆、张活游、张瑛“三生”和紫罗莲、黄曼梨、容小意、梅绮“四旦”联合主演,卡司阵容之强大,在香港粤语电影界一时无两。拍摄过程中,每位影人尽管只拿少量车马费、其余薪酬全部作为公司资本,均以“事业”之心通力合作,认真负责、反复修改提升,成就了“中联”一炮走红。尽管最初这部电影不被看好、档期从1953 年元旦黄金档延误至一周后才上映,但公映后大获成功,据统计当时在香港、九龙两地224 万人口中,有18%的居民都看过《家》①1953年《家》公映时的说明,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档案号PR605X。,“第一天收入三万四千多元,第二天比第一天更高,收入三万七千多元……据说院方跟‘中联’订的影出日期为一连八天,看目前卖座之盛,一般估计,大概会超出十五天之数”[9]。
《家》票房成功之后,“中联”成了严肃优质的粤语片代名词,一下子成了片商竞相争取的粤语片公司,不仅香港本土的院商片商由冷眼质疑转到笑脸相迎,“环球”院线率先取得“中联”电影的首映权,而且包括新加坡、越南等多个国家的东南亚以及美洲外埠均抢购“中联”电影,新加坡“国泰机构”下属的“国际发行”公司在大老板陆运涛的强力支持下,与“中联”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凡是“中联”出品的电影,“国际”均先付订金10 万元,并按照34%的比例分担影片拍摄成本。[10]由此,“中联”作为影人自发合股、兄弟班合作、资金相对拮据的公司,消除了创作拍片的资本不足等担忧,从而保障了后续《危楼春晓》《春》《秋》等粤语佳片的顺利产出。
二、电影改编:情感为核,时空集中
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是五四新文学中被改编次数最多的小说,迄今在中国电影史上已有四部,分别是:1941 年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国语版本《家》,卜万苍、徐欣夫、李萍倩等集体导演,袁美云、陈云裳、胡蝶、陈燕燕、刘琼等主演;1953 年,“中联”出品的粤语版本《家》,吴回导演,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等主演;195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国语版本《家》,陈西禾导演,孙道临、张瑞芳、王丹凤等主演;1957 年“,长城”公司出品的国语版本《鸣凤》,程步高导演,石慧、张铮、鲍方、陈思思等主演。不同版本的改编都有其侧重点,风格也有不同,足见当文学转换为电影时,如何解读和呈现与导演的创作意图有很大的关联。正如夏衍所说改编要“忠实原著”,同时他也指出:“除不同的艺术样式含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外, 主要还存在一个改编者对原著的看法(包括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和改编者的功力问题”[11]。
吴回的《家》总体上还原了原著,但将重点集中于主角间的爱情关系,以情感为内核,时空集中。影片讲述了高家子孙三人觉新、觉民、觉慧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他们在面临旧制度、旧礼教及追求爱情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策略,也呈现了与这三位主人公相关的几位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原著小说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时间线更长,如觉新成婚后经历了父亲去世、孩子出世等事之后梅表妹才重新出现,而且人物也更多,不只是对几位年轻人情感关系的讲述,更主要是对以觉慧为主的进步青年在新旧交替中的挣扎矛盾状态的描述,体现了浓浓的时代特色,而且不断地在强调时代背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而电影《家》就像是处于被基本架空的时代空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家庭内部的冲突挣扎,却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而且时间跨度小,压缩在一两年的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冲突事件一个个上演,电影明显强调故事的冲突性。全片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重在强调反封建、反礼教的主题,其实也是启蒙的精神思想。以情感为内核,时空集中,这与香港电影的商业机制有关,即使是对于强调“教育性”与“艺术性”的“中联”来说,也依然需要考虑观众,注意电影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另外,当时香港属于英国管辖,香港电影要经受港英政府的监管审查,因此“中联”进行创作时,难免会尽力淡化政治色彩。
相对于原著小说,电影《家》中的空间设定明显做了浓缩、简化处理。整部电影几乎都处于住宅内,而原著中的地点则是公馆、街道、报社、学校等多处。电影开头伴随“家”的片名的打出,高公馆的内部景象开始出现,在中国传统乐声中,一群身着旧式服饰的太太、丫鬟、老爷相互作揖,随后镜头中展现了老式住宅的景象,透过门窗阻隔,可以望见卧室中两个正在燃烧的红烛。反观原著,首章以街景展开,雪花在风中飞舞,灰暗的暮色中,觉民与觉新走在路上讨论着学堂的事情,渐渐走到公馆门前,大门的对联写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家”才正式出场。两者形成对比,电影中的主人公们直接被束缚到“家”中,困于一方之地。而原著则强调场景上的转换,从开放空间转入封闭空间,街景的生动与黑漆的大门形成鲜明比较。这点的不同,也体现出原著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因为“街头”常常代表着对自由民主的追寻,近现代史上各种重要的运动都与它有着密切联系,而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和五四运动影响的巴金更能领悟“街头”的重要意义,它象征着“革新”与“自由”。在“激流三部曲”的《春》中,也有对开放空间的描述,觉民和琴第一次提出带淑英出门参加聚会,走在街头的淑贞感慨到“我害怕,人这么多,我想回去”。[12]“街头”是一种对“传统”的僭越,对家庭束缚的挣脱。因此无论在原著、还是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的结局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觉慧告别灰暗的家庭,走向丰富多彩的街头。
电影对空间范围的缩小,也是从对整体的内容进行考量。比起巴金所处时代的矛盾尖锐性和当时思想上的活跃度,电影的创作背景则相对平和得多。巴金自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创作《家》时,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他就像小说中的觉慧一样,生活在传统封建的家庭之中,他在写《家》的过程中,大哥自杀身亡,这些都给巴金带来冲击,激起他对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愤怒,所以我们在原著中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作者对时代的控诉以及更细腻深刻的内心矛盾与挣扎。电影拍摄与原著创作已相隔大概二十年,时代和地域上都有差异。“中联”的影人们选择将五四新文学进行改编,更看重的是原著中所体现的反封建精神和教育意义,对于民族国家和政治立场的思考则相对较少。此外,当时大多数香港观众的教育程度较低,因此电影会选择尽量对原著进行简化,集中于相对单一的空间中,用化俗求真的方法,更简单直接地来讲述故事。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花园”常常作为重要的空间,如《牡丹亭》中“人立小庭深院”,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与了断瓦残垣”。深深庭院内似乎永远发生着或缠绵或浪漫或伤感的事情,在景色的烘托下,回忆过往。“一切景语皆情语”,花园为情感的抒发和寄托提供了场所。《家》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提及这部作品时,一般常常将重点锁定在它的批判意义和革命精神上,但实际上,《家》也带有相当多的传统小说元素,其实也包含了对往事的无限追忆,讲述着流连于花园中的青春男女的忧伤爱恋。小说中有很多对心理的描写,巴金在自传性的书写中,花园成为承载记忆与体察传统文化的空间。当觉慧走进花园后,他的心态常会发生转变,内心被私人化的情感占据。他在花园中遇见鸣凤,憧憬着自己的爱情;在花园中追悼悲痛,愤恨着礼教制度。梅与觉新在花园中重遇,为两人的爱情悲剧哀伤。鸣凤茫然伫立在湖畔,心里充满无处倾诉的哀怨,纵身一跃的声音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
电影《家》中主要有三场出现在“花园”。第一场在枫影婆娑中伤感的梅自怜诉说痛楚,“就好像一场梦,我又来到这里。就像以前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池塘,一样的荷花,但现在什么也没我的份了。”之后,她唱道“重游故地,痛心事已非。记双双嬉戏,花荫柳下诉心事”。充满古典韵味的唱腔和歌词,增添了电影的抒情性与诗意。当然,“歌唱”形式应该也与当时香港电影的“泛歌唱化”有一定联系。第二场是令人悲伤的一幕,绝望的鸣凤来到花园,凝视着湖面,他人的脸庞浮现在波动的水中,各种声音响起。伴随着雨与雷,无路可走的鸣凤只有跳水自尽。这部分在小说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而影片则是发挥电影语言,借助蒙太奇,以具象化的外部场景与声音来展现鸣凤内心的焦虑无望。第三场是替鸣凤出嫁的婉儿蹲在湖旁,一边为鸣凤烧纸,一边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湖畔成了伤心无奈人的常驻地,见证着一个个被压抑的生命。电影中并没有呈现那段在花园中的美好时刻,没有烟花,更没有欢乐。比起巴金对花园的复杂情感和记忆追溯,电影的创作者们对花园的态度则相对简单直接,更多是将花园作为事件发生地,丰富电影的空间,另外也多少借助花园的景色来渲染气氛。
与此同时,花园也并非完全是负面情绪的承载地,也包含了美好时光。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对花园进行描绘,也表达出他对花园的留恋,这里也曾有过欢聚,“他们忘记了琐碎的现实。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于是全沉默着,沉醉在回忆中……烟火的确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像彩虹一样,点缀了这年长的一代人的生活”。此时花园的身份便转化为一种充满“凝聚力量”的庇护所,是对旧时光的温存。
三、电影人物:多种形象对比、反派人物强化
电影对原著中众多角色选择了剥离、简化,主要选取重要人物,强化角色上的正反派对立,这使得影片可以在138 分钟内将故事讲得更清楚,也更加强调戏剧冲突。无论是原著、还是小说,都包含了很多角色,各类人物的生活追求与精神面貌各有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原著中的人物比起电影更为庞杂,除了高家的主要家庭成员和佣人外,还包括觉慧的同学朋友、琴的女同学等。比如剑云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有不少对他的描写,忧郁胆怯真诚谦逊,他与觉民一样深爱着琴,但却只能永远做一个旁观者。在电影中,这个人物是缺席的,并未在觉民和琴之间再添加“第三者”。
原著中,觉新作为长子不得不承担家庭重担,在身份限制和性格原因下,他几乎永远选择妥协退让,成为弟弟口中的“懦夫”。觉新一直秉持着“作揖主义”与“无抵抗主义”,希望借此能够将《新青年》的理论同他们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直到最后才发现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觉新无疑是新旧时代中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但在骨子里却难以摆脱大家庭与旧制度的约束,他的顾虑与责任感使他时常处于两难境地。书中这样描写他的分裂感:“他变成了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他是一个暮色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在心理和行为上,形成了鲜明的新旧对比。电影中的觉新形象就相对单一了些,似乎永远一幅温吞老实的样子,对家庭的安排和家长的指挥,即使内心是反对的,却还点头接受,永远是家庭冲突的调和剂,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电影中饰演觉新的演员吴楚帆,他与三位著名粤语片男演员张活游,李清和张瑛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戏路很广,他将一个隐忍软弱无奈纠结的形象演绎地生动贴切。比起原著中的双重性人格,电影中的觉新明显更容易屈服,整体上也更加循规蹈矩,和弟弟们的反叛大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哥觉慧作为原著中着墨最多的角色,最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在“囚笼”“沙漠”一样的家中深感压抑。他将过去的坟墓封闭,不断提醒着自己“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一直醉心于思索与抗争,提倡人道主义,却在一些瞬间察觉到自己同样处于矛盾的境地。当觉慧得知鸣凤将要嫁给冯乐山,立刻冲出去寻找鸣凤,想要为自己的忽视赎罪,然而寻找未果,经过一夜的思索,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而支持他的决定的理由是:“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当他发现鸣凤自杀身亡后,曾做了一场梦,梦中鸣凤变成有钱人家的小姐,似乎只有这样,两人才可以顺理成章的结合,由此可见,觉慧作为所谓的进步青年,实际上也依然时不时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电影中的觉慧由张瑛饰演,作为粤语电影的“四大小生”之一,他的表演可正可邪,英俊的外表为觉慧这个角色加分很多,有很好的观众缘。同觉新的人物处理类似,电影中觉慧的形象也变得更为“片面化”,他没有太多犹豫与心灵上的自我折磨,整体有反叛与积极的生命活力,身旁那位永远穿着旧式长袍满脸愁容的大哥觉新,则更显得落伍又悲伤。三弟觉民这个人物,则与书中没有太大出入,同样作为进步青年的觉民,在对爱情进行追求时,坚定地站在自己立场上。
片中创作者借助几位不同的女性角色,进行细节书写,呈现出新旧交织的时代风貌。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在封建体系中,女性则更容易变成制度与时代的受害者。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开始追寻自我,反对父权,否定社会固化的性别规范。当她们出现于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时,创作者是“以一种从男性意义投射出来的、绕开女性内在本质和精神立场的女性观,在呼唤女性解放和衡量女性价值的”[13]。《家》中的几位女性有着不同的阶级地位和成长教育环境,传统的贤妻瑞珏、多病温婉古典的梅、追求进步的女学生琴、决绝无奈的女佣鸣凤……她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前两者并没有太多反叛性,后两者的反叛一个是自觉主动,另一个则是因自我节制。书中有对琴与母亲多次争辩的描述,她也曾面临痛苦,喃喃说着“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琴代表着典型的五四女青年,敢于付诸行动。而鸣凤则是旧制度的牺牲者,她“离去”的姿态充满了对命运的不甘屈服。
影片由大小冲突事件不断推进,而最大的反派冯乐山拥有最丑恶的面目,他作为推崇孔教的代表人物,是觉慧口中的“刽子手”,肆意践踏生命。很多事件都与他有关,包括觉新结婚、强迫鸣凤出嫁导致自杀、插手觉民婚姻……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分别代表的青年团队,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既要对家庭内部父权的反叛,又要与社会上的对立权威进行斗争。
总体上看,电影对原著的人物进行了删减,对特定的人物形象进行简化,将传统与进步两大阵营的分配更为简单明了,其中缺少对中间动摇派的描绘,并且将反派人物的丑恶面目进行放大。这样处理使得故事性更强,观众能够更好融入剧情当中。不过,由于人物形象太过于“绝对单一”,也使得电影在思想性上没有原著那么深刻。
四、电影主题:反封建,自由爱情
香港电影作为港人重要的娱乐方式,一直扮演着文化载体的角色,它在不断贴合观众需求的同时,也在侧面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随着冷战的到来,香港成了多种意识形态的交织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国民党退于台湾,而香港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一场“冷战”。香港因为地理、政治和社会环境,成为左右派的前哨战场,两派的报纸刊物甚至是社会团体,常展开对立性的论争。这一时期,受多种文化影响的香港电影,即使是在讲述传统的中国故事时,也会将重点放在现代性上,当以爱情为主题时,家庭与亲情也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当时,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的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左派电影致力于从启蒙出发,将电影作为教育教化的工具。尽管“中联”不能直接定性为左派电影团体,但它与左派进步电影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它认同代表进步希望的新中国,核心影人自20 世纪40 年代以来一直参与进步电影创作,是左派电影公司“新联”创立之初的创作主力,另一方面“中联”效仿左派公司,也成立了以李晨风导演为主任的编导委员会,强调集体创作、品质把关,出品的电影也因为左派意识形态而无法进入台湾市场。但客观而言,“中联”更多是从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的进步意识出发,与香港左派电影创作达成了内在的和谐一致。
“中联”创业之初,选择将巴金的《家》改编为电影,希望汲取“五四”新文学中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并宣扬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反封建、反礼教的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典型呈现出五四新文学中所传达的追求进步解放与现实冷峻的文化意识,能够唤起港人的思考与反省。但考虑到香港政治环境的限制以及给观众的接受度,在进行作品改编时,更强调故事性,而非政治性。影片以强调自由个体、独立解放、现代思辨和主体思考的文学内蕴与时代精神,既契合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港人的历史境遇与文化反思,也自觉承载起那时香港电影浓郁的民族情怀与中国意识。
周蕾曾指出,中国大陆官方对于巴金小说的阅读方式为“读者获邀参与一种新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成形于对旧中国的断绝以及一厢情愿宣告新中国出现之际。”[14]不过,《家》作为巴金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即使是以第三人称进行书写,但那些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活动,却又都指向作者本人,它所记述的不完全是时代的真实,而更侧重于“内心的真实”,包含了一种含混复杂的意味和情感。作品中,除了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自我心理的解剖,整部作品带有其理想色彩。此外,原著中也包含了很多潜在的文本,觉慧阅读的书籍、那些引用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物的行为与思想,引用的文本和小说本身的文本之间也形成了对照。
电影省去了对新旧派之间挣扎的描述,减少了对人性暧昧之处的刻画,并未指出明确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而是聚焦于人,专注于家庭伦理与爱情追求上。全片以觉慧的旁观讲述以及与鸣凤恋爱的悲剧经历为贯穿,实际上,“通过对家里最具有反抗精神、最为热情的觉慧为了解救自己所爱的人而终告失败、到场送葬的形象,与立足于两个时代之间而无力自拔的觉新形成对照”[15],既弱化了原著小说中觉慧身上的社会政治色彩,又提出了现代人出走后如何独立的现代性命题。电影中,无论是“旧绅士”的祖父,还是曾受过新式教育、又回归到旧家庭的大哥,或是一直宣扬出走、逃离牢笼的觉慧,他们都是复杂矛盾的个体,不能简单地拿“谁对谁错”去衡量。影片从易被观众接受的角度,来达成反封建和追求爱情的独立意识,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现代意识表达与文化探讨。
革命与爱情常有着密切关联,从小家到大家,在“家国同构”的理念下,五四青年们对家庭的反抗、爱情的追求,实际上也呼应了对现代国家的召唤。巴金的创作来源既有生活阅历,也包含了阅读体验,借助小说《家》,从个体出发,再到对家庭集体的考虑,最后走向社会群体,“五四”机制在多角度的叙述下得以清晰和放大。“恋爱对觉慧来说,先是争取自由的标识,后来成了迈向自立的途径,最后成为抛开封建大家庭的主因”[15]243,汇入中国社会革命的大洪流。正如巴金提及《家》时曾说道 :“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 (我控诉) ”,他憎恨的是制度,而非人。
结 语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香港被学界想象为是“文化沙漠”。但事实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时代政治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的多元化改编和再创作,是香港电影文化显影的重要部分。
本文所论述的作为“中联”电影创业作的《家》,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以既“忠于原著”,又简化聚焦情感故事,在精品“文艺片”中,融入了进步意念与现代意识,一举击破囿于哀怨戏曲和神怪法术、“曲折离奇的故事以及色情的渲染,格杀打斗的刺激”[16]等粗制滥造的毒素电影,树立了关注社会现实与伦理文化的优质粤语片的理想标杆,成为香港粤语影界一股扬帆起航的清流。《家》的成功,引领了后续香港电影更多元化的新文学改编潮流,推动巴金“激流三部曲”后两部《春》《秋》与“爱情三部曲”《雾》《雨》《电》、鲁迅名作《阿Q 正传》、曹禺名作《日出》《原野》等新文化电影的陆续涌现,通过娓娓道来的文学性故事,有效地建构了香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都市过渡的社会想象、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