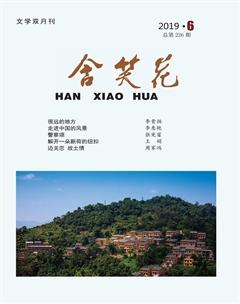嘿,你摊上事儿了?
阿传
一
老张最近有点儿背。
先是二儿子仲春与媳妇离了婚;接着大儿子孟春,因为“涉嫌敲诈”进了公安局。这老张心里,跟压了块铁板似的,很烦闷。正当他坐在自家花楸树下左想右想时,腰间的老年机咋呼呼地响了。电话是在市公安局工作的三儿子打来的,老张迫不及待地问,“暮春啊,你大哥的事咋说啊?”电话那端传来憔悴而又无可奈何的声音,“爸,这事你就别过问了,问了也是白搭。这诈骗兼伙同他人敲诈勒索的罪,少说也得判他一个三到五年的有期徒刑,还就高不就低……”
“别跟我废话!”老张眼珠一瞪,粗鲁地打断三儿子的说,“你就跟你二哥一个样,动不动就法律,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好日子不过,离什么婚!”
“爸,这婚不离也离了,再说,这二哥和二嫂闹不和,你也不是这一天两天才知道的事。”
“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老张喘了喘气,接着说,“那我问你,你大哥的事,你们总得帮帮他吧?”
“爸,这非常时期的,我俩谁也不敢过问。再说,这市公安、区公安又不是咱老张家的看家护院。”
“你……”老张气得当场就翻了好几个白眼,“我刚从你大哥家出来,你大嫂还在那边寻死觅活。说你哥坐牢坐死算了,可那小张镭还在兰州读大学,这以后要出来上个岗或考个公务员啥的,还不被你哥这点破事给牵绊住一辈子?”
“早干嘛去了?”暮春也颇有些愤愤的,“我哥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放纵惯了,什么地下出警队、飞鹰帮,狐假虎威!听说最近还搞了个什么‘煤矿安全维持会,都啥年代了,拿我们公安系统当摆设吗?不治治他,他还不反上天去?”
“你别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老张继续骂骂咧咧的,语气也愈发的尖锐,“他也是你亲哥,就算他张孟春现如今混成了一坨狗屎,那也是你哥!要不是你大嫂辛辛苦苦帮衬着我,供你俩读书,会有你们今天……”
“你俩哪得现在的神气活现。”
“还算你有点良心。”老张说,“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儿,你俩要不把你哥给弄出来,今后,就别指望再跨老子这道门槛。”
“爸,你这是逼我和二哥……”话还没完,老张这边已气咻咻地挂上了电话。
二
和老头子通话完毕,张暮春就把桌上的卷宗小心地合拢,理好后重又放入警务科的档案柜中。然后,径直就往二哥住所走去。
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暮春见二哥正骑着辆电瓶车过来,车上绑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一见暮春,这仲春就扯直喉咙地大喊,“快过来,过来帮拿下。”
暮春一边帮二哥解下车上的东西,一边说:“老爹为大哥的事又打电话来了。”
“你咋说?”仲春问。
“我跟他说不通。老头子听起来似乎还挺生气的。最后竟下通牒说,我俩要不把大哥给捞出来,今后,就别指望再踏他那道门槛了。”
“若种恶因,必收恶果。大哥这样,预料当中的事。可话还得说回来,他发展到这步,我俩作为他弟弟,也有监管失察的责任。”
“话虽如此,可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且都又不在我俩的监控范围。再说,我们也不是没说过他,可他哪一次听了?”
“可他毕竟还是我们的亲哥,你说能不管吗?”
“我也没说不管。可问题是,不知道咋管。”
“管,肯定是要管的。这几天我也想清楚了,我俩先各自回局里办个‘回避申请,以表明我俩对待此事的态度。再给他请一律师,有什么事,让律师替他说去。只要他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供述罪行,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我俩这身份可不能置身进去,否则就是在违法乱纪。”
“就是。这可真急死个人。你说这大哥……哎,他算自作自受;可大嫂,小张镭,我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从这一点来说,老爹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若没有大嫂,我俩……”
“我俩哪得现在的神气活现。”
两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的就把老张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了出来。
三
老张在沙地村,无论之前还是现在,都可算一人物。
年轻时撵马车,开磨坊,愣将一个老张家的面条生意,做得那叫一个远近闻名。这么说吧,在整个沙地村或沙地村周边,只要大家想以麦换面,都会下意识地选择这老张家的面坊。“地道、有筋骨、价格又合理,煮出面条后的水不浑,還清澈。”——正是老张家面条的口碑。
但当面坊生意做得正红火的时候,老张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将自家面坊的机器,转手了。
对此,大伙儿均感到大惑不解。
好心人说,“老张,钱多了烫手啊,一大家子人,开支不小呢。”
老张只是笑而不语。
不久,村子周边挨着的就冒出很多家面坊来,这开面坊的人,竟大有反超这面条消费者之势。这时的投资者们,才渐渐的尝到这跟风的苦头了。他们生产出来的面条,要么供大于求;要么竟便宜到连成本都快保不住的地步。可有什么办法呢?此时,再要脱手手中机器,已无其他可能。那就只好把机器,搁下来慢慢生锈、锈坏。
大家才都想起老张当时的那一笑。这老张,人精呢!
老张人虽精,可老张也有失算的时候。
老张婆娘去世得早,早些年,净忙着没玩没了地挣钱,也没顾上这续弦的事。待到想盘算一下时,孩子却大了;再想盘算一下时,孙子又大了。于是,老张就干脆不去想了。
张孟春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老张一直把大儿子像“太子”一样的精心侍弄。老张觉得,只要把“领头羊”精心侍弄好,就会把仲春和暮春这两只“跟班羊”领上道的。可最后的事实表明,精于算计的老张,在张孟春读书的这件事上,太过于高估了。
老张曾粗略地算了一下,孟春一个人耗去的钱粮,竟比张仲春、张暮春这小哥俩耗去的,还多得多,光一个小学,张孟春南征北战,转了四五个学校。好不容易的考上临镇的一所中学了,可一架打下来,又花去仲春、暮春他哥俩差不多一个高中的费用,但这些,并没动摇过他老张的对大儿子抱有的希望。直到有一天,张孟春从学校带回一个大腹便便的姑娘,老张才陡然发觉,原来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看好的这只“领头羊”,竟长成一头“领头猪”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仲春、暮春这小哥俩,好像就跟老张在不断较劲似的,这老张越不重视,他俩就越发的出类拔萃。最后,两人均相继的考取了政法类的大学。
四
老张清楚地记得,当年孟春和猫五联手的那一架,这张孟春硬是没用了几闷棍,把一个叫顾开河的同学的膝盖,打了个“粉碎性骨折”。事后,那个绰号“猫五”的家伙,“喵呜”的一声就溜之不见了。唯剩這个“张老财”的公子,在班上“财大气粗”地等着他老爹拿钱来赔医药费。
为平息此次事件,应该说,老张是动用了他这一生相当一部分积蓄的。好在调停过程中,受害方既没报官,也没向老张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只希望老张能把孩子的腿治好就行。事后,老张生气地摁着他张孟春的后脑勺问,“张孟春,猫五都知道跑你咋就不知道跑呢?”张孟春就嘀嘀咕咕地说,你还真以为我傻啊老张,可全校谁不知道我是你“张老财”的儿子。我要跑了,你还不给他们做一辈子的面条?老张就表示理解的看了他张孟春一眼,然后,又心疼地看了看那张调解的字条,“三万多啊张孟春,以后没钱了看你咋折腾。”
没钱就打没钱的主意呗……
初三上半学期,张孟春就把一女生往他老张面前一带。老张那时,正在闹哄哄的面坊里压面条。说张孟春,同学来了就带家里去啊,带这里来干什么?张孟春“噗”的一声,同学?马上声音又往上一扬,她不是同学,她是你儿媳,爸。你要有啥忙不过来的,就尽管吩咐她便是。
待到老张再要说什么的时候,这张孟春就没当回事的跑出去了。仿佛他此次前来,就是专程来向他老张办理移交手续的。老张抬起头,透过那挂满面条的间隙,粗略地扫了那边的女孩一眼,问姑娘,你家是哪里的?女孩期期艾艾,半天头也不敢抬地,“田坝村的”……
“哦,那不远,就六七里地。”老张说着,就把一竿子面条挂在了木架子上。接着又道,你和孟春来家里玩,我很欢喜,可要让家里知道,担心他们到处找你。见女孩还是不作声,老张更像没话找话,这时,女孩就跟憋足了很大的勇气似的,开口了,说“不回去了,叔……再说,也没脸再回去了。”
怎么就不回去了呢?老张抬起头,定目瞧去:这孩子,还真是一讨人喜欢的主。红扑扑的面庞,俊俏而略带着一定稚气的脸;朴素得体的碎花小衬衫,遮掩着微微隆起的肚皮。老张结合张孟春刚才所说的话,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妈的,原来张孟春这家伙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儿媳,还有孙子啊……
原本老张对孟春读书还是抱有一丝期待的,见他生米已做成了熟饭,给自己带回来这么一漂亮的儿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抓紧时间紧张办事,按沙地村传统的方式,去女方家提亲。因为这门亲属典型的“提前亮”,女方家也没好在“关键时刻”再苛求些什么,一切均水到渠成。
原以为他张孟春成家后,会有个过日子的态度,哪知这家伙婚后的日子,竟然过得更加游手好闲。整天东游西逛不说,还净想着发大财。按理这发大财也没什么不好,可他张孟春的“发财梦”里,总时不时地透露出一股邪气。好在这小子摊上这么一贤惠能干的好媳妇儿。不仅是贤惠能干,还勤俭持家。自打这儿媳妇过门,老张觉得这家才有点“家”的感觉。
仲春、暮春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读自己的书,丝毫没被他哥孟春身上的不良习气所沾染。
五
这些年在沙地村,他老张算是尽享“尊荣”了。这无论走到哪,都会有人与之招呼,总有人给他几分薄面。其实他老张打心眼里知道,这面子,终归还是市里的那两个儿子给的。这古话说得好,“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老张活了大半辈子,不糊涂。
但老张心里的隐忧,却随着“富升”煤矿的到来而越发的明显。去年,自“富升”煤矿进驻沙地村以来,这张孟春更是成天的“上蹿下跳”,日子蹦哒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欢。当然,沙地村村民,也欢。这不就要进行煤矿开采了吗?煤矿开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赔款,意味着搬迁,意味着沙地村村民从此就要像城里人,过着那种远离“锄头把”的生活。张孟春呢,更是把日子描绘得无比的光辉灿烂。说“那时,我们就可骑着‘小电驴每天上下班;下班后,如果想在家吃,就随便带点菜回家来做;不想做,那就在外面的餐馆吃……再然后,你就可以和小区里的大爹大妈们跳跳广场舞;我呢,也可以约几个朋友去喝喝咖啡……”
“喝咖啡?”婆娘边剁猪草边说,“我听儿子说,那地方消费可贵了,一杯好几大十呢……哎,再要有个关猪的地方就更好了,听说城里的猪都净是些饲料猪,吃着根本就没什么肉味。”
“没趣。”张孟春鄙夷地看了他婆娘一眼,“这年头肉都还没吃够的人,也怕只有你小张镭他妈了。自个忙去吧,我还要去跟猫五他们开会,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按以往这样的聚会,一般都是“乌烟瘴气、鬼吼鬼叫”的。可那天,当张孟春跨进门来的时候,这猫五家却安静的出奇。这十几个人的屋子里,一个个就跟他妈中邪了似的,全他娘的不吱声。见张孟春进去,只齐刷刷地站起来叫了声,“春哥好”,然后便都又把头耷拉了下去。张孟春没见这门背后还坐着个人,清清嗓子就想主持这次“会议”。门口那人却先开腔了,“说吧,猫五,这下,张孟春也来了,你就说说,当年你们这笔糊涂账,咋理?”
张孟春顿时吓了一跳,这老头子,怎么不请自来的“莅临”本次会议了?就问猫五到底怎么回事。猫五就拿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苦笑了一下就递给张孟春。
“调解协议”。张孟春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当初打伤顾开河的那笔善后费。就不快地说,“老爹,这都是哪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你今天干嘛又把它翻了出来?”
“什么陈芝麻烂谷子?这叫人不死账不烂。猫五,我来问你,当初,是你跟张孟春一起打的顾开河,是吧?”
猫五客客气气地回答说,“是的,张大叔。”
“顾开河的腿是张孟春打断的,对不?”
“是顾开河提着砖头朝我砸来的时候,春哥情急之下,才打断他的腿的。”
“不需要你陈述情由,你就说顾开河的腿,是不是他张孟春打断的。”
“是的。”
“嗯,那就是张孟春该负主要责任。但是,”老张话锋一转,“你是不是也该负点连带责任呢?”
“是。”
“好。既然你也觉得自己该负点连带责任,那你觉得你是该负多少的责任呢?”
猫五道:“我觉得,至少该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张大叔。虽说顾开河的腿是春哥亲自打断的,但招惹上顾开河,究其根源,起因在我。”
“仗义。”老张说,“那就按你说的三分之一的责任来划分吧。三万二千多,以三万来算,三分之一,你出一万。”
“可以的,大叔。”猫五起身就想出去取钱。
老张却叫住他,“慢。当年这包谷是一毛二一斤,现在是一块三一斤,涨了十倍还多。就以十倍来算,你说现在再拿这一万块钱,还赔得了我吗?”
“老爹,看你,都在说些什么。”张孟春再也听不下去了,“你是缺钱吗还是少喝?丢人。”
“你给老子闭嘴。你还好意思问我是缺吃还是少喝?你怎么不问问,这些年来你给了我多少吃喝?若不是仲春、暮春每月一人出两千给你在家服侍我,就你,还想承担小张镭读书的那点费用?”
这话还真戳中了他张孟春的软处。
这些年,沙地村有谁不知,张孟春就指着他那两兄弟过日子呢?张孟春虽被老头子呛得无言以对,但他更知老头子一旦即兴起来,嘴里还会跑出更多让他丢脸的事情。所以只得把手朝大家摆了摆,说“散了散了,有什么我们改天再议。”
六
老张还是没能阻止住张孟春等人即将要干的那些“糗事”……
富升集团要进山采矿,先得打通通往河沟头的交通枢纽。否则,那些煤,根本就没法运出去。张孟春等人那天所要商议的,就是如何借机坑富升集团一笔的事。虽然,在此之前,沙地村村委已在全村的动员大会上,再三给本村村民打了招呼,富升集团来我们沙地村开矿,是件利村利民的大好事,不仅可以带动本村经济的发展,还可解决本村劳务的相对过剩。所以,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故意捣乱或刁难。张孟春在会议一结束,立马找到沙地村村主任说:“主任,作为沙地村一员,我有个问题,想跟你反映反映。”
村主任问:“什么事,你说?”
“诚如你刚才所言,富升集团来我们村采矿,确是一件利村利民的大好事。只是,在通往河沟头的那些路上,都葬有我们祖先的一些坟。我想,这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家也有个祖先老人的不是?”
村主任是刚来这里上任不久的大学生村官,对沙地村本地的人文、地形都還不太熟悉,就悄悄问了问身边的副主任,这人是谁。副主任悄声地说,张家老大……然后,对着主任又耳语了几句。主任马上就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向张孟春表态说,“你说得很对,这谁家都有个祖先老人,通往河沟头的路所涉及的所有坟所,限期迁葬;每所迁葬的坟所产生的费用,村委会这儿,都将有所补贴。至于补贴多少,待村委会和富升集团商量后,再定。”
“好。”张孟春说,“主任还真是快人快语,一看就是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主任。只还有一点,这迁葬费归迁葬费,那修路占去的地,也该……”
“一并一并,”村主任说,“具体标准是多少,暂时还答复不了你。”
大家见主任那么不明就里,就“嘿嘿”地干笑起来。
其实,“河沟头”哪来的什么坟。
水发的时候,“河沟头”就是一“河”,涛声滚滚、势若奔马;水不发的时候,“河沟头”就是一“沟”,怪石嶙峋、荒草遍坡。谁家会把老人的坟葬沟里?但张家老大说有坟,那应该就有坟了。果然,这没过几天,沟底就冒出十几所“坟”来,张家的、李家的、王家的、赵家的……其实知情的人都清楚,这些“坟”,全都是他张孟春的。好在迁葬费和土地赔偿费还没下来的时候,这件事就传到了老张的耳朵里。老张气得火冒三丈,操起扁担就冲到了张孟春家里,家里只有儿媳妇。
“张孟春呢?”
儿媳妇见事态严重,也没敢招惹这老头子,小心翼翼地回答:“他一大早就跑出去了,也没说去哪里。”
老张扁担一丢,恰好砸中了墙根处那正吐着舌头的小母狗,“老子今天就来问问这个不要脸的狗东西,我老张家是哪些先人葬在了沟底?”
七
张孟春如此花样百出,并非一朝一夕。
大前年,他去县城参加初中时的一次同学聚会,老婆奚落他:“那些同学,人家个个可都是功成名就,你就别去丢人了。”张孟春一脸不屑:“他功成名就咋的?想当年在学校,我乃沙地村鼎鼎大名的“张老财”的儿子;现如今,我市公安、区公安里哪里没人?还不说我那正就读于兰州大学的儿子。”婆娘说:“你牛,你在儿子身上花过心血吗?”张孟春在他婆娘的屁股上捏了一把,牛里牛气的说:“别人不知你还不知道吗?”
还真如婆娘所说,这同学聚会,还就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刷存在感的,根本没人拿正眼看他,正当他在左岸的包房低头喝闷酒的时候,门口乌压压就进来了几十号人。一律的黑西服、黑眼镜。一进门,就快速地分往这过道的两边,像木桩似的站着。站毕,中间才走来一人,也一身黑西服、黑眼镜。与此同时两边的黑西服、黑眼镜还把头都低了下去,齐声道“五哥”。张孟春定睛一看,妈的,这不就“喵呜”一下就消失不见的猫五吗,啥时都变“五哥”了?
见其他人都在相互的黏乎,唯张孟春一人在那里喝闷酒,猫五就有些生气了,大声问,谁这么没眼力劲儿,也不知道过来陪陪咱春哥?黑西服、黑眼镜和其他正黏乎的人就都走了过来,齐声的道,“春哥好,春哥您多包涵。”
张孟春趁着酒劲就故意拉高了声调:“好啊猫五,如今都人模狗样了。”
猫五爽朗地说:“哪里哪里,以后还得仰仗春哥您多关照。”
张孟春道:“此一时彼一时,春哥现在也不行了,就指望着两个兄弟过日子。”
“你说的是仲春和暮春?他俩现在哪里?”
张孟春说:“妈的猫五,你他娘的咋跟一归国华侨似的。仲春、暮春一个在市公安、一个在区公安你会不知道?”
“春哥见谅,你不说还真不知道。这些年在省城,小日子也过得挺煎熬,亲朋好友都疏于走动了。”
“你还煎熬?妈的,你都带这么多弟兄了还煎熬?这每月要没个三五千他们会跟你?”
“那倒不止,春哥。这每月下来,也就一个三两百万的毛利,”猫五说着就指了指那帮人,“可你看,我这人多嘴杂的,几十号人,不仅得管他们吃,管他们喝,管他们发工资和五险一金,还得四方打点,所以这花费,也不小。”
张孟春惊讶道:“猫五,你他娘的做什么生意,一月竟能挣三两百万,莫不是——毒品生意吧?”
“我不碰那。我们是地下出警队。平时嘛,也就专给各街道、各办事处维持下市场秩序;其他时候嘛,就给那些大公司、大企业的收下款;再有,就是遇到拆迁时拿不下的“钉子户”,我们就上了。”
“啊?这不就黑社会吗,猫五你还真够牛逼的,黑社会也敢美其名曰‘地下出警队?”
“嘘!”猫五食指在唇边比划了下,“如今这社会,哪敢再玩什么黑社会,除非想死。我们不过是在帮一些生意人,收一些法律不好过问或问不了的烂账而已。春哥加入我们一起发财怎样?”
“开什么玩笑,你看如今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拿什么来加入?”
“假如你感兴趣,‘我们地下出警队正准备拓展湄溪方向的业务,只要你让二位弟弟在关键时罩着,我每月即可分你两万红利。”
猫五,你别当了皇帝还想成仙——想歪了。我那俩弟弟,从不在这些方面罩我。那年我和朱绍龙为了几锄自留地,摁上了,想让他俩帮忙解决下,那两个小兔崽子说,哥,我俩又不是专为你看家护院的。而且,我俩还劝你,别在乡亲们的面前耀武扬威的,不就几锄自留地吗,就哪怕全是金矿,你那几锄地,又能产出几两金子?”
八
“迁葬费”和“土地赔偿费”被老张骂没了之后,“富升”集团为感老张其德,先后在厂上给张孟春夫妇,安排了一份开叉车的工作。
张孟春不乐意。扯着嗓子在家里跟婆娘喊:“谁他妈愿叉谁叉,反正我是不去叉的。”
婆娘说:“这你可要想清楚,这是多少人都眼红得要命的事。那些每天在矿里作业的,每月都才拿一样的工资,这么轻松的工作,你还想哪里去找?”
张孟春说:“你别管,反正老子自有老子的办法。捧着金饭碗,还会去讨饭?”
“你就别折腾了,我可听说了,那猫五本不是什么好人。他在省城混了那么多年,干嘛现在又折回来了?听说现在“扫黑除恶”的风聲非常紧,在外面混不走了才重新折回来的。哎,我问你,你那“煤矿安全维持会”,到底是想搞些啥子?”
“不搞些啥子。就是装煤的车多,想给某些快速装车的司机行个方便。”
“不都按序排队吗,行什么方便?”
“你懂个球!这一车出去,光运费就他妈好几千块,谁不想多装那么几车?”
“你的意思,就是帮那些人插队?”
张孟春说:“对。还算你没跟我白混这么些年。老子就是要帮这些人插队。谁要不服我管,我就让猫五他们收拾谁。当然,我帮这些人,也不是白帮的,一张车必须要我塞个三百五百的。”
婆娘说:“那要个个都给你钱,你怎插?不可能拿了人家好处又不帮人家办事吧?”
张孟春说:“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俗话说粑粑都有个厚薄,就算个个都给我钱,也不至个个给我钱都一样多是吧?反正老子不管,谁给我的钱多,我就让谁先装车。你说这每张车要都给个三百五百的,这一天下来,我能挣多少?”
婆娘默算了下说:“这一天吧,少说也有四五十张车在排队。就算只有两张车找你,那也是大几百乃至上千块;要真如你所说的,每张车都在找你插队装车,天哪,你这死鬼,一天还不挣个几万块?”
但婆娘立又觉得有些不妥,她担心时间长了,煤厂就会被搞得乌烟瘴气,只怕那时,局面就将难予控制了。
但张孟春还是坚持说不会出乱子,理由是第一他张孟春从始至终根本就不会出面;第二猫五的“煤矿安全维持会”养着的那些人,也不是吃闲饭的;第三即便局面真变得难予控制,那仲春、暮春这两个小王八蛋又岂会坐视不理,难道他俩就会眼睁睁看着他哥接下来吃官司?
婆娘说:“反正我说不过你,但我觉得,你还是万事小心。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这有些事情,不仅不能给仲春、暮春他们带来为难,还不能给他俩脸上抹黑。”
张孟春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你们咋都一个腔调,咋都那么高风亮节呢?”
九
但一切,还真没顺着他张孟春的思路来。
在富升煤矿以地下规则形式运营了大半年之后,张孟春他们的“煤矿安全维持会”,还是出事了。
这天,两个司机因为谁先装煤的事,扯皮了。司机甲:“你是从我后边来的,凭啥要在我前面装车?”司机乙:“凭这。就凭我在维持会那儿开了条子。”言迄,就递给了司机甲一便签。
司机甲是一新来的。接过那便签一看说:“你们还兴这个呀,怎么下个苦力、卖个苦啥的还得交个什么排队费?莫非,今儿还遇上现实版的周扒皮了?”
司机乙:“嘘!你小声些,要让他们知道,以后要在这地界顺趟的进出,就没那么容易了。”
也活该要出事。
那人话音刚落,猫五便提着橡胶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什么周扒皮,兄弟,你说谁周扒皮?”
司机乙赶紧打上一支印象,说“五哥,闹着玩的闹着玩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嘛。”然后,给猫五把烟点上。
猫五朝那人肆无忌惮地喷了口烟雾,“兄弟,你装你的煤,我们维持我们煤厂的秩序,大家互利共享、双赢,何来周扒皮一说?”
“好。那我问你,你们这排队费是从哪儿来的,是富升集团给你们的吗?笑话。你们每张车都在收取车主的排队费,这哪来的互利共享?分明就是在车主口里抠食嘛。”
“又没人用枪硬抵着你屁眼让你交,你想不顺趟的跑进跑出,你那排队费,不稀奇。”
“老子今天就偏不交这排队费又要跑来跑去,我看谁能把老子怎么样!”
“那你就试试……”
“试就试,青天白日的,老子还怕你个鬼。”那人话完转身,打开车门就准备登车。
“砰!”猫五一橡胶棍,照准那人脑门当场就打了下去。血“倏地”冒了出来。那人身材晃了两下,慢慢就靠着车门倒了下去。
“打架了打架了,快报派出所,那边好像打伤人了。”富升煤厂上,一时之间就跟煮沸了的粥,跳得噼里啪啦的……
张孟春几乎是跟派出所的人一起到达现场的。他正在家里逗一新买的画眉,听说猫五在厂上伤了人,张孟春就坐不住了,立即往煤厂跑。
张孟春以为,事情还远非到了那种难以控制的地步。这派出所的人来到现场,得先了解了解情况,做个笔录、采集下证据什么的,这时,他就可以来个居中调停,以一个一般的打架斗殴来了结此事。“不就是钱吗,妈的,反正又没弄死人,只要这善后工作做得好,一切都会相安无事的。”张孟春想。
但事情的恶劣程度,还真远远超过他张孟春的想象。这派出所的人一到现场,马上就開始抓人,根本就没他张孟春斡旋的余地。“嘿,我还真佩服你们,”这派出所带队来的,正是那姓潘的副所。张孟春知道,此人脾气不好,每遇严肃或需特别提醒的事情,必先“嘿”一下。张孟春到时,见他正骂咧咧的控制着有些混乱的现场,同时嘴里也在不时的“嘿……嘿。”
“嘿,受伤的,赶紧送医院;嘿,这打人的,马上给老子铐走。”这时,被打的司机已差不多醒来,只样子看上去还有些傻傻的;布满血丝的脸上,像爬满了几条红色的蚯蚓。
十
次日晌午。
张孟春吃罢午饭,准备去趟派出所“刺探”下猫五的情况,姓潘的副所带着一民警就推门进来了。装模作样地问,“你是张孟春?”
张孟春气定神闲地说,是。
“嘿,你摊上事儿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请问潘副,我犯法了?”他识得这姓潘的副所,好几次饭局上,他和姓潘的副所曾有过杯酒之交。
姓潘的副所没理他。
旁边那民警却开口了,你“涉嫌敲诈富升煤矿司机排队费,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拘传。”
到派出所后,张孟春原想来个一推二三五,可猫五却先“背不住锅”,没几下就跟抖篓子似的,全交代了,并将所有的罪责给推给他。
当着张孟春的面,猫五说:“警官同志,你想我这身后若没春哥这张保护伞,你就算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造次啊!”
潘副啪的拍了下桌子:“嘿,猫五,你小子皮又痒痒了不是?什么春哥,但凡来这里的,都只是嫌犯。”
猫五说:“是是是,警官同志,张孟春,是他张孟春私下里给我当的保护伞。”
张孟春虎死不倒威,依然气定神闲:“潘副,你听听你听听,猫五这不是阎罗殿里出告示,鬼话连篇吗?请问我张孟春有什么?权,还是钱?这些年,我可一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我有什么条件去给他猫五当保护伞?”
潘副所说,“张孟春,你就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哈。有什么事,最好一次性的给我们交代清楚。你那两个兄弟,跟我们也是一个系统的,你应该听他们讲过‘自己说出来是一回事,我们调查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的话。”
“那你们调查啊潘副,我又没做什么拿什么来交代?”
潘副所终于忍不住了,他先“嘿”了一声,“张孟春,别给脸不要脸哈。这几年,中纪委拿下的省部级高官到底有多少,我不说想必你也很清楚,所以我还必须告诉你,千万别存什么侥幸心理,值此紧要关头,任何保护伞,都将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面前,灰飞烟灭。”
张孟春就不说话了。这潘副所言外之意,就等于在告诉他张孟春,如今,任谁也保不住他了。
“没啥可说的了是吧?这没啥可说的我们就进行下一个话题,”潘副所从抽屉中又拿出一沓子信,“这些,都是关于你的——举报信。举报你自富升集团进驻这沙地村以来,涉嫌诈骗的一些相关情况。你说,有这回事没有?”
张孟春气得脸色发白,申辩道:“有。但还我知道这叫犯罪中止。虽然这些事,是曾造成一定的事实,可我根本就没诈骗到富升集团的一分钱。”
潘副所于是很难得的就笑了:“张孟春,亏你还知道啥叫犯罪中止。好,请在这拘留证上签个字,我们将对你实施刑事拘留。至于服与不服,待我们侦查、提请逮捕后,你再耐心的等待法院对你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