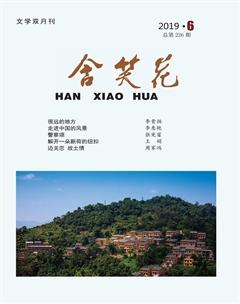守望
陶岚
时间仿佛一个光圈,没有起点,亦无终点。时光的年轮转过一圈又一圈,埋葬爷爷的黄土上早已冒出了青青的野草,站在爷爷的坟头前,我的喉咙像被坚硬的石头卡住一般,记忆中的往事,如潮水一样地涌入脑海。
爷爷去世之前,希望我能在他的坟前种下一棵小树,他说他要站在家乡最高的山上,看着家乡一路的变迁。
我出生于文山州丘北县官寨乡一个偏远的壮族村寨,属于官寨乡最东边,与曲靖市的师宗县接壤,与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泸西县隔江相望,交通十分闭塞。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当年的故乡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乡亲们长年累月地在土地上弯腰耕种,风吹日晒,早出晚归,可所得的收益仅能维持温饱。
那时父亲母亲去赶集,要到南盘江边坐船去对面的泸西县,懵懵懂懂的我一直不明白,我们属于丘北县,为什么要去泸西县赶集。当时村里通向山外唯一的捷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其中不但要越过泥泞的田野和低矮的灌木丛,还要翻越两座高而陡峭的大山。村里人说,从我们村到官寨乡政府的所在地有40公里山路,说是40公里山路,没有人丈量过,只是祖辈们一辈一辈的相传,固定了这样一个数据,我们也深信不疑。
可就是这40公里山路,阻断了多少孩子的梦,也阻断了多少成年人的未来,村里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而我,是这众多人中的幸运儿,我顺着这条山路走出了故乡,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在我的身后,有一个苍老的身影总挥之不去,那是我最敬重的爷爷,他一路守望我走出大山。
爷爷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他会写字是跟村里的教书先生学的,而那个人,是我爷爷的爷爷。听爷爷说,祖上并不是这个村子的人,因为祖上会识字,有文化,才到这个村子教书。
村子与外界相连的路非常难走,山上石漠化严重,马儿牛儿踩过的石头经过雨水的冲刷,变得坑坑洼洼,特别是下雨天,异常湿滑。并且这是一条上山的路,非常陡峭,最陡的地方,爬坡人的鼻尖,已经离土坎很近,需要手脚并用,很多时候遇上赶着牛赶着马的人,需要侧过身子趴在立着的石头上,让牛儿马儿先过去。
这条路虽然很难走,但我们却不得不走,因为这是我们通往外面世界唯一的路。我们要把瓜果蔬菜背到街上,去换取商店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孩子们去上学、村干部去开会、村民们去看病,都要通过这条路。
这条路上有我童年温暖而美好的回忆,也有我不能言说的伤痛和恨。
记忆深处,我虽然埋怨这条路难走,但当时内心里却是最期待走这条路的,因为每周一次的赶集日,在这条路的尽头,我可以看见楼房,看见马路,看见五颜六色的玩具,会看见穿着漂亮裙子的女人,也会看见穿着黑色皮鞋的男人。最重要的是,可以去吃一次我最喜欢的米线,没怎么出过小山村的我惊叹于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每一次去赶集,中午时分,我都会用渴望的眼神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说我肚子饿了。母亲知道我想去吃米线,嘴上一边说着,早上出门不是吃过饭了吗,一边从贴身的衣服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抽出两张零钱递给我。那时的家庭条件,只允许我吃那种没有肉的米线,可我依旧馋得不行。每次我叫母亲一起去吃,母亲都说她不喜欢吃,早上出门已经吃过东西了,不饿。后来才明白母亲是舍不得,毕竟那时我和哥哥还要读书,卖鸡蛋卖米的钱要留着给我们交学费。
那时我们去赶集,天不亮就得起床,母亲已经做好酸菜洋芋汤泡饭,吃完立马出发。母亲挑着米在前面走着,我背上家里自己种的洋芋、鲜姜跟在母亲身后。我们走过田野,走过玉米地,开始登山时,懒洋洋的太阳公公才从山的那边爬起来。八月的天空很高很蓝,云朵也很轻。小路的两旁,是一些类似芦苇的植物,叶子细长细长,像剑一样,边上还有许多小锯齿,从中间的芽里冒出一根很长很长的光滑的秸秆,上面长满了白色的须,我猜那也许是它的花。早晨经露水沾湿的白须显得很湿很沉,但是,经太阳一晒,它们马上就会变得轻盈无比,在微风中摇曳着向我们招手。
农村的日子是有许多光阴可以消磨,小孩子们上山抓野味、摘果子,下河捉蟹、摸鱼,可爷爷从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在太阳炽热的下午,他会在家里教我识字,用他自己做的老鼠毛毛笔,沾上电池电极做的墨汁,将繁琐的繁体字写在发黄的旧报纸上。虽然那些字一直被我当做笑料,可终究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一抹色彩,年幼的我怎能明白爷爷搁在我身上的希望。
爷爷的改变是在哥哥生病的那一年。哥哥大我五岁,中学毕业后,因为不忍心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辛苦劳作,便自告奋勇放弃学习,回家帮母亲做农活。
那是夏日的一个夜晚,吃晚饭时,哥哥说他肚子不舒服,不想吃,那时的我们就当他是做农活累的。不一会儿,躺在屋里的哥哥开始呕吐,然后呕血,一口一口,我们都被吓得手足无措。族里的老人们拆下我家厨房的门板,安排族里的年轻人抬着哥哥,一路朝乡上奔去。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我忍着泪,随着众人一路奔跑,走过弯道,接着上坡,然后下坡,经过泥塘,跨过乱石。哥哥一边呻吟,一边不停地吐着血,耳边的风催我加快速度,路旁的小草也让我快点,脚下的小石头恨不得变成车轮来护送,我焦急地看着山顶,感觉今天的路特别长。
平时我得走六个小时的路,这一次,我跟着大部队,这么快的速度我都没有掉队。赶到乡上的时候,我拉着哥哥的手,拼命地喊着他,可哥哥脸色惨白,手心冰凉,似乎已经听不到我带着哭腔的呼喊,只是被褥上浸湿的血迹诉说着这一路的不易。
医生说如果再晚些,哥哥就危险了。那一夜,母亲失魂般坐在哥哥病床前,不说话,眼神空洞得让我害怕,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那一刻,我真的恨那条路,恨那个小山村,恨它太远、太崎岖,恨它太多的坎坷和绊脚石,甚至恨它的坑坑洼洼和残缺不全。
哥哥住院的那段时间,炽热的午后爷爷不再写他的毛笔字,他一个人带着锄头镰刀,修路除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外界不再遥远。
终于,村里开始修路了,村里家家户户都出动,带着锄头、簸箕,就像要上前线的士兵。爷爷更是欢喜,自告奋勇也去帮忙,就这样,这条路靠着沿线群众一锄头一簸箕合力挖了出来。
路修好的那一天,村里像办喜事一样热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虽然这条路只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不仅简陋,而且凹凸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但这条路是村民的希望,是村民发展的动力,是通往外界的桥梁。
爷爷有事没事经常扛着锄头在路上走来走去,路面塌陷了,他就填上石头,填上泥土,方便行走。遇到泥泞的路面,他就找来树棒,缠上稻草,让牛车马车方便通过。爷爷还会从山上挖来树苗,种在路边容易塌方的地方,爷爷说,有树在路边拦着,路面才不会塌。爷爷说,修路补路是最大的善事,不仅可以修今生,还可以修来世。爷爷还说,希望我能像路边的小树苗一样,长大了要守护家乡的路。爷爷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要我把他葬在路对面最高的山上,他要一直守望着这条路,看着家乡的变化。
多年過去了,村里积极响应国家“村村通”政策修了弹石路,村民们凭着这条公路,或做生意,或外出务工,如今都富裕起来,不仅盖了楼房,有的还买了汽车。日子是越来越红火,爷爷却再也看不到了,92岁的他带着微笑离开了我们。
父亲把爷爷葬在村后大山的最高处,对面是新修的公路,山下是越变越美的村庄。我在爷爷坟前栽了一棵小树,就像爷爷当年种下的树苗一样,既耐寒又耐旱,不管土地如何贫瘠,不管环境如何恶劣,那棵小树苗都顽强地生长;不管时间如何久远,不管树冠如何高大,树的心永远在故乡,根永远在故乡的土地上。
偶尔回家,我会用脚重新丈量曾经走过的路,细数路上留下的足迹,回忆路上温暖的瞬间……我爬上后山,来到爷爷的坟茔旁,静静坐在旁边,就像坐在爷爷身边一样。透过爷爷坟前的小树,我仿佛看见了爷爷,他昂首挺胸地站立在大山上,守望着小山村,也守望着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