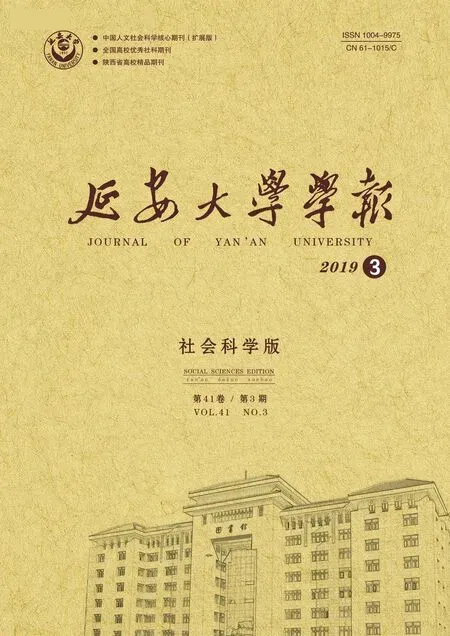中和文化的学术理路与传承
——以儒学流变为基本脉络
陈国庆,曹 松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一、上古中和文化奠定中国哲学基础
自尧、舜、禹禅让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上古文化原创时期,中和概念已经出现并得以应用。在历史文献中,对上古时代明君圣主观察、形成和运用中和之道的记载俯拾即是,其中可见中和文化的发端。
春秋末期,孔子对禅让时代圣君虞舜采用执中之道给予高度评价。如《礼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此处所言“执其两端”,即是防止偏离中和之道的具体方法,以维持“执中”“用中”和“守中”的平稳、协调状态。
记述较早史实的《尚书·大禹谟》写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所谓“允执厥中”,包括治国理政及人们思想言行须符合不偏不倚中正之道等内涵。《尚书·酒诰》中记载周公的话:“尔克观省,作稽中德。”[2]此处所言中德,即为中正之德,是一种道德品性。这种认识被中华文化原创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引入治理天下的理念和社会政教之中。
较早关于“和”的论说则出现于《国语·郑语》所记载的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则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夫如是,和之至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3]470此意为:和能生殖自然万物,同则万物无法繁衍。不同的事物相互交合、相互补充,即称为“和”;那里有“和”,那里就有万事万物的不息繁衍、蓬勃繁荣。单调的声音不动听,单一的颜色没文采,等等。周代史伯及晏婴等人提出和实生物、心平德和、以及可否相济等哲学命题,对中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阐释。这里所表述的和实生物思想,是把不同事物之间相杂、交合看成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和”与“生”的关系,不仅是世界万物生成的依据,而且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阴阳之中和、恰当与平衡,不仅是自然之道,而且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造福社会、实现幸福的人文之道。《国语·周语》里写道:“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3]26此处描述了自然万物皆由阴阳相合相抱而生,乃是自然物的生成和社会治理的天人之道。《周礼》里写道:“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左传·文元年》又有“举正于中,民则不惑”等说辞。这些思想都把人生于天地之中,教民以礼,执中而行,作为天下民生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法则。
综上所引历史文献可见,上古时期圣贤对中和思想进行了诸多论述。其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和基本理念,历经数千年演进变化,形成丰富深奥的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构成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形态的有机要素。就儒家而言,历代硕学鸿儒皆秉承中和文化体系,并有深邃而宽泛的阐发和论说。
二、中和文化基本范式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百家争鸣诸子学说的显学,儒家学者对中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扬。儒家经典《六经》中皆有诸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等关于中德、中和、中行、中正的思想,中和文化并进一步被赋予伦理学属性和美学特征。孔子在上古圣贤论述基础上提出中、和以及及中道、中和、中庸等范畴,并赋予上述范畴以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等内涵,认为“中和”是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学术界长期争论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还是礼的问题,其实只是表面分歧,其思想核心恰是仁与礼相统一的中和。他把中庸、中和、中道称为至德,以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中庸、中和、中道为最高智慧和德性。
孔子在回答弟子问话时曾提出,过犹不及。因为过和不及都偏离了中道,故而加以否定。孔子中和概念里的执中不是折中和调和,不是和稀泥,而是恰当、适度、互补。中与和所表达的都是如何致中和,以及如何执中和。事实上,中和文化在早期形成过程中也是作为统治者立国之道的帝王术,用以维护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在古代历史上,中和文化一直被统治者所垄断,某些圣贤以为中和文化仅为帝王者的德性和职责,而忽略了其民生意义。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和,以达到治理天下、教化万民的统治与政教目的。
孔子的中和文化显然具有政教论意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语:“宽以济猛,猛以及宽,政是以和。”此意为:治国之道在于以宽厚与严峻相补充,如此则政事和美、人心安定。所谓宽,即宽松仁厚;所谓猛,即严厉峻苛。治国之道,宽则百姓心情舒畅,无所顾忌,敢说敢言,易于造成一种宽松气氛。但一味地宽,则易使乱国者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混乱,影响秩序安定。猛,可以严肃法纪,使乱国者慑于法纪威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但一味地猛,又易于使陷入绝境者铤而走险,或使百姓胆怯懦弱、心有余悸,不易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唯有宽猛相济、恩威并济才能发挥各自优势而去除弊端,形成稳定安宁的社会局面。
孔子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为例,提出一系列判定原则或标准,“中庸之为德也”“君于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何分辨并取舍和与同、周与比、泰与骄、矜与争、群与党,正是在社会伦理等领域如何实现中和的具体方法。这也体现了儒家一贯提倡的所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和文化。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也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论语》里随处可见有对立着的两种极端状态的分辨和取舍、和谐与协调。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由“仁”“礼”“中”三个基本范畴为核心而构成的。其中,仁是道德哲学,礼是政治哲学,中是纯粹哲学,是作为用中之道的最高方法论。此三者之间互通互融,或称为三位一体,亦无不可。中和文化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世界观。在“仁”“礼”“中”三者之间,正是中构成并反映了仁和礼的本质与原则。孔子说,“礼者,所以制中”。[4]这就充分说明,“仁”“礼”“中”,是孔子学说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思想体系。
荀子明确提出中和概念:“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5]把“中和”提升为判断是非的道德法则,是对中和文化的政教观、伦理观和方法论的深刻阐释。
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此书开篇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对中、和及中和概念和文化的系统论述,使其作为本体论和自然观而得以呈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建构了中和文化的框架,为后世儒家论述中和文化之滥觞。例如,受儒学影响极大的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对《中庸》那段经典论说做如此评论:“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吾顺之者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臣也,夫如是,则伪不起矣。”[6]此意为,君子应以中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努力改变社会现实,恢复或重建天地自然的原有秩序。这是以中和文化改造世界的观念。由此可见,中和文化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有学者提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句应为天地各得其位,万物自然发育的意思。此意与《中庸》涵义似无实质差异。在儒家学者的认识上,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皆应恪守中和之道,中和是宇宙自然观和本体论,更是社会政教论与道德伦理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
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先贤圣哲们,基于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从救世的社会责任出发,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具体思路,并通过实际行动积极践行。但在那个时代,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霸道盛行天下,僭越之事时有发生。因此,无论孔孟的“仁”还是荀子的“礼”,都没有可以践行的社会土壤。然而,先哲们关于社会政教与伦理的探讨,毕竟建立了中和文化的基本范式,并赋予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由此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雏形。
三、汉儒对中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汉儒继承并创新先秦儒家学说,以为中和文化是宇宙自然本性之天道,故而将宇宙自然及阴阳五行作为中和文化的主体形态。董仲舒是汉初重要的代表性哲学家。他以阴阳中和作为宇宙万物产生及发展的根本,“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地大盛。”[7]159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立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认为,“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天人同类”“同类相感”“非有神,其数然也”[7]128,这是事物内含的定数所决定的。这个“定数”就是规律和本质。上天的意志可以通过某种祥瑞或灾异显现出来,这也是对中和文化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天人合一的概念较早由庄子阐述,随后被董仲舒发展为中和宇宙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即所谓以阴阳中和作为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根因。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既是宇宙观,又是价值观,还是最高明的治国之道,是最适宜的养身之道。如此,便达成了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这是说,天是宇宙自然的大世界,人是与自然相互沟通的小世界,一切人事皆应与自然和顺,遵循自然规律,此即为中和状态,既符合“中”的规律,亦呈现“和”的状态。董仲舒也将中和文化作为政治之“和”,“中”与仁、义、礼等互为作用,这是中和作为方法论的互助互补的具体途径。自此以后,“中和”成为中华文化圣圣相传之道统,体现为政通人和的政教观,执着追求的价值观和熟稔运用的方法论。
四、宋明儒学对中和文化体系的建构
宋明儒学对中和文化体系的建构,贡献颇著。朱熹是孔孟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和理学集大成者。在中和的认识上,他秉承所谓“平常论”与修养论之统一。他解释“中庸”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8]他较为详细地辨析《中庸》所谓“未发”与“已发”“性”“情”与“心”等概念,在他的认识上,所谓中和,就是已发未发的问题,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在修养方法上进行更加切合实际的探索,例如他提出“居敬”的修养方法。他从参悟中和的已发未发问题,梳理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的修养方法。这种认识属于感悟与意识问题,可能带有主观色彩。
“中和之悟”是朱熹在理学修养论方面的一种探索,他的“中和论”对其“心性论”的确立,以及其思想体系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事实上,朱熹关于中和文化的探究,与其说是单纯的学理或理论的探讨,毋宁视其为一种道德践履、意识参悟或价值功用。朱熹在《近思录》中认为,凡天地间皆有两端。这种凡物必有两端的中和文化在中国哲学史上屡见不鲜。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人着力探索和追究宇宙天地万物自产生、存在到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规律及其依据,把天地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无形无象的抽象物,并以其表现天地万物之间的共性和根本差异,这种抽象物往往用中和加以概括和表达。在古代哲人的视界和话语里,“中和”是宇宙本质及其大化流行的根本规律,所谓“和实生物”即表示宇宙万物得以生成和演化的源泉及其存在方式。
对“中”“和”“中和”这三个概念,宋明理学家有着独到理解和阐释。其实,中、和二者并非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而是互为体与用的关系,即“中体和用”与“和体中用”互通,朱熹的“中和体用说”似乎另有其论述的规定性,或者特定视域。他以为,“天地之性浑然而已,以其体言之,则曰中,以其用而言,则曰和。”“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时指已发未发而言。”[9]于是,在朱熹的观念里,中与和成为中体和用之二者合一的命题。
其次,朱熹从宇宙本体的“天地之中”转变或过渡到心性本体的“未发之中”,再经过所谓“致中和”的修养工夫,便实现了由“未发之中”到“已发之和”的超越,从而完成了构筑涵养心性以安身立命的中与和之间体和用的对接及转换。事实上,中与和是互相渗透、互相兼容、互相交融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往往是中包含了和,而和也包含了中,它们互为体用。
五、结语
中和文化首先源自于自然界万事万物,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自然万物存在与演变状态长期观察和准确认知后的归纳、抽象。“中”之本义即中间、中央、居中,这是自然万物的实然状态。就中和文化的本体论属性而言,宇宙自然万物有左右、高低、前后、顺逆、闭合;人类社会有优劣、智愚、贫富、尊卑、强弱,但在对立着的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以及或宽阔或狭窄的过渡状态。“中”是存在于两极之间的状态,也是通向两极的桥梁,由“中”而发,则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基本途径,其中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孕育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发展场景。
作为宇宙自然万物的“中和”,主要表现为阴阳之中和,即既不偏向于阴,亦不倾向于阳,而是处于阴与阳之中。其实,阴与阳之中即为和。此处的“中”并非绝对的二分之一处,而是阴与阳的适合、恰当与协调状态,不是绝对的阴,不是极端的阳,也不是阴与阳各具二分之一的平分。由中而生和,因中而致和,是世间万物生成和发展的逻辑。
阴阳之调和是规定和影响自然万物的决定性因素,阴阳之结合是化生自然万物的发端,阴阳二气相互融合而成新的融合体。这就是“中”,也是“和”,以及“中和”。事实上,中和的本体论价值首先在于描述与探究宇宙之中和,表示宇宙万物或客观世界的各个层次、方面、领域及诸因素处于中正、恰当、统一而协调状态,决定人们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遵循其规律。“中和”表达了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或客观世界的中正平和状态,并进一步引申到社会领域。
中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是固定不变、平静僵化的状态。《易传》把这种状态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的“道”就是中和之道,指阴阳二气聚散消长、升降沉浮与冲突转化的平衡状态。王夫之在《张子正蒙记》里写道,中和就是体与用、动与静的辩证协调,也是万物理想的生存状态。它阐明和透视了万事万物对立面与异质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向和平衡、互补、有序的本质属性。这种认识与朱熹的观念有某些相近之处。
一般而言,基于人类感官及一定思维过程而作出认知、理解、判断或选择的观念被称为价值观。其是人类判定事物、辨别是非、表达立场及呈现观念的思维或价值取向,体现人、事、物的价值或作用,代表人或群体对事物的评价。例如,对幸福、尊重、平等、服从和良莠等,依照自己的观念加以轻重主次高下评判。
如前所言,中和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往往被人们加以应用。“中”“和”“中和”表达了人们的行为符合特定的应然要求和理想状态。传统观念中的中,往往被应用于社会实践,实现其作为方法论的价值。例如,中,表现为执中、用中、立中、致中,等等;和,则表达了和的行为及和的结果。天人合一不仅是天与人之间简单地合二为一,而且是天与人的恰切融通、协同与共的关系。
中和是事物相反相成而达到的状态,这是两个平衡点,事物保持着均衡、有序、稳定的关节点。致中和,即要求人们充分认识事物的不同方面,尤其是事物的对立面,实现对事物的中和的把握。
总之,从梳理儒学流变过程中,就文献资料所述可知,“中”“和”“中和”是三个既联系又区别的哲学范畴,且内涵与外延各有其自身规定性和变异性,与中庸、和合、中行、中道、中德等概念相近却不简单地等同。“中和”之“中”不是绝对化的折中,也不仅仅是无过无不及;“中和”之“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也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简单的和合或和谐,而是包含有更加丰富与多样、广泛与深奥、稳定与变异的哲学语义。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以及其他诸家学者皆有对中和文化的论述。不仅如此,历代志士仁人也极为推崇中和文化,并以此置身社会、涵养心性。可以说,“尚中贵和”学说极大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状态、心理品质和性格特征的形成,导引中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优化及演进,并成为中华民族智力的重要宝库和支撑力量。
中和文化是用以协调人与人、群与群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智慧和帝王治天下的政教观,这是人们为祈求圆润融通、万邦协和的大同境界而做出的探索,也是个人达成中正平和、宽容大度的道德涵养之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