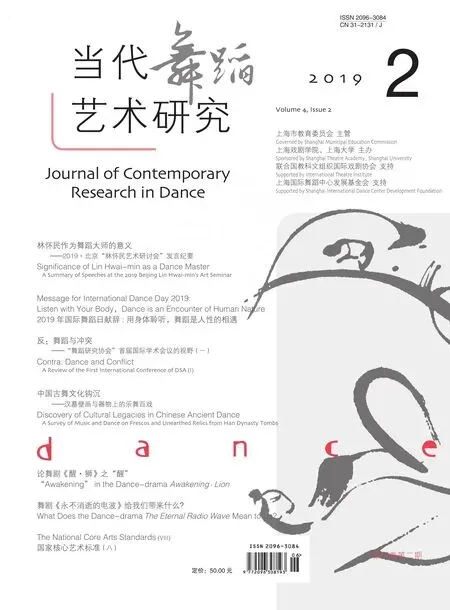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的艺术价值评析
董 丽
一、以再现与重构的方式诠释经典
电影《闪闪的红星》深深打下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而舞剧《闪闪的红星》对电影的再现与重构,一方面表明了欣赏者对“经典电影”改编的接纳和认同,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舞剧创作者看“经典电影”的独特眼光。舞剧《闪闪的红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它既保持了电影创作对艺术经典性维度的追求,又使之焕发出与电影艺术迥然不同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电影版还是舞剧版,《闪闪的红星》都秉承了红色经典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思想性的创作理念,但是两者在形式表达方面又有着根本不同。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电影《闪闪的红星》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创作的艺术作品,不自觉地将“革命的想象”附加在人物形象之上—将主人公潘冬子塑造成为一名近乎完美的“成人式的儿童英雄”,以满足受众审美心理的需求。而舞剧《闪闪的红星》没有将英雄人物“脸谱化”,它重在刻画一个男孩的心理成长历程。一个曾经懵懂的少年,在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之后,手握着红色五角星,逐渐将对其的情感凝结成心中不变的信仰。可以说,舞剧版的人物形象塑造更符合艺术创作人性化的特点,在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因为人性的真实使得舞剧具有了时代审美特征。此外,意象化的表现手法也是舞剧创作的一大亮点。通过创作者的匠心独运,那枚“红星”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舞剧中的“红星”没有作为单纯的道具出现,而是幻化成一段段女子五人舞,伴随着不同的情境营造出不同的意境。笔者以为,意象化的“红星舞”是舞剧《闪闪的红星》最精彩的创造,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予观众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心理想象空间,也使得舞剧在精神旨意上得到了升华。
二、以简洁与丰富的视角演绎当代
身处信息与快节奏时代的我们,人际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悄然发生着改变。舞剧《一起跳舞吧》把创作视角转向当代普通都市人,以一对白领夫妇通过“跳舞”走出情感隔膜为叙事主线讲述当代都市人夹杂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生存现状。看似简单的主题背后,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虽说“器有形”而“道无形”,但是《一起跳舞吧》“以简驭繁”的艺术创作手法却使得“道似无形却有形”。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化解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属于个体的孤寂感?舞剧《一起跳舞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走出心灵困境,寻找精神希望之所在。此外,舞剧没有将叙事视角局限在男、女主人公上,而是成功地刻画了一群现代都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之情。整个舞台呈现的是一幅幅市井图,描绘的是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但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不正是靠这些芸芸众生所凝结的力量所推动的吗?舞剧的创作者正是以这种宏观的视角为我们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且具有深刻哲思意味的叙事脉络。这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形式,不仅聚合起作品的情节,给主题以有力支撑,还实现情节书写与哲思表达的和谐统一。《一起跳舞吧》为我们开创了舞剧创作的新思路。
三、以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勾勒未来
判断一部艺术作品良莠的关键在于看它是否解决好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既要呈现传统艺术的审美经验又要与当代文化境遇相关联。然而,现实中传统艺术审美与当代文化境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带,这个断裂带不会自己弥合,它需要一种介质来连接。舞剧《朱鹮》正是通过并置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创作途径,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对这种“断裂”的弥合。
“穿越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类型风靡网络,已成为当下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它具有自由、冲突、荒诞的美学特征。从剧情架构上看,《朱鹮》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说“古”,下篇论“今”。“古今”转换之中,以“信物”— 一片朱鹮的羽毛作为贯穿。用这种完全符合“穿越小说”言说方式的创作手法来架构舞剧,不可谓不前沿。而这种大胆的创作手法应用于舞剧创作却也体现了其优势所在:不仅能满足观众对历史的认知需求与对艺术的审美需求,让其更好地在同一坐标轴上审视不同历史褶皱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能够直抒胸臆,呼唤当代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另外,从舞蹈语言上看,“风格迥异”可谓《朱鹮》的标识。上篇言“古”—“古典舞”的气质清晰可闻,创设了清秀而甜美的传统审美意境;下篇说“今”—“现代舞”的形态挥洒自如,灰暗而压抑的气氛呈现出现代审美质感。客观地说,《朱鹮》用前沿的风格创造出的舞蹈形态语言的变换不仅不突兀,反而能让观众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了解整部舞剧的叙事逻辑、梳理出清晰的剧情。这种将传统审美与当代文化境遇进行深层融合的创作手法,既延续了传统审美的生命力,又明确了《朱鹮》的题旨:期望未来能够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