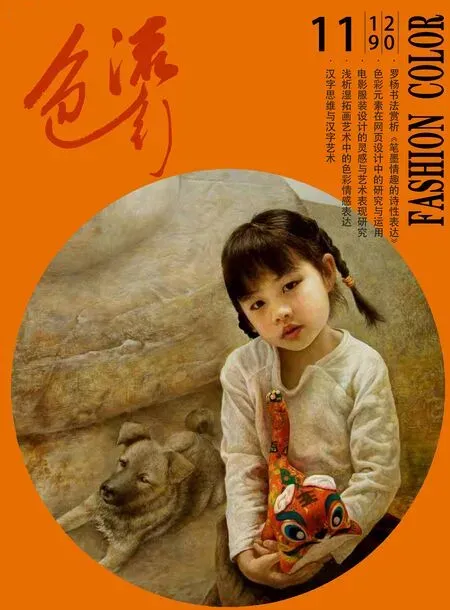选秀节目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邓冰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的选秀节目模式经历了几代更迭。时代环境的变化带来了节目模式的变化,不同节目中选手的形象,也是时代环境和人们观念的缩影。
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传统选秀节目模式和以腾讯视频《创造101》为代表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节目模式。同是为女性选手提供的选秀平台,其女性形象及其背后传递的意义,有大相径庭也有巧妙的重合。
一、《超级女声》和李宇春——大众文化的文化符号
2004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横空出世,打破了原有的声乐比赛节目的形式,极强的参与感和颠覆传统的选秀模式使其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娱乐盛事,也奠定了此后国内音乐选秀节目的基础。
《超级女声》的前身是湖南娱乐频道一档名叫《超级男声》的电视赛事,2004年转入卫星频道举办后,便一直是女性声乐比赛,直到2007年才推出《快乐男声》,这本就带有深意。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女性不再受家庭的束缚,而是可以走出家门,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但是,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传统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依然牢牢地扎根在人们心中,甚至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年轻人中,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急需通过传播手段树立新的女性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女声》这档声乐节目应运而生。
2005年是《超级女声》获得盛大成功的一年,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公布的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收视数据表明,该节目收视率高达11.749%,至今没有同类节目能够超越。当年在总决赛拔得头筹的选手们,如今依然是活跃在一线的超级明星。但是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超级女声》无疑带着某些叛逆的元素。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十强选手中,包括冠军李宇春、亚军周笔畅在内的四名选手,都是偏中性的形象。她们留着和男生一样的短发,穿着背心、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带着黑框眼镜,从不穿裙子,嗓音或低沉或粗犷,但绝非甜美温柔。而就是这样的李宇春和周笔畅,在那个通过短信和电话投票的全民参与的娱乐盛事中,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人气王”,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标签。同时那也是一个“恶搞”文化盛行的时代,李宇春在收获人气和成功的同时,也成了被“恶搞”的对象,被称为“春哥”,意为讽刺其没有女人味。
其实,无论是李宇春、《超级女声》还是“恶搞”,都是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产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是精英文化凌驾于大众文化之上。学者朱大可曾说,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大众文化统领精英文化的年代。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思想的传入,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展开了博弈。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终于获得了反攻精英文化的机会,《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缩影。它一反CCTV青年歌手大赛一样的声乐比赛模式,主张“想唱就唱”,打破年龄、唱法和专业性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站上舞台。它也不再让专业评委掌握唯一话语权,而是将选择更多地交给观众,让大众投票选出真正的平民偶像。而在如此理念下的《超级女声》中诞生的“超女”李宇春,无疑是那个时代女性呼唤解放的一个文化符号。女生也可以不留长发、不穿裙子,不受刻板印象的束缚,成为独立勇敢的新女性。它反映的是新一代青年渴望解放自我表达自我的集体诉求,是青年亚文化反叛基因的一种外化的体现。
二、《创造101》和杨超越——偶像产业中的文化产品
《超级女声》之后,众多音乐选秀类节目层出不穷,但都未脱离“超女”系列的模式,也鲜有为大众记住、引发社会热烈讨论的选手,直到2018年。
2018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偶像元年”,原因在于这一年诞生了多档同质化的偶像养成节目,如《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这类节目的原版是韩国《Produce 101》,是练习生同场竞技出道机会的真人秀节目。它与中国的“超女”模式存在许多区别。它完全取消了评委的决定权,而把决定权全部交给屏幕前的观众,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在节目模式上,“超女”依然是一场在演播室完成的竞技秀,但是101的主要部分是真人秀,舞台竞技只是真人秀的一部分。
十几年过去,虽然同为年轻女性,“101”式的偶像和“超女”时期的偶像也大相径庭。首先,“101”模式不侧重个人,而是以团体为概念。公司选派的练习生多为组团出战,在节目中练习生们也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组队,然后进行团体表演。最终通过节目选出的优胜者,也将被经纪公司包装为偶像团体,而并非个人歌手。虽然每位选手依然具备自身的特点,也有各自的粉丝群体,但是每个选手都是偶像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因此她们的风格多为趋同,而缺少个人特色。究其原因,“101”模式是韩国练习生演艺模式的产物。几乎每个娱乐公司都有新秀练习生储备,公司根据规划会定期进行选秀,有着相当成熟的流程。
除了由个人变为团体之外,女性形象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创造101》中,我们再难看到如李云春、周笔畅一般的男性化形象。在《创造101》最后成团的11名选手中,除了选手Sunnee是中性化形象以外,其他女生无一例外都是长发、短裙、长腿的甜美形象,符合刻板印象中对于女性的柔美温顺的标准。例如,《创造101》的热门选手杨超越,在练习唱歌和跳舞时,由于跟不上其他选手的进度,因此崩溃大哭,在节目的其他地方也经常落下眼泪。这样的行为反而让许多观众觉得她很真实,因而收获了较高的人气。这是因为杨超越的行为符合了观众心目中对于年轻女性一贯的印象,即柔弱、爱哭、天真,更能激起观众心中的保护欲和对自我的投射,产生认同感。
“101”模式中的选手会呈现出这些变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们选出的还是符合偶像产业链的营销产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偶像”这个词的内在含义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就如“偶像”这个汉语词汇本身,是处于神坛之上的。尽管“超女”们相较于以往的著名歌手、港台明星要更平民,那只是因为她们来自“草根”而已,观众对于她们的平民身份是有认同感的,这也是这一类偶像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但是在如今偶像产业已经渐趋成熟化、标准化、模式化的情况下,偶像养成节目只是产业链中的一环,而“偶像”便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产品。虽然“超女”的成功也催生了中国偶像模式的发展,但是当时仍处于探索阶段,观众对于“偶像”的看法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如今,观众十分清楚和认同自己消费者的身份,明白“偶像”不是神坛上被供养的神圣之物,而只是用来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商品。消费者通过节目中的投票实现了产品的购买,因此希望偶像能够满足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这就对作为偶像的选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能肆意地张扬个性,而是要符合大众心目中的标准。这也是节目制作的目的,要建构能够满足观众需求的标准化的偶像。
这一点也导致了女性形象的变化。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稳定,社会文化不再处于矛盾激烈期,取而代之,现代年轻人的主要矛盾,是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孤独感。青年观众不再需要像李宇春那样反传统的偶像来引领新的风潮;相反,他们只是需要符合心目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选手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就是温柔、美丽、大方。他们渴望陪伴和内心的满足,而偶像这样的文化产品正好能够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
三、选秀节目建构选手形象的手段
李宇春之所以为“李宇春”,杨超越之所以为“杨超越”,一个普通的女孩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与选秀节目在策划和制作中的方法是分不开的。选秀节目找准每个选手自身的形象和特质,然后通过一定手段进行包装,使其成为能够引领潮流、获得观众喜爱和追捧的偶像形象。
首先是良好的舞台表现。选手的个人表演能力,加上合适的编排和包装,是优秀选手能够树立个人形象的根本。李宇春在《超级女声》的代表作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原曲是一首由南美洲音乐家创作的老歌。她带有特色的女中音与这首歌的异域风格相得益彰,与其他选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李宇春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独特的个人风格也成了舞台上靓丽的风景线。值得一提的是,李宇春版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这首歌的字幕也是女字旁的“她”,更加重了选手的中性形象。反观《创造101》,很少有这样不拘一格的舞台表演,各种群体表演都能被归入可爱、性感、帅气等类型,展示的是女性不同阶段的魅力。即使是帅气风格,也是像《木兰说》舞台这样突出女性表现“巾帼不让须眉”的帅气,与男性的帅气风格有很大差别。
除了舞台表现以外,选手的谈吐也是重要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声乐比赛,各种音乐选秀节目中,选手总是有大量机会可以说话,表达当下的看法。舞台表演通常只占了节目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各种各样的交流和谈话。谈话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选手的谈话能让观众觉得他们不是只会唱歌跳舞的傀儡,而是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选手和观众的距离,让观众产生认同感。
最后,选手在真人秀中的表现也是树立选手形象的重要手段。早期的选秀节目都以舞台竞技为主,真人秀的部分只能在选手的宣传片以及一些衍生节目中展现,但是在如今的偶像养成类节目中,真人秀成为了节目的主体。这也是由观众的身份变化带来的。真人秀为观众提供了上帝视角,使其能够看到选手的日常生活,满足其窥视欲。作为消费者的观众能够观察作为商品的偶像的生产过程,挑选最符合自我期待的选手。生产过程,即节目塑造选手形象和人物性格的过程。如前文提到的《创造101》的选手杨超越,“爱哭”的形象深入人心,天真柔弱的小女生形象通过她的这几次哭泣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的选秀节目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今的选秀节目经过十几年跟随市场环境和传媒环境作出的改变,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不同时代的偶像反映的是不同时代青年的心理需求,因此选秀节目需要以最敏锐的探知力和创造力不断完成自我的更新,以打造出符合受众需求的偶像,以实现经济效益,偶像形象正是这种变迁的外化和体现。选秀节目作为如今综艺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靠极强的传播能力,带给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社会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