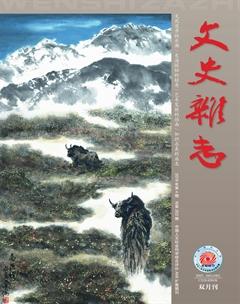试析晚明困局与困局中的叶向高
赵映林
关键词:晚明困境;叶向高;万历怠政;争国本;矿监税使;群体事件
一代明清史宗师孟森在总结明亡历史时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德)、嘉(靖)以后,至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20)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1]历史经济学泰斗李文治在总结明亡时强调: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怠政聚敛使得政治一团黑暗,终于引发农民造反走向败亡。[2]至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取此说更为大家所熟知。此时,明朝建国已有200年出头的历史了。经历了200余年的明王朝到了這一时期已经是风雨飘摇,偏离了航道,在困局中苦苦挣扎。这其中支撑这一困局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叶向高。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其父叶朝荣曾任广西养利知州。万历七年(1579年)叶向高中举,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内阁首辅沈一贯不喜叶向高,故最初叶向高仕途并不顺畅,在南京坐了多年冷板凳。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初,包括沈一贯在内的两位大学士都被免职,内阁仅剩一人;次年五月,叶向高出任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奉调入京,与王锡爵、于慎行和李廷机三人同时入阁,为最末一名内阁学士。然而,机缘巧合,叶向高入阁一年就成为首辅。先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叶向高入朝不久,于慎行已经过世半年,王锡爵坚辞不至,李廷机到任也就几个月,就养病不出,挂着个空名(直到万历四十年退休);接着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首辅朱赓过世,于是,叶向高这才顺理成章地继任为实际上的首辅。而此时的万历皇帝,统治这个王朝已37年了。
这时叶向高面对的明王朝是千疮百孔,腐败充斥,暴政肆行,内忧外患。放在叶向高面前的困境,一是财政危机,一是皇帝怠朝,一是政治危机,一是辽东战事。就这么一个烂摊子,因为万历长期不补缺额官员的原因,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不得不以一人之力独立支撑内阁长达七年,被人称为“独相”。其主政期间的奏疏约850封,结集为《纶扉奏草》(30卷)、《续纶扉奏草》(14卷)、《后纶扉尺牍》(10卷)。其任“独相”时的奏疏集中在《纶扉奏草》。而《蘧编》(20卷)为其自编的个人生涯的编年纪录。
财政危机日甚一日
先说“独相”面对的财政危机。明代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宫廷支出、宗藩支出、俸禄支出、军费支出、教育支出、水利建设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计七大类。明代中央财政,从嘉靖时期(1522—1566)开始就相当糟糕,最高的一年(嘉靖三十年)太仓库(明英宗正统后专用来储存银子,即后世所称的国库,其银俗称太仓银)亏银395万两。明代财政收入分存四个部门(另三个部门分别是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库、光禄寺库),财政收入的大部银两(不含实物)是入户部的太仓库,主要负责中央一级开支。这种年年亏损状况在万历前期略好些,万历前期因张居正改革,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如万历五年(1577年)太仓库盈余865200两,共有900余万两白银储存(还不含节慎库、太仆寺库和内帑存银),加上南京库房有250万两,就超过1150万两。[3]各地方政府也有存银,多寡不一而已,如广西、浙江、四川等省存银平均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就中央政府来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盈余723300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盈余20万两,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入不敷出的亏空趋势。随着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虽然时赢时亏,但大多年份仍是亏空为多,收支平衡年份少,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太仓库亏银100万两、万历二十年(1592年)亏953000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亏50万两,最高年份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亏203万两。[4]地方财政情况也开始不容乐观,很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库银日见其少。出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计六奇回忆说,张居正秉政时,“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可在清算了张居正后未出二十年,就财政日蹙,“无可支吾,赋加民贫”。[5]
在所有支出中,最大的是军费开支。隆庆(明穆宗年号,1567—1572)初年,军费开支不过280万两,此后,一年比一年多,万历中期增加到380万两。除此之外,碰上战事,又有临时战费支出。万历二十年后,征讨宁夏、朝鲜、播州(贵州西南地区)三地,号称“三大征”,耗费白银1000万两。之后的辽东战事更是让万历年间的财政雪上加霜,总计用去6000万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万历积年不补缺官员,与财政困境有关,一厢情愿想以此来减少政府开支。可见已是病急乱投医。
其次是宫廷宗藩开支,主要是直接为皇帝及后妃服务的开支,包括帝后日常生活之费、帝后巡幸、庆典、赏赐之费,还有宫中人役(太监、宫女、匠役)之费、帝后宫廷陵寝之费,以及宗藩、公主支出。万历年间,帝后的各项开销每年需30万两白银。万历中明神宗为自己修建定陵,耗资800万两。[6]明神宗营造皇宫三大殿,仅采木一项耗银930万两;到天启(明熹宗年号,1621—1627)末三大殿完工,共耗费白银5957500两。至于皇子册封、藩王就藩、公主出嫁,也是一项惊人支出,如为皇长子(后来的明光宗)和另两位皇子册立冠婚礼,耗资1200万两。[7]
明代宗藩到了万历年间,由洪武中叶的亲郡王以下男女58位,增至103000人,[8]宗藩支出成为明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大重负。对这个问题,朱元璋在世时就已发现。他鉴于自己子孙众盛,觉得诸王岁禄标准太高,重新作了规定,降低原有标准,如将亲王岁禄米由5万石降至1万石,郡王岁禄米由6000石减至2000石,最低的奉国中尉岁禄米200石,比从四品还少2石。到了明晚期,少数的藩王岁禄落到2000—1000石。[9]即使如此,由于宗藩人口众多,除岁禄米以外,加上宗藩的其他开支,以及皇室的奢靡无度,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矿监税使瘠民肥己
财政困难的后果是矿监税使(矿指开矿,税是店税,两项合称矿税)四处出动,加大对民众的盘剥。征税名目花样百出,搞得民不聊生。最直接的突出表现就是腐败之严重。这一时期,叶向高面对的是法纪废弛、贪腐成风、吏治败坏,已成不可救药的溃败之势,其腐败而又以矿监税使为烈。史家将矿监税使的贪腐搜括手段概括为:督民开采,坐地分赃;包矿牟取;重征迭税;私加征税对象和名目;以包税借名掠夺;攘夺和敲诈;实行矿税以外名目的掠夺,达七种之多。[10]矿监税使的四出掠夺,国库没进多少,大头都进了皇室内库和这批矿监税使腰包。时任礼部侍郎的冯琦指责矿监税使是“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11]矿监税使的贪腐不仅导致地方官与他们的矛盾冲突,更是直接引发了无数“群体性事件”,造成官逼民变的局面。当时有朝官说:“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12]这些群体性民变,在万历后期,遍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云南、福建以及江浙一带,成为20年后敲响明王朝丧钟的明末农民起义的预演。
对万历皇帝四处派矿监税使的敛财措施,叶向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一再上疏陈说厉害,“极言榷税之害”,希望召回矿监税使。其对因反对矿监税使受到迫害的官员则竭尽全力予以救赎。[13]
皇帝怠朝任百川自溃
万历皇帝亲政后,对改革派大臣、内阁首辅张居正等进行清算,使之切切实实控制了朝政;但他又不愿意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使自己困于治理。所以,在否定张居正所为时,万历帝又一再强调不要翻旧账。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其结果是直接导致朝臣争论不休,在相互指责、攻击中漸成朋党。伴随朋党的逐渐形成是皇帝本人的怠朝。可以说,万历帝的怠朝(万历十四年后)与朋党之争是互为因果的。对万历帝的怠朝,叶向高十分感慨地说:“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浮沉其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然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嗅,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14]叶向高于此深刻揭示了万历帝怠朝的严重后果,可皇帝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致使朝政长时期陷于停顿状态。因为不批奏章,遂致政事不决。如吏部上奏要求给缺官衙门补官,万历帝却来个不理不睬,奏章留中不发。皇帝不批复,吏部就不能自行其是擅自任命官员。中央缺员严重,地方亦是。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12名尚书缺3名、24名侍郎缺10名、科道官(监察官)缺94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缺66名,知府缺25名。至于县里缺官更严重,有的县城已经七八年没有知县了,去衙门办事经常找不到官。连带着官司都没人审,专门负责写状纸的讼师,好多也都改行干别的了。甚至有些判了死刑的犯人,因为复核死刑的官员缺员,关在牢里十多年竟然无人过问。全国御史巡行差务共13处,有9处缺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缺官情况更严重。南北两京各衙门,大半空署无官,如北京中央部院正职应有9名,却只有3人,6个中央行政部门没有正职负责;地方督抚重臣,常年空席,布、按两使缺员近60名,府一级地方政府缺知府近50名,严重时缺知府75名。特别是监察部门,如南北两京都察院堂官应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共6名,然而仅有1名任职,缺5名。至于内阁就叶向高一人独力支撑。[15]吏部尚书孙丕扬再三上疏请皇上补缺,不听。因皇上不表态,所选官员“无从领凭,哀号长安市数百人”[16],数百人无法上任,坐吃山空,只能哀号于市。孙丕扬一气之下,上疏乞休,可万历帝明白,倘若孙丕扬致仕,整个吏部可就瘫痪了,于是就批了两字:“不允”!为此,孙丕扬前后上疏二十余次,仍不能改变万历初衷,于是干脆称病不出,直接“罢工”。[17]孙丕扬敢于坚守职责,与皇上软顶,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首辅叶向高的支持。针对官员补缺与增补阁臣一事,叶向高自己所上奏章“至百余上”[18],这在《纶扉奏草》中都可以数出来。
衙署缺官的直接后果是公务堆积,无人处理,久拖不决,小事衍成大问题而积重难返。如刑部长期缺掌印官,狱中关押了1000余囚徒,竟无人审理,以至于新捕犯人无监狱可关。[19]其中最严重的是由于长期缺官形成门户之见。先是监察部门官员上疏就朝廷用人不当言事,这就势必牵扯到具体人事,如都给事中林材上疏指责用人不当,直接点了国子监祭酒顾宪成、吏部侍郎刘元震等多人的名,而这些人中恰恰就有在无锡东林讲学的人物。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久之使得东林书院成为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此,“东林名大著”,这批人就被其政敌视之为东林党。[20]与东林党对立的官员在与其矛盾冲突中,因地域的不同,形成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楚党等。万历年间朋党之争的结果,到天启年间是邪派官僚势力彻底压倒正派的官僚力量,使得官场腐败之风如江河直下再也不可挽救,引发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终至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所以,后世有观点认为崇祯亡国,崇祯帝本人却非亡国之君。
宫斗党争不断的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是由明神宗不遵祖制、不守规则,偏爱私心引发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争国本”后引发宫中大案的频繁出现和朋党之争。万历年间发生过四件大案,一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忧危竑议》妖书案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续忧危竑议》妖书案,统称妖书案。此案的实质是万历宠妃郑贵妃借事打压宫内外的政治对立面。最有名的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俗称明末“三案”。移宫案类似妖书案,有两起,前一起发生在红丸案之前,但波澜不惊,只可算是个前奏。后一起则与红丸案相接;牵扯大,可以算是正案。加上妖书案之前的争国本,和始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乙巳京察的党争,以及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后开始加剧的朋党之争,中间又夹了个巫蛊案——整个万历朝从张居正被清算后,只过了近十年的稳定日子,之后就没消停过。
晚明三案,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间,叶向高于头年八月已退休在家。所以,此案发生后,越闹越大,万历皇帝叹息道:“叶向高在,事不至此。”[21]红丸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九月间,万历帝于这年七月中驾崩,朱常洛继位,即明光宗(年号泰昌)。叶向高这年八月奉召再入阁,快到十月底才到任。
“争国本”是万历朝发生的一件大事。万历皇后无出,宫女王氏生下朱常洛,是长子。万历帝是一时兴起把宫女王氏“临幸”了,后来还想不认账,在太后的干预下,让内侍拿来记载皇帝生活的“内起居注”,你跟哪个妃子、宫女睡觉,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万历帝赖不掉了,只得承认此事,于是不得不封宫女王氏为恭妃。而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的是皇三子朱常洵(就是后来被李自成杀死的福王)。因为万历帝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也就喜欢皇三子;又因不喜王恭妃,亦自然不喜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帝在郑贵妃的影响下,总想废长立幼,遭到朝臣们的竭力反对。在帝制时代,太子被视为“国本”,围绕废长立幼的这场政争就被称之为“争国本”。争国本经过15年的无数回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告结束,朱常洛勉强被立为皇太子,成为皇位继承人。这场激烈的政争影响实在太大,有四位首辅和十多位部级高官离开,牵涉其中的各级官员三百多人,有一百多名被罢官、解职、发配,并且在激烈的争论中孕育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东林党。此后的党争直到明亡也未能停息。在争国本的过程中,因叶向高是朱常洛的老师,自然要站在学生这边,且是铁杆。在皇太子确立后,叶向高仍未敢懈怠,总是千方百计说服万历帝让福王早日就藩,以稳固太子的地位。在这场争国本中不少官员遭贬,叶向高却毫发无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的上疏在任何时候都用语平和,注意不去激怒皇帝,即使动用了封驳权;二是他个人道德品质为皇上所重。《明史》本传说他“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为世人推崇,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东林党党魁。其实,他只是在品德上一直视东林党人为君子,有好感,倾向于东林党人而已,谈不上是东林党;尽管《东林点将录》列有其名。叶向高“好扶植善类”,如上疏竭力替为官清廉,嫉恶如仇,遭到贪官污吏忌恨、陷害的礼科给事中王元翰辩护。在整个政争中受叶向高保护的正直官员有相当一批,这也就保持了朝政没有完全落入邪恶之手。待到叶向高辞职,再也无人能够遏止魏忠贤与阉党,遂致东林党一派官员几乎全军覆没。
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时,巫蛊案发。锦衣卫百户王曰乾上书万历帝,说有三个人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上、皇太后圣号,皇太子的生辰;在这三个纸人身上分别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钉子,摆设香纸桌案和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又念咒语又烧符,七天后将这三个纸人烧了,收坛相聚。这其实就是西汉武帝时巫蛊术的翻版。王曰乾在疏中揭发,做这个事的三个人是受太监姜丽山的指示,而姜丽山是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宫中的。万历帝见疏大怒,叶向高遂建議冷静处理。他在密揭中强调王曰乾的奏疏不宜发下,称一旦王曰乾的奏疏泄露,就会上惊太后,再扰太子,郑贵妃与福王也会不安,不如留中;只要让法司治这些奸人罪,让其消失,天下就无事。叶向高的密揭说服了心神不定的万历帝,遂转怒为喜,怡然说道:“吾父子兄弟全矣!”[22]叶向高此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这场可能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政治危机得以妥善解决。第二天,王曰乾悄无声息地死在了牢里。对这一真假难辩的案件,叶向高以不审理,不追查的方式了结,采取与妖书案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避免了殃及无辜、人人自危局面的发生。
巫蛊案牵涉到郑贵妃、福王。围绕“争国本”,宫里宫外已闹腾了整整15年,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被牵涉其中,郑贵妃、福王母子一直处于漩涡中心,搅得朝争不断,影响至深。为了维护国本,巫蛊案了结后,叶向高趁热打铁,向万历帝提出让福王尽快就藩。万历帝在叶向高的坚持下,被迫于是年下诏,宣布赐予福王良田400万亩,在良田准备就绪后福王才能就藩。不过,这又遭到叶向高的反对,他认为赐藩王400万亩田太多,有违先例,最后福王实际取得的封田是190万亩。[23]次年五月,福王离开京城前往河南洛阳。对这个继“争国本”之后围绕福王就藩朝中又争斗了13年的政争,到此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对此,叶向高说这是自己为首辅五六年来“报国第一事”。内廷宦官也为此事感佩叶向高,私下纷纷传颂:“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24]《明熹宗实录》记载,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校继位后,一次曾流着眼泪回忆说,父亲朱常洛一次带着他去觐见祖父朱翊钧,在宫门口等了整整一天,都没能见到祖父。原来祖父正陪着郑贵妃以及福王朱常洵在宫内玩耍,根本不理睬太子与皇长孙在宫外候着。这件事反映了万历帝对太子父子的冷漠。所以不排除朱翊钧易储之心的不死。从这件事中,也不难窥见叶向高维护太子、调停皇室矛盾的难度。
为了防止皇室内部因福王就藩再出新矛盾,叶向高可谓煞费苦心。明制,藩王就藩,需拜别皇太子,皇太子坐受藩王四拜,可以不说话。据查继佐的《罪惟录·叶向高传》说福王辞国前,叶向高特地密启太子朱常洛,对其作了交代。福王到了,朱常洛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辞,乃站立受二拜,并还礼,握手哭别,送到宫门。对太子的殷勤答谢,福王大喜。而万历帝与郑贵妃早已暗中派人观察太子的态度,在侦知这些情况后,也很高兴。至此,皇太子朱常洛总算度过了“争国本”以来此起彼伏的诸多危机。满朝文武也都松了一口气,无不认为幸有叶向高的转圜处置,避免了节外生枝。维护皇室内部的团结和睦,成功化解朝廷内争的政治危机,叶向高功不可没。对叶向高竭尽全力维护太子地位,朱常洛一刻也未忘,时常说到这里就流泪。他登基(是为明光宗)后一再说:“我有大恩人未报”,遂召叶向高还朝。可惜朱常洛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不过,他在帝位上虽仅一个月,却做了叶向高任独相时要做因受阻未能做成的事。《明史·光宗本纪》等记载:光宗即位后就补发了边境军队的欠饷;拨乱反正,让因进谏被罢官被关押的言官们复职;重振朝纲,提拔了一批正直官员,充实各地各级严重缺员的衙门,使得国家机器能够运作;召回各地的矿监税使,停止对工商业的滥征,也就遏住了群体性民变的势头;特别是他派往边关运送饷银的公差,加发沿途的开支费用,防止这些公差借皇命扰民。所以,当时京城百姓说他是“一月太平天子,万年有道圣人”。中国历史上360多个皇帝,还没有一个被老百姓喊作“有道圣人”的。皇帝施了仁政,老百姓总是会记住的,真正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宦官专权与辽东战事
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去世,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1621—1627在位,年号天启)。叶向高在天启朝任首辅四年。他在任期间面对的主要危机,一是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权乱政,二是辽东战事。叶向高二度入阁为首辅,根据形势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安辽民,省烦言,明职掌,恤民困,收人心;措施的重点放在“抑宦”上。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之烈,莫过于汉、唐、明三代。然而,明与前两朝有明显的区别:汉、唐宦官专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而明代再无此现象出现。明代宦官权势再大,也是依附在皇权上;一旦失去皇帝信任,立马完蛋。明代宦官专权途径主要是通过一项权力实现的,即“批红”。朱元璋废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到明成祖朱棣时创设内阁。内阁职掌中最关键的重要权力是“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大小臣僚的章疏经御览后发下文渊阁,由阁臣在朝臣章疏上拟定皇帝的批答意见,再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之上进呈皇帝。而阁臣的票拟最终要经皇帝以朱笔批出,这就是俗称的“批红”。阁臣根据“批红”来执行皇帝的决策。在天启年间,这“批红”权基本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操持。为此叶向高没有少上疏劝谏,试图说服明熹宗,遏止魏忠贤擅权,以期保障政治机构的良性运行。叶向高在明熹宗时,值得后人记住的有五件事,一是落实了为张居正平反;二是抚恤方孝孺的后代,赐予谥号,给予祭祀与安葬;三是大力任用东林党人,扶持了正气,刷新朝纲;四是动用内帑稳定军心;五是致仕前请求明熹宗废除“廷杖”。“廷杖”虽未废除,不过,此后“廷杖”却是极少发生了。天启年间,身为首辅的叶向高奏请起用了一批正直能干的官员,主要是东林党人。他多次上疏痛斥“阉党”,千方百计调护众臣,救援贤臣,甚至不惜与魏忠贤作正面斗争,因而结怨于“阉党”。阉党攻击其为“东林党魁”,伺机加害。由于熹宗的顽劣昏庸,叶向高上疏劝谏几无效果,他只得于执行上尽力补救。魏忠贤曾借故欲廷杖御史林汝翥,后者被迫逃往河北遵化。阉党造谣说林是叶向高的外甥,指使爪牙围攻叶府。叶向高此时已是无力回天,知事不可为,力求辞职。“乞归已二十余疏”获准。[25]而明熹宗遂成为有明一代依赖宦官乳母而又骄奢淫逸的昏君而无可救药,明王朝也就犹如一辆汽车高速行驶在下坡路上,点刹刹不住,强刹则翻车无疑,毫无悬念地走向了它的终点。
万历时期,后金迅速崛起,构成对明王朝的巨大威胁。辽东局面难以改观,可军费开支却日益剧增,朝廷不得不年年加派辽饷。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年,辽饷加派竟高达520多万两。这一现象到天启年间更加严重。然而仍是入不敷出,兵饷时常被拖欠,以至于常常发生兵变。如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陕西都司陈愚直以固原兵入援辽东,士兵走到临洮全军溃散。接着,宁夏援辽骑兵复溃散于三河。[26]同年十二月,浙江参将袁应兆领兵7000人援辽,溃逃2000余。到了天津,袁应兆招补新兵,许给每名士兵安家银5两,入伍后却不给。新兵索要反遭捆打,于是新兵尽数逃散。[27]由于叶向高重用正直的东林党人,在天启初期,局面一度出现起色,政治开始向清明方向发展,吏治得到整顿,尤其是在澄清铨政(官吏考核选拔)方面,颇有起色。在这批正直官员的支持下,叶向高为弥补太仓库的亏空,于泰昌、天启元年,曾拟动用内帑白银700万两予以充实。内帑是皇帝的专用库银,叶向高也敢动,由此可见他是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无私而无畏。为了解决士兵欠饷,加强辽东防务,叶向高分三次发内帑充兵饷犒赏士兵,共计用了内帑白银530万两。明熹宗曾悻悻地对工、户、兵三部的尚书说:“内帑所发已多。”[28]这一举措解决了欠饷,稳定了军心,也延缓了百姓税赋负担的加重,给病入膏肓的明王朝注入了一针缓释剂。
叶向高两度入阁,共计十一年四个月,其中有7年在万历朝是“独相”,一人独撑内阁。他在时局艰危之际,不以个人进退为念,不与闻六部事的逊居姿态,尽一己之能济时匡漏,努力消弭各类矛盾,使得皇权得以在平稳中实现了衔接,鞠躬尽瘁补救因“万历怠朝”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他为了达成他的报国心愿,利用皇帝的信任,不惜以辞职相“要挟”。能查到的,他向万历帝提出过62次辞呈,甚至以“罢工”逼皇帝就范。天启年间,他又向明熹宗提出过20余次的辞呈。不愿做宰相,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奇事。万历年间,他对神宗说:“臣屡求去,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29]可惜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叶向高面对这一时期的困境,确已无力回天。他在明熹宗天启年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在一群宵小阉党的围剿下,不得已“一走了之”。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二十二日,叶向高终于获准退休返乡。《楹联新话》卷九载有叶向高此时的自题联:“黄阁误承恩,叹此日经纶,辜负了金瓯玉铉;青山频入梦,留衰年精力,准备着竹杖芒鞋。”该联隐含了他去国的苦衷。葉向高的致仕,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正直官员群体在朝廷失去了一位十分重要的支持者。此后,魏忠贤与阉党终于控制了朝政,万历时期的困局已无解了。三年后的八月,明熹宗驾崩;又过了两个月,叶向高在家乡去世。崇祯皇帝追赠其“太师”,谥“文忠”。又过了不到十七年,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留下“景山的风景”独自凄凉。
对叶向高在国家困境中苦苦支撑,不断调和朝廷内斗政争,尤其在天启年间与阉党作坚决的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世皆予以褒奖,指出他是有明一代161位阁臣中才能比较突出的一位。[30]
注释:
[1]孟森:《明清史讲义》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6页。
[2][7]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绪论第4页。
[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
[4][6]参见张建民、周荣:《明代财政史》,《中国财政通史》(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1—392页,第208、220页。
[5][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6、687页。
[8][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九十一,转引自《明代财政史》(《中国财政通史》第六卷)第234页。
[9]参见《明代财政史》(《中国财政通史》第六卷)第237、238页;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增补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409页。
[10]参见《明神宗实录》,“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版;《明史·宦官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矿税之弊》,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12]参见《明史纪事本末·矿税之弊》。
[13][23]参见《罪惟录》之《列传》卷十三下。
[14]《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
[15]参见《明神宗实录》,《明史·神宗本纪》,《明史·孙丕扬列传》及《明清史讲义》上《万历之荒怠》第262页。
[16]《罪惟录》之《帝纪》卷十四,第316页。
[17]《罪惟录》之《帝纪》卷之十四第317页,《明史·孙丕扬列传》。
[18][22][25][29]《明史·叶向高列传》。
[19]参见(清)夏燮:《明通鉴》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995年第四次印刷。
[20]参见《明史·顾宪成列传》,《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
[21]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七《叶向高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
[24](明)谈迁:《国榷》第五册,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8年第二次印刷。
[26]参见《明熹宗实录》卷十,《明史·熹宗本纪》。
[2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十七,《明通鉴》卷七十七—七十九。
[28]《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30]参见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3页。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