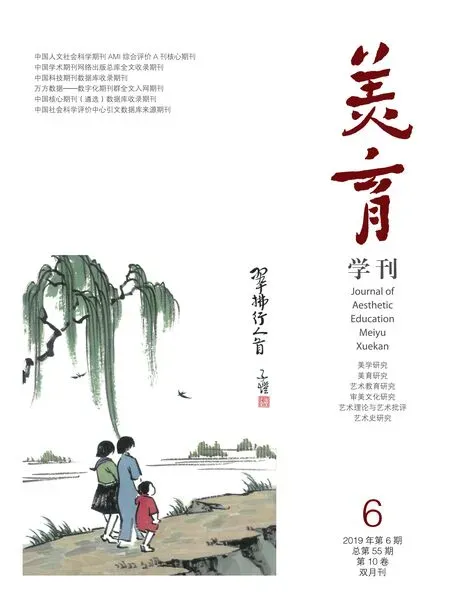汉魏时期表演艺术的发展及新型艺术形态的形成
——以“技艺”与“叙事”的相互关联为视角
王廷信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艺术门类是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出来的艺术形态。艺术门类的形成均有其特殊背景,是在特定时代精神需求、特定环境和条件的支持下产生的。艺术门类一旦形成稳定的机制,就会有大量的艺术家按照这个门类的基本规则从事创作。艺术门类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养分,丰富艺术语汇,形成了自身的特性。但在发展过程中,新的艺术门类也会在特殊背景下涌现。本文就表演艺术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变化探讨这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以汉王朝为代表的国家统一让艺术归于一统;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交流的频繁,外来艺术进入宫廷,为艺术带来新的机遇。具体到表演艺术,这个时期以歌舞、杂技、魔术、说唱、小说等五大艺术门类为代表的艺术形态遇到了相互借鉴、促进新型艺术形态涌现的机会。
一、奢靡之风为表演艺术提供了演员队伍
汉魏六朝时期的表演艺术一方面源自春秋战国就已兴起的传统歌舞,这种歌舞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与“礼”相对应的“乐”,二是源自民间的百戏。前者一直活跃于宫廷,多为仪式性的表演,在艺术史上被作为“正声”。后者则是对于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的民间各类表演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在艺术史上被作为“俗乐”,多是偏于娱乐性的技艺表演。杂技和魔术未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门类,多与其他“俗乐”放在一起表演。说唱则是较为纯粹的民间表演艺术,在汉代民间已经出现,与说唱有着共同特征的小说也在汉魏六朝时期日渐兴起。说唱与小说两大艺术门类的兴起,为汉魏六朝新的艺术形态的涌现提供了机遇。
战国时期,民间的表演艺术已趋繁盛。秦国宫廷中也聚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艺人。刘向《说苑》记载:“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说明秦朝宫廷的奢靡、宫廷演员数量的巨大以及表演艺术的兴盛。秦国宫廷所呈现的表演艺术既有偏于礼仪的“正声”,如钟磬演奏,又有偏于娱乐特征的“俗乐”,如倡优表演。
汉代宫廷亦然,司马相如《上林赋》云: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上林是汉武帝时建的宫苑,主要用于皇室游玩、打猎等娱乐,有专演歌舞的宣曲宫、专演百戏的平乐观。《上林赋》所云狩猎游戏休息期间观看的歌舞百戏一方面来自宫廷乐舞,另一方面来自各地的民间表演艺术,达到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观赏效果,让众多艺人云集一处,“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极尽奢靡。
《汉书·礼乐志》云,汉哀帝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当时宫中乐府“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但哀帝罢黜乐府中的部分人员和乐种后,并未影响到各地富豪大户。《汉书·礼乐志》云,“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仍然我行我素。富豪大户对于乐舞的沉迷为民间表演艺术的兴盛提供了空间。《史记·货殖列传》云:“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中山乃今河北、河南一带,因地薄人众,民不聊生,故多以倡优为业,经常远游千里,奔富厚之门。汉代乐府以及诸侯富厚之家,常蓄民间倡优。《汉书·礼乐志》所记载的“蔡讴员”“刘讴员”“邯郸鼓员”“淮南鼓员”“沛鼓员”“郑四会员”“楚四会员”“秦倡员”等均为来自各地的民间艺人。众多的艺人因宫廷延至豪富之家的奢靡之风而找到了生存之道,也带动了这个时期表演艺术的兴盛。
北魏时,有了专门的乐户制度。《魏书·刑罚志》云:“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北魏孝昌之后对触犯法律者的妻子和孩子罚入乐籍虽然不合理,但这种制度以强制手段稳定了表演艺术队伍,使表演艺术有了较为充足的演员来源。
我们从古籍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来说明汉魏六朝时期民间表演艺术的繁盛。宫廷的奢靡之风吸引了大量民间艺人从事表演艺术,正是在这种精神需求和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中,有别于单纯歌舞和杂耍的新的艺术形态——小型戏剧才可能出现。《东海黄公》是三辅一带民间表演艺术盛行的结果,《公莫舞》是民间乐舞艺术盛行的结果,《踏摇娘》也是北齐民间表演艺术盛行的结果。这些新型艺术形态的规模、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大大区别于纯粹的宫廷乐舞和已往的民间百戏。
二、外来艺术丰富了表演艺术的形态
汉魏六朝,由于历朝同周边各国的频繁交往,所以来自周边各国的艺术也随之进入宫廷,纳入汉魏六朝表演艺术的行列。
西域艺术对汉魏六朝时期表演艺术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汉武帝曾派遣使者出访安息,安息也派使者来朝。《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出使安息归来后,安息派遣使者“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安息使者进献给汉宫廷的黎轩国的“善眩人”就是会耍幻术的表演艺人。而位居西南边陲的掸国派遣的使者进献的歌舞与会玩魔术和杂技的“幻人”多达上千。这类进献使原本活跃于汉宫的“角抵奇戏”类型大大增加,更加兴盛。
《通典·乐六》记载:
后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而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以两大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
这是来自西域的百戏表演,主要是技巧性较强的歌舞和杂技。《通典·乐六》记载: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
这是来自西南诸国的百戏表演,主要是狮子舞为特征的歌颂太平盛世的大型乐舞。《通典·乐六》又载:
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真人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代,与西凉乐杂奏。
这是来自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的百戏表演,主要为马上鼓吹之乐。《通典·乐六》又载:
高昌乐者,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
这是来自高昌的乐舞表演。《魏书·志·乐五》记载: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
这是用来自平凉、西域等四夷的歌舞“增列于太乐”的做法,一方面是征服匈奴和平凉州后将其雅乐、伶人和器服作为战利品吸收进宫廷,另一方面吸收西域鼓舞进入宫廷。此外,宫廷还会因“典章有阙”而从民间搜访艺人进入宫廷。
这些进入宫廷的外来艺术不仅大大丰富了宫廷表演艺术的形态,也会与宫廷中原有的表演艺术相互借鉴,从而为新的艺术形态的出现提供机遇。《上云乐》之类的小型戏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神仙方术的盛行,助长了表演艺术的叙事机能。西域艺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神仙方术,其能输入中原,也同中原地区朝野上下信奉神仙方术的风气有关。
早在战国时期,神仙方术即初露端倪。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喜好神仙,追求长生不老,使方士之术大兴。汉代各种宗教和谶纬之说相继衍生,神仙方术再度盛行。《后汉书·方术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武帝之好,助长了方术之兴。方士为神异其道,多述异事,张皇鬼神,以骗取世人信任。方士们为了骗取信任,不仅利用文字记录,也通过表演来进行。这种情形也影响到了表演艺术。早在战国时期,由于神仙方术的盛行,就对表演艺术产生了影响。例如,刘向《列女传》就曾记载过齐宣王日夜置酒作乐、钟离春为他表演“遁术”之事。遁术乃隐身之术,葛洪《抱朴子·登步篇》引《遁甲中经》记载,入山“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时,刻鬼魅,施符书;以天禽日天禽时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盗贼,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避乱世,绝迹于名山,令无忧者……一名天心,可以隐沦,所谓白日陆沉,日月无光,人鬼不能见也。”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所谓“遁术”也不过是运用“刻鬼魅,施符书”的方术手段,使自己“出天藏,入地户”、令“白日陆沉,日月无光,人鬼不能见”的隐身避害之法。齐宣王置酒作乐、观赏遁术,是将方士的把戏作为娱乐性表演来欣赏的。但神仙方术毕竟是“假把戏”。方士们自吹自擂的本领也经常露出破绽。因此,许多方士不仅遭到皇家的杀头之运,而且也被民间百姓传为笑谈。《东海黄公》之类的小型戏剧就是民间艺人通过表演方士故事对神仙方术的讥刺。
由上可见,汉魏六朝时期,各宫廷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宫廷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艺人及其表演艺术的主动吸收,大大丰富了这个时期表演艺术的形态,从而为新的艺术形态的涌现提供了参照。
三、说唱、小说的出现为表演艺术提供了融合机会
歌舞百戏是对林林总总艺术表演的统称。在歌舞百戏当中,一般都是单纯的炫技表演,以声色技艺供人耳目之乐。较为综合的艺术的出现还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叙事风尚。汉魏六朝以说唱、小说为代表的具备叙事特征的表演艺术的出现,就是这个时段叙事风尚的体现。
说唱艺术在周代就已出现。刘向《列女传》卷一“母仪传”“周室三母”条云:“古者妇人妊子,寝不则,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叙述周室三母中的太任在妊娠期的生活。其中的“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便是目盲艺人用颂唱的形式为太任讲述一些有关妇德的故事。
时至汉魏,民间说唱艺术趋于发达。说唱艺术源自周代的“成相”,相是一种乐器,即所谓春牍。《旧唐书·音乐志》云:“春牍,虚中如筩,无底,举以顿地为舂柞,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成相是指击相而歌的故事演唱形式。《汉书·艺文志》曾有“《成相杂辞》十一卷,已佚”的记载。如今发现最早的有关成相的记载是《荀子·成相篇》。成相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已有不少专家做过考证,虽然详细表现形式尚未明确,但汉魏时期已有说唱艺术是无疑的。1957年在四川成都天回山墓发现的东汉时期的“说书俑”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该俑左腋下夹一鼓,右手扬一鼓槌,以击鼓而歌的滑稽形态让我们领略到东汉时期说唱艺人的表演状态。无独有偶,1982年,在四川成都新都三河镇马家山崖东汉墓出土的“说书俑”与天回山墓发现的“说书俑”动作相近、神态酷似。说明东汉时期,民间业已出现了以击鼓作为伴奏方式进行说唱的表演艺术。东汉时期,李尤《平乐观赋》就记载过“侏儒巨人,戏谑为偶”的表演,这种表演盖为一高一矮的演员,通过对话(偶语)形式所进行的滑稽调笑类的说唱艺术,类似今天的相声。
此时,还有把小说敷演为说唱故事的行为出现。《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曾叙及曹植在客人面前“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事迹。在此,曹植“诵俳优小说”的表演并非曹植自己所创,而是对民间艺术家说唱小说表演的模仿。这反映了当时民间艺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所从事的艺术是以说唱来表演小说故事。俳优把小说敷演为说唱故事是汉魏时期“故事”与“表演”结合的典型事例。这种事例在民间当不在少数,也说明这个时期“故事”与“表演”之间的相互需要。这种需要正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借鉴并相互结合催生新型艺术形态的契机。
《南史·陈始兴王叔陵传》记载:“始兴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叔陵少机辩,狥声名,强梁无所推屈。……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始兴王叔陵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亦是敷演民间故事以取乐的行为。这种情况说明,在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故事”的钟情,也为“表演”与“故事”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由上可见,说唱艺术的出现,使“故事”能以“声容”——即“表演”的形式流传,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新型艺术形态——戏曲艺术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汉魏六朝时期,小说艺术较为发达。《汉书·艺文志》记载: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汉书·艺文志》把说这些故事的人称为“小说家”: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可见在汉代,小说家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是以“街谈巷语”为题材叙述故事为人们提供娱乐。在《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这十五家中,《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等七家均依托古人;《周考》《青史子》二家记载古事;《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等四家为汉代人所著;《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百家》二家未著明何时人作,据鲁迅言,“依其次第,自亦汉人”[1]13。《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家小说,除少数篇目仅存外,多不存世,故无以考其真相。就仅存者而言,多为记述古人事迹,近于杂史,与今之小说概念不尽相同。今见汉人小说多为晋以后人所托。鲁迅云: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1]16
这种托古而言今的小说,多为文人“好逞狡狯”“夸示异书”的做法,也是方士们“自神其教”“托古籍以衒人”的做法,都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文人与方士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外,两汉时期,还出现了《燕丹子》《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飞燕外传》等小说。这些小说大多出自方士之手,所记事迹亦多关神仙。与这些艺术相适应,汉魏六朝也出现了表演神怪故事的、有别于纯粹歌舞、杂技、说唱和小说的新型艺术形态——小型戏剧。《上云乐》是表演西方得道成仙的长寿老胡为梁皇祝寿故事的,《东海黄公》是表演神仙方术失灵故事的,《总会仙倡》是表演各类仙怪瑞兽的。这些小型戏剧的内容都同神怪小说的盛行相关。
上述情况说明,汉魏六朝时期,以说唱、小说为代表的偏于叙事的艺术已广为流行。人们对于叙事的喜好,让原本兴盛的各类表演艺术超越了单纯的炫技,从而有了为“叙事”而表演的机会,为新型艺术形态——小型戏剧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创作基础。
四、“技艺”与“叙事”的关联及新型艺术门类的出现
汉魏时期流行的歌舞、杂技、魔术、说唱、小说五大艺术门类大致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依托简单的故事表现表演技艺的特征,偏重于单纯的视听娱乐;二是以演唱的形式叙说故事,偏重于叙事。视听娱乐重在表现歌舞或杂技的技艺,虽有一定的故事甚或是纯粹的技艺表演,但故事性不强,重在以表演技艺为人们提供较为纯粹的娱乐。以说唱、小说为代表的叙事艺术,已为表演注入了大量故事内容,无论是民间细事还是神怪传说,观众倾向于对这类故事内容的领会和思考。但这两类艺术经常在一个空间生存,各自的优长都有可能被对方吸收。新型艺术形态的出现恰恰就是两大类艺术在同一空间彼此借鉴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空间就是以乐府为代表的专门机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的乐府机构,旨在采集各诸侯国歌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便把乐舞艺术与民间百姓的生活俗事关联到一起,进而把“娱乐”与“叙事”关联到一起,从而使乐舞歌曲的题材扩大,也给乐舞本身增添了活力。汉魏六朝出现的歌舞戏,就应当是这种关联的结果。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把歌舞与叙事有机结合的诗歌,我们可称之为“叙事乐舞”。如《艳歌罗敷行》《艳歌何尝行》等,都是故事性很强的叙事乐舞。
在文学史或音乐史上,经常将这类叙事乐舞表述为“大曲”,而所谓的“大曲”就是有一定表现结构的叙事乐舞。
“大曲”的结构按“解”来分,“解”是大曲中的一章或一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一》云:“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一只大曲往往有多解。例如《陌上桑》有三解:第一解以铺叙方式表现罗敷之魅力;第二解以对话方式表现罗敷之坚贞;第三解以自述方式表现罗敷对使君之斥责。三解层层递进,罗敷的美丽坚贞形象亦逐“解”显现。
大曲最先表演的是“艳”。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一》云:“而大曲又有‘艳’……‘艳’在曲之前。”可见,大曲之“艳”,乃曲之“引子”。由此推知,乐府诗之“艳”亦当为诗之“引子”。张永鑫认为:
所谓“艳”,大多置于乐曲之前,起到概括和提示乐歌内容的作用,宛如乐曲的引子或序曲。同时,“艳”是一种音乐、舞蹈。作为音乐或曲调,它大多具有婉转激越、悠扬流丽的情调;作为舞蹈,它又大多具有艳丽华美、潇洒蕴藉的风韵,两者配合,既有舞姿和节奏,又有形象和伴声,把乐歌表现得完美而淋漓。[2]
可见“艳”是大曲的序曲,表演形式华美,旨在引导观众继续观赏;位于“艳”之后的是“歌”。“歌”是一支大曲的正曲,可分多“解”;位于“歌”之后的则是“趋”与“乱”。方以智《通雅》引王僧虔语云:“大曲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前,‘趋’与‘乱’在曲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趋”大多出现在乐章之末,是一种用以结尾的乐舞形式。《礼记·玉藻》云:“走而不趋。”《疏》云:“趋,今之捷步则趋,疾行也。”可见,“趋”是一种步伐节奏较快的乐舞形式。“乱”是大曲的结语,表达一种愿望或者感慨。一般以五言诗歌表达,有的以杂言形式表达,是故事情节的延续。
“大曲”这类大型叙事乐舞由最先表演的“艳”,中间表演的“歌”(分为多“解”)以及最后的“趋”和“乱”结构而成。这种使乐曲体制扩大,而且其不同的情感特征也为叙述多变的情绪和故事情节奠定了形式基础,也为以歌舞形式叙述故事的表演方式提供了借鉴。汉魏六朝以大曲为代表的叙事乐舞以不满足于一般体现“声容”特征的技艺性表演,而是将技艺性表演和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这个时段的许多叙事乐舞已近于戏剧表演。
除了叙事乐舞外,汉魏六朝也涌现出把技艺表演与叙事有机结合的小型戏剧。如乐府中的“杂舞”《公莫舞》,该舞曲是描述儿子出外谋生、与母亲分手的情景。杨公骥认为,《公莫舞》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3]。东晋太尉庾亮家伎所表演的《文康乐》也是一个小型歌舞剧,在隋之《九部乐》中被称为《礼毕》。《隋书·音乐志》云:“《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文康乐》因庾亮死后之谥号“文康”而得名,其家伎为表追思,佩戴面具,手持羽毛载歌载舞,象庾亮之容。《文康乐》歌辞已佚,故无以判断其具体内容,疑当表现庾亮生前事迹,为之歌功颂德。因《文康乐》以面具装扮庾亮之容,用以表演庾亮事迹,故可断定其为歌舞剧。梁武帝时期,清商曲辞中的《上云乐》可以看作是一个歌舞剧。清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明人胡震亨注周捨辞谓:“梁武帝制《上云乐》,设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发,导弄孔雀、凤凰、白鹿。慕梁朝,来游,伏拜,祝千岁寿,周捨为之辞。”任半塘根据周捨《上云乐》辞认为:
西方老胡,半人半仙,来游大梁,对天子上寿种种,原属虚构之故事,供剧本之应用而已。老胡、陛下、门徒、凤凰、狮子等,同须演员扮饰。彼“娥眉”“高鼻”“青眼”“白发”等,俱是化装;俳笑、饮酒、奏伎、胡舞、奉乐章、说内容等,俱是情节而已。周捨辞应如此看,李白辞正同。此伎远之颇似优孟衣冠之对真庄王演叔孙敖,而另扮戏中之庄王,共同完成情节。在此伎则对真“陛下”演老胡文康,而另有戏中之“陛下”,同演上寿。[4]
根据周捨《上云乐》,我们可以判断,西域人的《上云乐》应是一个类似拜寿的小剧目。大致表演西域仙人文康前来为皇上(不一定指梁武帝,剧中之皇上似仅用来喻指梁武帝)拜寿,剧中应有文康和皇上两个主要人物,文康为一仙人,“寿如南山,志若金刚”,率凤凰、狮子和侍从载歌载舞,为皇上歌功颂德,并以“奇乐章”祝皇上“寿千万岁”。由此看来,周捨是以西域人所表演的《上云乐》为题,描述的是西域人拜寿时的表演情形,而非梁武帝所制《上云乐》之本身。
除从乐府中的叙事乐舞发展而来的歌舞戏外,民间歌舞中也有歌舞戏涌现。《代面》和《踏摇娘》就是北齐时的民间歌舞戏。
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著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代面”亦称“大面”,《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引《乐府杂录》云:“《大面》处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北齐时的《代面》已能从战争中提取题材进行表演。演员“衣紫、腰金、执鞭”,“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这种表演有装扮,有动作,是演员装扮为兰陵王进行表演,故已具备小型戏剧规模。徐慕云曰:“其事虽简,而于戏剧之所需,已是‘规模略具,大体毕备’,谓非戏剧之源,固不可也。”[5]
崔令钦《教坊记》记载:
北齐时,民间艺人从生活中提取题材,编为小戏表演(“时人弄之”),《踏摇娘》便是典型例证。该戏已有“丈夫”和“妻子”两个主要人物,另有以和声呼应之“旁人”。“妻子”由男性演员扮演,且行且歌,“旁人”亦和声与其呼应。后“丈夫”入场,与“妻子”作殴斗之状,是一个表现民间夫妇争吵故事、具有喜剧风格的小型戏剧。
汉魏时期,除了歌舞戏外,还有许多偏于娱乐,但又包含一定故事情节的民间广场戏剧。广场戏剧仍然融合在角抵百戏当中,作为其中的一个节目出现。这类戏剧多表演仙怪故事,依托一定的故事呈现表演技艺。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海黄公》。《东海黄公》的出现与秦汉时期神仙方术的盛行有关。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过擅长幻术的鞠道龙向葛洪讲述黄公的故事:
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现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戏焉。
《东海黄公》是世俗戏剧在形态上定性、定型的标志之一。十分明显的是,这个戏是直接由民间方士的故事演化而成的。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则应是《东海黄公》的故事题材之源。《东海黄公》是角抵戏的节目之一,它体现了由神仙方术到世俗戏剧艺术的一条清晰线索。梁朝时,还有一个剧目——《蚩尤戏》。梁任昉《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有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角抵戏在秦朝即已盛行。《史记·李斯列传》云:“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观。”可见角抵戏非自汉代才有。梁时冀州一带的百姓所表演的《蚩尤戏》是角抵戏的一个节目,其戏剧表演的痕迹仅能从“头戴角”略见,蚩尤与黄帝战斗的故事不再明显,已经完全演化为一种游戏了。
这个时期的广场戏剧的代表还有《辽东妖妇》。《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废帝奏》记载过齐王曹芳耽于淫乐之事,说他:
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燕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
这则记载中,郭怀、袁信于广望观下扮演辽东妖妇进行娱乐,就是一场小型戏剧表演。王国维云:“则此时倡优以歌舞戏谑为事;其作辽东妖妇,或演故事,盖犹汉世角抵之余风也。”[6]
无论是歌舞戏,还是广场戏剧,叙事的痕迹都已十分明显。这与宫廷乐府这种专门机构的设置有关,正是这个专门机构让不同类型的艺术交会一处,出现了相互借鉴的机会,也正是这种相互借鉴的机会,催生了汉魏六朝时期以歌舞戏和广场戏剧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态。
汉魏六朝,有别于单纯表演艺术的小型戏剧艺术主要从歌舞、杂技、魔术、说唱、小说五大艺术门类的交融基础上产生的,其形态也分别体现在歌舞戏、广场戏剧两大方面。歌舞戏主要取材于民间琐事,是民间艺术家以生活琐事为题材创造出来的戏剧。从仅有的几个剧目来看,汉魏六朝的戏剧还是停留在技艺层面的小型戏剧,故事虽已渗入,但它们是依托简单的故事情节呈现技艺,而不重视故事情节本身的表现。但可喜的是这些剧目已经开始叙述故事了。
由于艺人地位的低下,汉魏六朝的戏剧还未能将触角伸向历史和更加深广的题材领域。由于民间艺人尚无更多机会接触到善于编写故事的文人,文人对民间艺人所表演的艺术也不屑染指。所以,尽管这个时期的叙事艺术已臻发达,但流行在文人圈内的叙事艺术尚未对戏剧艺术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又由于对外来语言、风俗、背景等情况的陌生,所以汉魏六朝对于外来艺术的吸收还是生吞活剥的,表演艺术主要取其形,而无法对其内在的故事进行详细的表演。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这个时期的戏剧在技艺层面的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