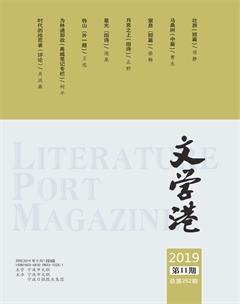窒息
徐畅
春萍刚到南桥做买卖时,人们只知道她是雪田来的乡下姑娘。也许,在他们看来,她是位干净的乡下姑娘,穿一身素,鞋面掸得雪白,袖肘没有丝毫褶子。站在石板街上,呆呆地望着棚顶的灰铁皮。她说话谨慎,对新环境保持着距离。除了这些小心翼翼之外,她还有着新婚期未脱的羞涩,是那种身心还像草木一样生长着,生活却将她推到人世跟前。
香料铺开张的时候,人们看到那个叫麦安的人,他骑一辆旧摩托,身上还套着板厂的蓝制服。他见人就散烟,搬着小茴香、肉桂、花椒的纸箱忙里忙外。到了傍晚,他赶去厂里值夜班,跟附近的商户打过招呼,拜托几句,递上烟。之后,踩着油门便走了。好似新婚的妻子就这样拜托给了南桥,拜托给了南桥各家商户。
很快也有了肚子。起初還不耽误进出货,到了秋冬,走路都要扶腰往后仰。铺子关了个把月,再开张时,春萍已经抱着小满在清账了。又过一个冬天,小满能在各家店里串门,吵嚷着要吃的。小满在菜场的日风和气味里养着,好似先天的营养环境,小婴儿跟头小兽一样,比同龄孩子更高更敦实。香料铺的门脸扩成两间时,小满已经在幼儿园读中班了。
现在的春萍,养成了慢悠悠的习惯,走起路来,丰腴的身体在宽松的套裙里撞来撞去。下午没有顾客时,她喜欢在躺椅上午睡。在香料房待久了,她能分辨出每种香气的来源。两点过了一刻钟,她揭开绣着早樱的毛毯,解下花围裙,换上外套。卷帘门拉下半脸。她走过两条街,来到一家旅馆。老板陷在躺椅里,午睡未醒。她爬上二楼,走向尽头的那间。房间阴湿,烟味未散,电视打开着。正当她为这小把戏感到厌烦时,有人从身后抱住她。她扭动着,身体自然地滑到了床边。他身上有股车里的汗腥,蓬乱的头发和穿旧的衬衫,到处沾着这股味儿。看来,他又拉了一天的客。这股味道将她带向那个遥远的夜晚。
她记得他开着车,驶出城区。在郊外的采石场里,他扑到她胸口。因为光线的缘故,她看不到他紧致的后背和结实的臀部。两人弄得满身大汗,她拉开窗户喘口气,半边天满是星星。她没有想到,他们会从一串电话号码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告诉他,他在各个县城跑客,有时住旅馆,有时找家浴室也能躺一晚。除了每月回趟家,他居无定所。正是这个居无定所,打消了她上车以来的种种犹豫。交往的这个男人不同以往。
到了这一次,他已经懂得张弛有度了。他搂住她的腰,手掌往腹部试探。她褪下胸罩,身体游进棉被里。底下暖烘烘的,她右手拿出被子,摸到大衣口袋。那里有两片肉桂。她注意力有些涣散。电视里在播一部纪录片。留意几个海胆的画面,她弄明白这是讲潜水。她神志恍惚起来,水面越来越遥远。他小声地喘息,将她从海水里打捞上来。他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了。她锁骨泛红,那一阵潮水涌上来时,她体内的神经猛烈地弹了一下,肉桂在手掌里,搓揉得汗湿。她忍不住喊出他的名字,“李瞳”“李瞳”。临了,她抱紧他,在他的后背上抓了一把。他身上也有香味了。提上内裤时,她这样想。
走在街上,阳光让她满足。她在货摊旁站了一会。她给小满买了一打棉袜,又给麦安挑一副挡风的绑腿。之后,她准备去锁上店铺。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简单收拾一下,走出门,美美地干上一个下午。
来南桥头两年,下午空闲的时光,她都昏昏睡了过去。要是睡乏了,她坐起来看言情小说,有的在手机上,有的是书店租来的。中学辍学的那一年,她就迷上了那些虚幻的故事。从老版的《玉梨魂》到琼瑶、席绢,再到如今网上离经叛道的浪漫小说。她沉浸在幻想里,她想象南方阴雨绵绵的黄梅天,想象深宅的姨太太或上海的小姐们慵懒地和着麻将牌。她知道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刻,雨中接吻、私奔后的新世界。每每那个时刻,她身体异样得热烈起来。除此以外,她时常感到厌倦,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时间一长,生意也懒得打理了。她趴在躺椅上,躺一会竟会流出泪来。为此,她花了一笔不少的钱,订了一份时装杂志。上面迷人的服装首饰,总能在一瞬间,让她出离眼前的世界。
往后,她接触了几个男人,他们要求的姿势都很相似。先前的一个,扑到她身上,爱咬她的脖子。在他的建材店里,掩上门,她躺在柜台面上,从墙上方镜里欣赏他肌肉绷紧的双腿。先前来她店里买调料,他总爱拖住塑料袋摸她的手背。她没有拒绝。两人的关系维持了一阵子。有天早上,有人来店里称了两斤花椒,装袋后,那妇人迟迟不肯付钱,只是接过扔到地上,撂下一句话:把你那货收好。
让她舒心的是一个瘦弱的男人。跟他做爱,就跟抱着一把骨头。但是他的温柔是来自骨子里的。他温火慢炖,从没有着急的神色。往往是她先没了耐心,骑到他腹部。他白白净净,脱光了也白生生的。高潮时,他一脸苦思的表情。这样看来,他倒不像个厨子,更像教书的老师。从他来店里采购到后来的见面,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他烧菜时,爱用大料,大料中最爱香叶。她喝过他烧的汤,喝完后身体一紧。不过在一次高潮中,她说她想离婚,要他娶她。他立刻软掉了。
拉上卷帘门,她想到下午时,李瞳在被窝里打开手机照明的怪癖。近来她发现他身上不少的小毛病。在人前人后,男人总是不一样。刚坐他车时,他大大咧咧,说话也客气。她只把他倒水、聊闲话的殷勤看成一种好心眼。在临县进完货,她看到他在近处揽客。她有些讨厌他的小心思,但是当车开到她跟前时,她还是迈上了台阶,并将大包货物放到邻座上。搭过几次车,她仍没有高看过这个人。他长得黑,还有点金鱼眼。赶上春节,她再去城里,她站在路口,没有等来那辆旧面包,倒是冲上一辆轿车。车盖有道隐隐的白光,并不显眼。李瞳摇下窗户,说面包卖了,换辆小车跑客。她拉开门时,后座已经塞了三位客人。她心慌地上了车,从后视镜里,她的眼睛不时碰到后面。他们目光怀疑,带着一丝畏惧。她系安全带的动作,古怪而笨拙。她偷偷抚摸座椅光滑的皮套,背脊上酥麻麻的。一股幽香飘来,她本能地找到了来源,那只湛蓝、漆了荷花边的玻璃瓶。这时,脚底下升起热烘烘的暖气。她开始坐立不安了,她感到身体的热度在上升。她隐藏好自己的心慌,说了几句闲话,幸好,他笑得还像过去那样,上槽牙支得老高。他随手灌进一张盘,梅艳芳深沉的歌声传出来。原来,他也是有一点品味的人。伴着哀怨的《女人花》,她一点点放低了自己。
回到雪田的家,小满哭着迎上来,我讨厌爸爸、我讨厌爸爸。她抱起小满,往里屋走。果然喝了酒。麦安坐在床边,身体轻微摇摆。平日放工后,他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打牌比喝酒好,牌打到深夜,她还落个清净。今天情况更差,沾了麻将也沾了酒。他骂上家藏了牌,眼睛在地板上摸索。一脸要吐的模样。春萍带上门,留他一个人待着。
她在耳房烧好饭,麦安走进来,端起红薯粥,就到嘴边。一顿热饭下去,他腮帮泛红,鼻头出了微汗。“还真以为我醉了?”他重重地搁下瓷碗,“诈胡!”小满搅动指头,不明白爸爸说什么。而一旁的春萍,笑得丢了筷子。她望着这个酒后虚弱不堪的男人,慢慢觉出他的好来。
回房时,床边一摊湿迹。就算偷偷清扫过,屋里仍留有来自腹腔的怪味。电视里在播枪战片,她蜷进被筒,酝酿着睡意。快要梦到一个人影时,麦安抱住她,褪下她的三角裤。
过去为了不露出马脚,她保持做爱固定的频率,说话的范围都在家庭和生意上,麦安还没敏感到能在微妙的气氛里,捕捉可疑的痕迹。她自以为瞒住了这个男人。早先相亲时,面对说话紧张的麦安,她就有所预料。婚后,麦安自然事事顺着她,去县里开铺子也是她的主意。她知道麦安只想待在镇上,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就像算盘上的木珠,你不去碰它,它就待在原地。
现在这颗珠子起了腻,她勉强抱起膝盖。麦安从后面进入了。她品尝着辣心的涩感,头在枕头上摩挲。她抓起遥控器,缓慢换着频道。她想在旅馆里,看到潜水的画面。那是电影的片段,还是广告的一部分?麦安一个劲儿地往上顶,她知道时间差不多了。电视停在一档购物节目上。屏幕上正展出一套精致的餐具。她心算着费用,等待体内那根神经弹起。但是没到那个点,麦安便拿了出来。她用脚丫钳他腰上的肉,麦安摇着头,呼呼要睡去。
这一夜,她睡得不安稳。醒来后,浑身疲惫。她看了眼手机,快十点了。床头的钱包打开着。看来,没做早饭,小满拿了早饭钱。到南桥时,家家都出了摊。她躺在躺椅上,挨到中午。她寻思去小满的幼儿园看看,但在躺椅里睡了一会,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到两点,她有些烦闷。她走到往常的那家旅馆。
打开房间,里面重新收拾过,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她打开电视,等李瞳来敲门。
这一回,她找到了那个频道。安静的海底,隐约看到浮游生物。有两个人在游动。他们穿着黑色皮衣,提着巨大的手电,靠手势引导上下。在床上躺了一会,她想象自己沉到水下,绷紧一层青蛙皮。她伸出手去,抓不到也摸不到。她睡到渾身冰冷。她想到那片嘴唇在手机照明里亲吻她,给她温暖。醒来后,她心不在焉地坐起来,发现底下潮了。
她在浴缸里放满了水,将身体盛进去。她捏住鼻子,用力往脑门充气。练习了几次,她听到耳膜“噗”地鼓起了。脑袋嗡嗡响。节目里是这样要求练习耳压的。耳膜鼓起后,听力封闭了。她憋了口气滑到水里,任浮力将她托在当中。她期待的并未来临,周围的一切太拥挤、太温暖了。
她带起一身的水,离开了浴室。那档节目过去了,屏幕上一群斑马在奔跑。快四点了,李瞳还没有来。走回南桥时,她才拨了电话。无人接听,不出所料。坐在铺子里,她清点了账目,点数纸币时,她顺带数了钱包。添上旅馆的钱,总数跟昨天的一样。小满为什么没拿早饭钱?拉上卷帘门时,春萍自语。
晚上,她炒了盘蚕豆,肉丝烩了青椒。小满趴在凳子旁啃笔头。春萍问她,早上吃的什么?小满说吃的茶叶蛋。喝的呢?喝了热牛奶。多少钱?春萍放下盛菜的勺,小满说五块。春萍刚要问,小满又说,爸爸给的钱。盖上锅盖,小满合上课本,说我讨厌爸爸。春萍疑惑起来。小满噘着嘴说,放学后,爸爸没来接我。我一个人走回来的。爸爸呢?春萍问。小满不说话,抱来凳子要吃饭。
坐下不久,屋里响起马达声,麦安熄掉火走进屋。他自顾拿了碗,在春萍肩头上摁了一下。指头上有股很重的烟味,现在他抽烟了,还抽了不少。原本春萍就有气,现在更想说他几句。麦安夹起米饭,在口腔里漫不经心嚼着。他望着瓷盘里的蔬菜,丝毫没有动它们的意思。偶尔抬起头时,眼白却是红的。
吃完饭,他把碗捧在手里转。又输钱了?春萍剜了他一眼,要去洗碗,却听身后小声说,昨晚,我起夜回来,帮你看了一条短信。春萍“嗯”了一声,往锅里添洗洁精。我就想问问,这个阿童木是谁?麦安说,用指头抹着碗边。春萍身体冷了,好似静电在身上走了一遭。她笑起来,用抹布揩手,说一个常来买茴香的小叔。哦,那你给这个小叔打过不少电话吧?麦安从怀里掏出一卷纸,纸上搁着一张身份证。麦安看她一眼,背手出去了。
有那么几分钟,她不知要做什么,太多的事向她涌来,手里的碗筷滑到锅底。她擦干手,划开手机,这一天她都没想起要看看短信。短信只是平常的一条:明天有事,就不见了。她怀疑麦安翻了之前的几条。她收起自己的身份证,摊开那一卷纸。那是她半年来的通话记录。她能想象麦安急匆匆地跑去营业厅的模样。他焦急地等待着,甚至期盼没有任何值得一说的记录。看到那一串相同的号码,他当时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要杀死一个人?她早该查看一遍床头的钱包。
她收拾了桌子,带小满去洗漱。看着小满入睡后,她突然紧紧抱住女儿,亲了她一下。回到房里,麦安躺下了,电视关着,床头柜上搁着皮带。春萍小心解开扣子,不敢脱衣服。她上床后,麦安动了一下。他要打她?或是扒光衣服用皮带抽?面对这样的事,她也难以料定。就算他扇了自己耳光,她也只能承受着。这是风雨前的宁静,但是风雨迟迟不来。
躺下后,她听到麦安凝重的呼吸。过了一会,那呼吸又轻了。“你是让人下了迷药了。”麦安清了嗓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她在心里说。麦安不说话了,呼吸又凝重了。她想了会心思,睡意袭上来,下午时,她就有点感冒。她想着闭会眼再琢磨心思,可一松懈下来,她就睡着了。迷糊中,她听到有人在屋里走动。她睁开眼,抽屉、衣柜都敞开了。麦安在翻东西。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焦急地折回床边。
他抓住她的肩膀,摁进枕头里。他住在哪里?操了你的那个人,住哪里?麦安抽过皮带,拴住她的脖子。这时,她才清醒过来。她挣脱着,连连咳嗽。麦安压上来,将铁扣往里紧了一格。麦安又问了一遍,索性勒住皮带一头。春萍面色惨白,眼泪都快沁出来。她用力喘气,用鼻子用嘴,但是空气沉不下去。她踢着腿,脸部发胀,眼前眩晕,黑暗中有小亮点在闪动。她呼吸越来越浅,快要窒息的那一刻,她脱口说出那片街名。具体哪里?麦安仍没有放过她。他从她喉咙里掏出最后几个字才罢休。他扔下皮带跑出了门。春萍慌张地解开皮带,往肺里大口大口地填空气。刚才的惊吓让她喃喃自语:最西边,最西边那家。
镇定下来后,她想到那件紧急的事。她夺门追出去,但是摩托已经发动了,喷口黑烟,冲了出去。她跑到屋后,站了一会,那道微弱的光亮驶上大路,踽踽远去了。她走回里屋,脚边碰到一个人。她缩回脚,眯起眼睛才看到小满蹲在门边,她睡着了。原来她一直守在这里。她抱起女儿,躺倒在床。小满在她怀里翻了个身,她抱紧小满的头,心思开始混乱了。
她在恶梦里多次醒转,她梦见很多人在追她,她爬上通信大楼的楼顶,楼底下人人都在高喊,有人涌上了楼梯,手持刀叉,看来他们是要杀她。她不知道是自己疯了,还是世界上的人疯了。似乎只有抓住她,他们才能平息下来。这样一想,她心底柔软了,觉得自己真渺小。她愿意牺牲自己,让人类变得善良。但在她等待就义的时刻,走上来的却是李瞳,李瞳浑身鲜血,滑在她脚下。麦安跟在身后,抱着钢刀两眼通红,他又在追问,是不是还有别人?是不是?现在她猛然明白,疯狂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她知道她能做的不是去拯救,而是尽快醒来。
她早早送小满上学。坐在店铺里,她把花椒当小茴香卖掉了,称重量时也时常看错数点。经顾客提醒,她才发现找错了零钱。上午稍好一些,毕竟还有顾客来打岔。到了下午,她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的焦虑中。她把那本《烟雨濛濛》翻了好几个章节,最后发现仍然停在同一页上。那一页,日本人来到了上海。她扫了两行,仍没能缓和一点心绪。
昨晚她随口说出一家供应商的地址。她丢下书,望着手机上那个座机号码。看了十多遍,她终于有勇气摁下绿键。接通了,不像一个好兆头。她询问了,搓手等着。那头说没见人来家里。她点点头,她忘记那边是看不到她。过了片刻,那边又问,是上门收麻椒的?春萍支吾过去,挂了电话。
她在店里转了一圈,又给李瞳打电话,仍然没有人接。一个念头抓住了她,麦安找到了他?李瞳死了?她坐在店门口,痴痴地望着落在棚顶的鸽子。这时,有家干货店传来邓丽君的歌声,她的心思跟着《甜蜜蜜》在空中漂浮。不知停了多久,新闻联播的前奏打断了缥缈的歌声,她拍了一下大腿,跟自己说,呀,小满早放学了。
等她赶到幼儿园,学生都走光了。小满在教室里睡著了。她背着小满往家里走。
走到家时,天还没有黑下来。有辆警车停在门口。后车门敞开着,民警正横躺着。她走近时,民警坐起来,哗啦一声侧下车。这是刘麦安的家吧?她点头。你是刘麦安的家属?她点点头。那上车吧。民警咬着指甲,另一手拉开门。他早等得不耐烦了。
她抱着小满坐进副驾。车拐上马路,她小声问,要去哪里?民警打量着她,又打量着她的孩子。没多远的。他说。她不敢再多问了,她只愿把心思集中在眼下。那件可怕的事情尚且遥远,但事与愿违,车速开过了六十迈,一路上路口都是绿灯。
有电话打进来了,她将小满挪到另一只手臂里。接了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出车去外地,去了好几天。她这才听出是李瞳。
你说话啊,这会儿忙着呢?李瞳问。
没有,她说,没在忙。
昨天,有个疯子给我打电话,开始是骂人,骂得七荤八素,后来就疯言疯语。不会有什么事吧?李瞳说。说到那个疯子,春萍突然想哭出来。
哦,没事的,大概是哪个卖房子的吧。春萍说。
现在这个社会都乱了。李瞳说,我明天就回去了。电话那头等了等。
回来再说吧。春萍说。她看了眼民警,他扶着方向盘,一面咬着肉刺。手指上的指甲秃尽了。她挂了电话,手在口袋里搓揉,那一把小茴香快脱了皮,沾满了护手霜。
他们在石墩桥旁停了车,河岸边有人在走动。民警领着她,往下游高草深处走。劈开一处小道,能看到其他几位民警。在人与人的缝隙间,她看到麦安裹着昨天晚上的夹克衫,躺在地上,很不起眼。他浑身湿透,一条腿丢掉了,关节处溃烂,露出了骨白。走近一点,他的整个身体浮肿,脸上只剩左边的皮肤,右眼睛没有了,只剩一个黑乎乎的框。
他们在芦苇荡找到时,他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天黑,往南时撞到了石墩,冲下了桥。摩托也没法捞了。春萍打断民警的解说,往南?为什么是往南。民警指着石桥,桥上有轮子印,往南印子深。她想到那家供应商,他是中途回来的。他改变了主意,春萍说,他改变了主意。她捧住脸,奇怪的是,她闻不到任何小茴香的气味。
她小腿软了,跌坐在水滩上。小满醒了过来,她打量着四周,揉着眼睛问,妈妈,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是谁啊?
春萍体温下降,手脚冰冷。幽闭感四面袭来,周遭逼仄,透不进一点光。那一处深渊,到达了地球的最深处。那一刻,她仿佛沉到了海底。她感到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