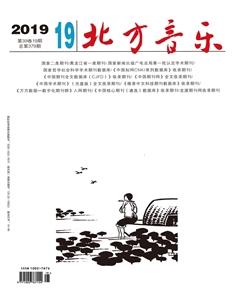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的结构力分析
【摘要】本文从调性结构、主题及核心音调等方面分析了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以期发现作曲家创作中的结构思维,以便更好地理解音乐。
【关键词】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结构力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识码】A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他创作的交响曲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尤以《第六交响曲(悲怆)》独具艺术魅力。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经典之作,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创作技法上及思想表达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该作品是柴可夫斯基对其人生以及音乐生涯的高度概括和总结。面对这样一部意义厚重的作品,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把握它?或者说,作曲家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呈现的呢?这需要从创作的角度解剖和分析音乐作品。
一、调性结构
调性或调式(现代音乐除外)对一部音乐作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调式调性是松紧与张弛之间不可或缺的结构力之一。调式调性的转换使作品暂时失衡,导致张力变化,对作品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音乐作品亦是如此,也需要戏剧性冲突。在西方古典到浪漫时期,几乎所有的音乐作品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调性思维。甚至可以说,将“调性结构音乐”作为金科玉律。通观《第六“悲怆”交响曲》,在不同的乐章设定主调的同时,调性复杂多变。
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陈述出现两次调性变化。首次,主题旋律从b小调到d小调然后转向f小调,均按照三度关系进行。三六度关系是浪漫主义时期特征,与古典奏鸣曲中四五度的功能性调性转换相异。随后回到主调b小调,调性体现出拱形结构。作曲家对调性设计并非刻意,是内心情感的音响外化。主部主题材料的调性并未就此停止,随后在#f、a小调陈述,并暂时回到b小调。副部调性从b小调转向关系大调(D大调)。调性呈三部性——D-A-D。展开部调性与古典奏鸣曲展开部相似,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调性为F、G大调和b小调;第二阶段调性为bE、bB大调,二者为五度关系。第三阶段是展开部的高潮部分,调性游移频繁,最终以b小调为再现部作准备。但再现部中副部调性并未用b小调而采用同主音B大调作为结束,可以看出,作曲家已经不再满足该体裁的传统调性规则,采用B大调就是对传统的突破,两调属同一调域,但调性色彩有差异。
第二乐章为复三部曲式,D大调。由呈示部、三声中部、再现部构成。呈示部中段建立在主调的属大调(A大调),三声中部建立在主调的关系小调(b小调),再现部静止性再现。第三乐章为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G大调。以主部和副部两个主要主题展开陈述,主部为三部曲式,首段以G大调陈述,中段转到D大调(属大调)。副部为三部性结构,以E大调呈现(作为主调G大调的下属关系调),属远关系转调。再现部分调性回到G大调,体现出“奏鸣原则”。第四乐章同为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调性为b小调。该乐章调性安排传统奏鸣曲式相似,从呈示部到再现部的调性依次为b小调—D大调—b小调。
统观整部作品的调性布局,调性构思巧妙,并不限于理性的推演。窃以为,调性布局更多源于作曲家感性的“意识流”。其中,第一、第三乐章的调性与古典奏鸣曲式不同,再现部的副部调性并未回归。调性的三度关系运用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特征,恩特斯·库尔特曾认为“浪漫主义是三度的年代。”[1]与古典奏鸣曲式中的调性安排逻辑即大调中主属关系(四五度关系)转调构思是有区别的。
二、主题及核心音调材料
调性在作品陈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作品的发展与情绪的变化也离不开主题材料,主题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作品的种子即基础性材料。
第一乐章的引子并沒有在主调b小调上陈述,而是在主调的下属小调(e小调)陈述。引子中低声部(低音提琴)半音下行,最终停留在b小调的主音上,与大管声部的环绕上行形成反向,两个声部的进行可作为全曲的核心音调始终贯穿。用e小调的属和弦作为半终止,是为主调b小调的出现作的一次准备。第二句以b小调的属和弦作为终止,第三句再次对主调b小调的属和弦作了巩固。从作品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题可以看出,材料就是源于引子中大管演奏的段落。第一乐章第一主题是在这个基础上变化发展,其中运用重复、变化重复等手法。
第二乐章主题明朗、轻快,属圆舞曲风格。五拍子的旋律流畅潇洒。分析该主题,材料也可在引子中发现。前两句是三度模仿,后两句是二度模仿。第三乐章是诙谐的进行曲,呈示部主题采用12/8拍,动力性较强。副部主题采用E大调的正音级作为材料,性格强劲有力,有一种英雄式的斗争精神。第四乐章作曲家悲观绝望的内心体现的痛快淋漓。整个乐章都是叹息般的基调。呈示部主题由弦乐队奏出,小调的暗淡色彩与叹息音调的结合始终表现出作曲家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尽管在副部调性变为D大调,但下行旋律线条的凄楚仍然难以掩饰,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性。
通过对不同乐章主题材料的分析发现,作曲家对作品的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和运用。通过不同的织体对主题材料展开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一是全曲引子中大管奏出的材料,二是低音提琴奏出的半音下行,这两种材料在各个乐章均有体现。
三、结构力与生命现象的关系
交响曲从形成到后续发展,都承载着作曲家的心血与智力。从历史看,交响曲自形成以来,表现手法、感染力以及艺术魅力都得到了拓展和提升。《第六交响曲》也不例外,作品在汲取传统作曲技术的同时,融入了作曲家的思考,将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无论是调性还是核心音调,都有助于展现作品的思想,这与作曲家的创作初衷相统一。柴可夫斯基认为,“第一乐章——激情、信心、渴望工作。应该短促末乐章‘死亡——毁灭的结局。第二乐章——爱情;第三乐章——失望;第四乐章——以静谧气氛告终(也是短促的)。”[2]上述思想决定了作曲家对音乐语言、织体与结构的构思和处理。
任何音乐作品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作品的背后承载着作曲家的感悟,这种感悟外化为具体音乐作品时,就具有了某种类型的生命现象。生命现象仅仅是作曲家本人的吗?还是某个特定的类现象?这属于音乐审美心理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代表了一部分类主体的情感,这也正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内心的融合所引起的,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诘问,对压抑情绪的宣泄和对现实的美好向往,是作曲家以音乐的方式对现实的思考。从四个乐章的音响变换来感悟作曲家的生命历程也自然成为每一个爱乐人读乐之旅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留给听者无限思考。
四、结语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曲》在俄罗斯上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性质。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调性结构和主题材料的运用都存在着偏离和回归的交替,偏离和回归既指向音乐传统,也指向音乐作品本身,这正是音乐现象的本质存在。既然有传统就有千篇一律的规则,既然有偏离就有千姿百态的创新,应该正视这一现象,既要重视千篇一律的作品,更要注重中作品中的“千姿百态”,这是音乐作品得以传颂的本质原因。
参考文献
[1][德]克列门斯·库恩,钱泥,译.音乐分析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逸文.柴可夫斯基论音乐创作[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宋曼曼(1983—),山东枣庄人,文学硕士,枣庄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