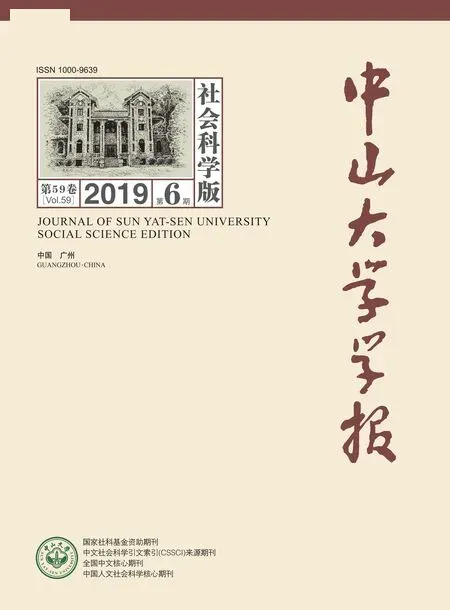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顺 真
一、比量为随现量之随量

梵文anumāna的藏译相当精准,译为rjessudpagpa’itshadma,其中rjessudpag义为随、跟随,tshadma即大家所熟知的汉字转音“择码”(2)关于anumāna的藏汉对勘,详见剧宗林:《〈因明入正理论〉藏译本略讲》,《因明论丛》,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由于受到玄奘大师关于hetuvidyā即因明译名的影响,即使近代以来将藏文量论著作汉译时,亦多将rjessudpagpa’itshadma译为比量,不仅译名并非绝对确切,而且由于这一译名的影响,也使研究者忽略了藏传量论与汉传因明(正理)的真正区别,即有将印藏量论汉传因明化的学术趋向,这实是关乎到佛教量论因明研究的一大误区。就中,体会颇深的乃是因明前辈剧宗林先生。剧先生在藏区工作学习近二十年,并随多位藏学大师学习藏语文,尤其是藏传量论,所作《藏传佛教因明史略》乃量论、因明学界的必读书,其早年的藏译汉著作以及研究亦随顺古译而将rjessudpagpa’itshadma译为比量,但后来有所订正,如在《因明论丛》的相关译述与论文中特别强调:
汉文“比量”,藏译“随量”,一字之差,意义侧重有所区别。“随量”义侧重“随现量智而生之量智”,“比量”则侧重“由类比而生之量智”。(3)剧宗林:《因明论丛》,第121,291页。
并明确地将早年所译《正理滴论》“比量”一词直接改为“随量”,如“余者是‘共相’,它是‘随量’之境”(4)剧宗林:《〈释量论·成量品·首颂·广注〉翻译、疏解与评说》,《因明论丛》,第291页。。又在随下的文辞中将传统所说“为自比量品”改为“为自随量品”,将“为他比量品”改为“为他随量品”(5)剧宗林:《因明论丛》,第121,291页。。剧先生对anumāna亦即对rjessudpagpa’itshadma这一量论核心概念之一的汉译以及深度解读,理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比量从语源上来说是紧随现量的随量,亦即比量(bì liànɡ),而且即使是在陈那思想的正理期阶段,其对此亦有明确的阐释。一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陈那在《正理门论》中将如理作意的正理体系划分为悟他与自悟二门,就中能立、似能立与能破、似能破为悟他门,而真现量、似现量与真比量、似比量为自悟门。这一思想被其弟子商羯罗主所继承,故《因明入正理论》开篇即曰:“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9)商羯罗主菩萨造,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入正理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1页。这就是著名的“八门二益”的结构性体系。就中又必然涉及两大问题:第一是悟他与自悟的关系。《门论》开篇即曰:
“宗等多言说能立”者,由宗、因、喻多言辩说他未了义,故此多言,于《论式》等,说名“能立”。(10)大域龙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3,3,3,3页。
不言而喻,作为悟他门的核心就是宗、因、喻三支论式,这一论式称为“能立”。但从量亦即从认识发生的向度来看,三支论式即是比量智中的自义比量,而对此自义比量的发生条件,陈那又将其具体分为两种:
此有二种:谓于所比,审观察智,从现量生,或比量生;及忆此因,与所立宗,不相离念。由是成前,举所说力,念因同品,定有等故,是近及远,比度因故,俱名比量。此依作具,作者而说。(11)大域龙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3,3,3,3页。
郑伟宏先生释其义曰:“比量智的产生分两种情况:显示宗法智的因或者从感觉量生,或者从推论所生,它们都是远因;记忆起因法与宗上之法间不相离关系(同品定有、异品遍无)的念则是近因。此念能增强远因所生之智的力度,因为此念所回忆的是显示因后二相的同、异喻。这近因和远因都是通过比较而成为因的,(因从果名)都可称为比量。远因与近因的不同是依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与对象之间的亲疏关系来分别的。”(12)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3页。又见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0页。就中,能够生起比量智的“远因”分别是现量与比量,具体而言即是“了火从烟,现量因起;了无常等,从所作等,比量因生”(13)大慈恩寺沙门基撰:《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册,第140页。。日僧善珠释曰:“了火宗智,现量因生,以现见烟,比知火故;了无常智,比量因生,由比所作,了无常故。二智既别,故此双陈。”(14)[日]善珠:《因明论疏明灯抄卷第六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8册,第423页。两类“远因”主要是确立因与“所比”的关系,即是确立因三相中遍是宗法性的因,而所言“近因”乃是“念”,主要是确立能立因与“所立宗”即主要是与作为“所立法”之后陈间的不相离关系。因此,自悟比量智虽以证因为主,但能够保证此证因真实生起尚待于由现量、比量所成的“远因”以及由“念”所形成的“近因”,“远因”与“近因”是自悟比量智作为“能立”的“能立因”,接着这一阐释,陈那对自悟比量与悟他比量的关系作了如下回答:“如是应知,悟他比量,亦不离此,得成‘能立’。”(15)大域龙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3,3,3,3页。郑伟宏释曰:“如上所述应知旨在悟他的比量也不能离开这远因和近因显示的因三相而成为真能立。”(16)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第236页。就中可知,虽然陈那并未明言,但已经可以看出悟他比量以自悟比量为前提的想法。当然,在此正理期阶段,由于学理背景的限制,陈那尚未真正区分开自悟比量与悟他比量的不同,这要在其基于量论而阐释两种比量时,亦即只有到了创作《集量论》的时代,才最终完成了比量的划分。不过,在《正理门论》讨论比量智形成的原因包括两类三种,即作为“远因”的现量因、比量因,与作为“近因”的念因。这似乎已然给法称从形成合乎因三相的动机过渡到结果提供了某种暗示和启迪,那就是法称最终提出了合乎因三相的三种正因:自性因、果性因与不可得因。自性因与果性因实由“远因”而成,而不可得因则源于人类“随量”认知更为复杂的精微层面,即发生认识论得以生发的深层动机,亦即能知心最初发动起来的“念”。
第二是比量与现量的关系。就此,陈那在《正理门论》中明确指出:“现量除分别,余所说因生。”(17)大域龙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3,3,3,3页。其长行释曰:“已说现量,当说比量。‘余所说因生’者,谓智是前智余,从如所说,能立因生,是缘彼义。”(18)大域龙菩萨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第1,3,3,3,3页。所谓“前智余”是指“现量智之余……换言之,现量乃比量的基础,以往的感觉经验一进入比量,即离开了现量无分别的境界,不再是现量了,这现量智之余,就是比量智”(19)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9页。。这一界定直接在《集量论》中再次得以呈现:“‘自相非所显,所取异是余’:问:何故比量分二,非现量耶?曰:此亦由所取境各异故。现量之境是自相,‘自相非所显’。故不可分为二也。若现量之境义,能施设名言,即由彼声,应成比量。故现量之自相境,不可以名言也。或曰:于现量之境义,亦见有比量转。如由色比所触也。曰:虽有见此,然比量趣彼义,非如现量。‘是余’。是由先见为因,乃比度所触。谓于彼色,舍离现量行相,由色之总比度触之总。其现触之差别,非可显示故。是故二量之所行境,非是一也。”(20)陈那造,法尊法师译编:《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30页。不言而喻,比量乃现量之余。原因在于,现、比二量的“所行境”亦即所量相分是二非一,而且比量作为能量,其所量相分的共相有其根源,这一根源即是作为现量能量之所量相分的自相。因此,比量必然是随现量的“随量”亦即比量(bì liànɡ),这一点在考察佛教量论因明的整体结构时尤为重要,亦即比量不能够绝对独立于现量而存在,而且即在比量本身,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亦终究是与现量密切相关的。这在法称关于不可得因、apoha即遣他、成量等量论专题的阐释中尤为明显。
二、比量为假而现量为真
通观陈那、法称的量论学说体系可以认为:一方面从比量的来源来看,其以现量为因,作为随量,其并非量的第一根源;另一方面,若从“唯有自相与共相之二相的原因在于,所量境有能作义与不能作义、不随余法转与随余法转、自体所成就与能诠声所成就,以及非由名言成就识心之缘与由名言成就识心之缘的四种不同是确然的,亦即从所量境与能量心来看,其体性只有两类的不同而绝无三类以上的不同,因此存在对境唯有依据前述之前者所成的自相以及依据前述之后者所成的共相,因此能量识心亦唯有建立在自相与共相二者基础上的现量与比量”(21)顺真:《印度陈那、法称“二量说”的逻辑确立》,《逻辑学研究》第11卷,2018年第3期。这一高度概括来看,就中已经表明法称关于构成二量说之现量与随量在量果层面的不同价值,亦即唯现量为真而比量为假。既然如是,严格说来量即现量,且除现量外不应再立比量,若如是就与顺世论外道的一量说相同了。对此法称在《释量论·现量品》中曰:“无非所量故,言一。吾亦许。”(22)法称造,僧成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北京:中国佛协,1982年,第183—184,183—184,184,182,182页。僧成大师《略解》曰:“顺世派言:共相非所量,是无事故。以是所量决定唯一自相,故能量亦决定唯一现量……顺世派对佛弟子不须成立能作义所量唯一自相。吾亦如是许故。”(23)法称造,僧成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北京:中国佛协,1982年,第183—184,183—184,184,182,182页。亦即法称与顺世论的立论并不相同。顺世论主张一量说,因其以为存在只有能作义的自相,既然能作义唯有一相,则所量亦必然唯有一相;既然所量唯一,则能量必然非二,故顺世论立一量说。法称则认为,从能作义的角度来看,我派亦许自相为唯一能作义者,虽然如是,但不因此就必然确立量唯有一量,原因在于,在能作义之外尚有不能作义者,此不能作义者即为共相,而依共相即可立随量,因此法称坚决主张“须许比量”(24)法称造,僧成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北京:中国佛协,1982年,第183—184,183—184,184,182,182页。。但在“须许比量”的基本前提下,法称认为:
自相一所量,观有无求义,由彼成办故。彼由自他性。
之所通达故,许所量为二。非如所著故,许第二为误。(25)法称造,僧成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北京:中国佛协,1982年,第183—184,183—184,184,182,182页。
僧成大师《略解》曰:“能作义之所量决定唯一自相,以诸观察有无取舍之果者,其所求义唯由自相所成办故。问:若尔,论师如何说自共二种所量耶?曰:论师许所量为自共二种者,谓自相法现量以自体性为所现境,比量以余共相体为所现境而通达故。问:若于唯一自相,有二种通达之理,何者错误?曰:许第二通达之理,如通达声无常之比量为错误者,以自所现声无常非是如实,而著为声无常故。”(26)法称造,僧成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北京:中国佛协,1982年,第183—184,183—184,184,182,182页。意为从所量来看,能够具有能作义的所量只有自相,因为从量的实际发生来看,是否具有胜义层面的量果,只有从有无自相才能够判定。对此他者诘问曰:既然达成胜义有唯有自相之一相,陈那论师又如何说有自相与共相之二相作为所量相呢?对此法称认为:陈那之所以许有自相与共相之二相,原因在于,在实际认识的发生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以存在的“自体性”为所现对境以及存在着以存在的“共相体”为所现对境的不同。对此,他者问曰:既然真实存在唯有唯一的自相,但对这唯一自相的认识确有两种方式,那么在现量与比量这两种方式中,谁对谁错呢?法称认为,肯定比量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如以“所作性故”因而欲成立“声无常”时,于其时自心所现“声无常”并非是“声无常”之自体,而是通过分别心将现量境中“离分别”层面对“声无常”的确认,将其通过第六意识妄执“声”为“无常”之缘故(27)关于这二者间的巨大区别,详见顺真《陈那、法称“量 —现量说”与笛卡尔、布伦塔诺“悟性 —知觉论”之比较研究——兼论老树的“象思维”》一文中关于现代大德虚云老和尚闻声悟道之特殊经历的阐释,原文刊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亦即从认知的具体发生过程来看,依现量能量对“声无常”的确认与依比量能量对“声无常”的确认,其在量果的真确程度上,是绝对不同的。不过,即使法称认为比量是错误的,但其仍旧认许比量为量的一种,对此其亦有非常细密的阐释:
意乐无欺故,虽误亦是量。见由余相知,此品已答讫。如于珠灯光,以珠觉而趣,错知虽无别,于作义有别。如是虽无义,比量于现彼,由作义相系,故安立为量。(28)法称造,僧或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第182,182页。
僧成大师释曰:“虽是错误而是量性,意乐于所趣境新生无欺故。又获得自相,应不须以自相为所取境,以除以摩尼为所取境外,现见由余行相亦能了知获得摩尼故。应不以自相为所取境,以于此品计自相为所取境者,已答讫故,虽错误,然不得所趣境,则不相同,如于珠光与灯光,以珠觉而趣,此二觉属于邪智虽无差别,然于获得有作义之珠则有差别故。(于珠光处求珠,则可得珠;于灯光处求珠,则不得珠。)如同彼喻,了达声无常之比量与于彼比量所现之觉,如如所现义虽同非有,然安立汝是不欺诳量。以与汝作用所趣境相系之名言,是符合实义之名言故。”(29)法称造,僧或大师释,法尊法师编译:《释量论释》,第182,182页。此中包含几层意思:第一,与现量相比,比量误将非实之自相妄执为自相,是对能作义之自相的虚妄增益,因此在认知量果的层面来看是虚妄错谬的,但其仍具有量的性质。原因在于,从能量的动机来看,比量意向性地将认知功能投向于所量对境,乃是刹那新生且没有欺诳的,亦即所成对境相分不是无分别、刹那新生故为欺诳,但其主观意乐即认知的意欲动机,是无有分别而为刹那新生且无欺诳的。第二,从能量对所量来看,对自相性质之所量的获得,亦非绝对唯有以自相为所取对境而能获得。原因在于,譬如以摩尼宝珠为例,固然以其自相本身为根本性所取对境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际经验中,亦可由其所生而在认知者心中生起的其他表象(如摩尼光)获得对摩尼宝珠本身之认识。第三,虽然依据“余行相”而获得对摩尼宝珠的认识是世俗有,而非胜义有,故其为错谬者,但在更为具体的实际经验中,即使在不能直接获取自相所趣对境方面,两者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比如依据某一摩尼珠“珠光”而欲认知摩尼宝珠本身,与依据某一酥油灯“灯光”而欲认知摩尼宝珠本身,两者的认识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亦即我们若顺着摩尼宝珠“珠光”之方向亦可获得摩尼宝珠之所在,但如果我们顺着酥油灯“灯光”之方向则永远也不可能获得摩尼宝珠之所在。原因在于,摩尼珠光与摩尼宝珠本身具有系属关系,而酥油灯光其与摩尼宝珠本身绝无系属关系。以此为证可以确认,如以“所作性故”因去溯证“声是无常”这一比量发生时,虽然声之无常的自相性对境没有呈现,但“所作性故”因确实是不欺诳的能立因。原因在于,由能量心的意乐动机所生起的与所取对境相联系的语声名言如“所作性故”,其与“声无常”这一存在的本然是相符合的。因此,比量亦是一种量。不难看出,法称的阐释是何等的洁净精微!若将此处之论述与其在《定量论》《成他相续论》中关于比量的评判相会通的话,则法称对比量的价值性判断是确然性鲜明的。由是我们亦可以勘透“自义比量”的核心乃是系属,但这一系属并非单单形式化的系属,而是比量作为随量其由果溯因的能立因之所以是正因,亦即能立因之所以为正因的根本保障,绝不是世俗有层面的系属,其来源、其保障、其归宿皆是源于人类认识与认知具体发生过程中其与作为真实存在的胜义有之间层面的不相离之“系属”性,亦即作为存在者性质的比量,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确实性的知识,乃是源于其与作为存在性质的现量之间的不相离关系,若就陈那、法称量论因明而言即是确实性的比量之“共相”必源于真实性的现量之“自相”,若就笛卡尔探求一切真理的指导原则来看,即凡一切演绎,若保证其为确实性的知识,当且仅当其必以直观为起始原理的唯一来源(30)详见[法]笛卡尔著,管震湖译:《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原则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13页。。是故佛教因明的“因论”必须建立在“量论”尤其是“量论哲学”亦即基于逻辑与认知向度的哲学诠释之基础上,唯如是才能够真正揭示出“自义比量”亦即“自义随量”的内在机理与本真面目。
总 结
陈那一生历经唯识期、正理(因明)期、量论期三阶段思想历程的内在转变,其于正理期即在《因明正理门论》中明确指出人类认知唯有直观性质的现量与绝对基于现量之比量的“二量说”,进而彻底取消圣言量,确立了大乘佛教逻辑与认知体系的基本构造。同时从存在论的向度对现量与比量二者间的关系作出基础性的界定,并在《集量论》中给予进一步的深化。到其再传弟子法称著“七部量论”,更是从量论哲学的高度,深刻回答了比量之所以能够作为量的胜义有层面的学理依据,使量论因明的比量观在存在本体论层面得以圆满成立。当然,确立二量说尤其是比量智根本属性的体认与建构尚有另外一个学理向度,就是陈那创立且独具特色的关于大乘佛教语言哲学方面的apoha亦即“遣他论”的深刻体系,因篇幅所限,将在其他专论中给予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