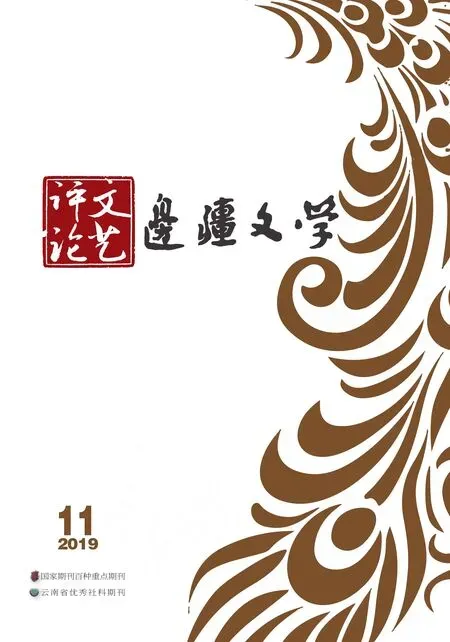文学批评还能更好些吗?
——刍议“李建军现象”
周思明
A
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确是空前繁荣,仅就长篇小说而论,就已年产4000部以上,如果再加网络小说,年产量就更加惊人。但需要问询的是,在这繁荣表象之下,又有多少入心入骨的感人之作呢?现在,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华丽模仿而非沥血原创,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不少“聪明”的作家往往省略了深入生活这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缺憾等等,也往往视而不见。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挖空心思走捷径、赶时尚。而当代文学批评的滞后,批评家对一些严重的文学问题的视而不见,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我们的文学批评像文学创作一样,出现了令人悲哀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的堕落趋势。
现在人们常常会问:在汗牛充栋的文学批评文章中,为何很难见到让人心悦诚服、痛快淋漓、刺刀见红的好的文学批评呢?更进一步追问,何为好的文学批评?或者,文学批评能否更好些?其实,好的或更好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并非理论多么新颖先锋、博大精深,也不是文章写得多么俏皮华美、与众不同,而是面对泥沙俱下的庞杂浩繁文学作品、思潮、现象,敢于不失去底线地发出真实声音。当然,这里的真实,不独是敢说真话,还包括会说真话。真话蕴含我们通常讲的真、善、美三要素。真,就是要讲真话、道真情、求真理;善,就是合目的、合伦理、合法则;美,就是行文美、表达美、形式美。做到这三点非常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用心用力地去呼唤、追寻和创造。
放眼当下文坛,虽然批评文章如泉水般涌现,但许多评论家习惯于锦上添花,不愿、不敢做作家的诤友,不具备替读者鉴别优劣的责任担当精神。正如评论家丁帆指出:“在中国文坛百年来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中,我们寻觅到更多的是亲密关系,鲜有毫无瓜葛关系者,像傅雷当年批评张爱玲作品那样,只顺从自己内心世界好恶,率性而为的批评,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消逝了。”“我们缺乏的就是那种真正敢于面对自己良知的大批评家的胸怀和勇气,像别林斯基那样对待自己捧出来的大作家果戈里违反作家良知的行径的猛烈抨击,在我们的文坛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即便是在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所谓‘黄金时代’,当然,鲁迅先生的批评是有这种风格的,但那多是在文化范畴之列。”丁帆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批评不缺少诸多的理论,也不缺少林林总总的方法。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批评家的品格,缺少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批评家往往成为理论的‘搬运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成为‘官’与‘商’的使用工具。百年来新文学的批评让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瞒和骗’的批评。”“当然,文坛上也不缺一些少数‘真的猛士’,但是‘真的猛士’却又往往带着个人的恩怨与情绪,也同样有损于文学批评的形象。”(丁帆:我的自白——文学批评最难的是什么)
置身于一个文化多元而驳杂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有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批评家能否用独立的见解,去启发创作者,去引领读者,使他们形成有价值的创作观和审美观,显得特别重要,也非常必要。米兰·昆德拉说过,写作就是写那些无人敢写之事,讲那些无人敢言之语,这就意味着要反一般人之常态。创作的乐趣就在于此。值此文化语境中,研讨批评家李建军及其文学批评实践的经验与不足,就显得十分重要,也自有其启迪价值。
B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李建军可谓一名尖锐泼辣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风格是坦诚的、尖锐的,不留情面的。他对当下中国文坛的贡献在于严肃批评了一系列被众多文学评论家捧上了天的名家作品,指出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作品消极、污秽和残忍的所在,无情地揭开中国当代文坛被遮蔽的作品真相和创作病象,因此被称为“中国批评界的良心”和“文坛清道夫”。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群体中,李建军无疑是其中颇具批评实力的发声者。与当下许多平庸或不平庸的评论家的“顺”(顺势而为,顺着来,讨好卖乖)相比,李建军表现出明显的“逆”(逆势而为,忤逆,反着来),像他的名字“军”,意味着“戈”或“兵”,是敢于亮剑,是兵戎相见,是刺刀见红。越是赢得文学评论界一致赞誉的名家作品,他越是不苟且,不盲从,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审视、去思考,进而得出与众不同的批评见解和结论。李建军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是以别林斯基等大批评家为标高的。在《文学批评的震天霹雳 ——纪念别林斯基逝世165周年》(李建军:2013年5月31日光明日报)一文中,他特别提到,别林斯基对那种低三下四地讨好作家的势利的批评家深恶痛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他反对“文学中的偶像崇拜”:“什么东西曾是、现在是、我认为将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将是极度妨碍在俄罗斯传布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培养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学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总是社会幼稚的命运。……要冒犯几个芝麻大的小权威,我们还得拥有对真理的公正无私的爱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权威就更不用说……”别林斯基知道冒犯这些“偶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无所畏惧:“跟社会舆论进行战斗,明目张胆地反对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胆敢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有勇气,毋宁说是为了对真理的无私的爱。”为此,别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他被称为“冷评家”和“酷评家”。有人则编造谣言侮辱他的人格,试图从道德上击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有像别林斯基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在前,李建军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对任何文学权威,他都从不表现出一点盲从和畏葸,而是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进行理性冷静的分析辩论。比如,在他的评论集《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对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批评,就显露了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独立思考素质。他将《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日戈瓦医生》《百年孤独》进行比较,在对《白鹿原》作了基本肯定之后,也直言无忌地指出《白鹿原》比《百年孤独》“低一个层次”。在他的上述文学批评著作中,李建军对阿来小说诗性语言弊端和性呓语怪症,对阎真小说议论过度的短板,对刘震云小说主题模糊的症候,对莫言小说的残酷暴力书写,对余华、苏童、格非、马原、残雪等作家作品的病态,对二月河小说“唯皇史论”,对贾平凹、王安忆作品的“伪艺术”表现,都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评。
C
身为一名以文学批评为志业的年轻学者,李建军的坦率与胆识是值得欣赏的,也十分难得的,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从不随大流,也不盲目唱赞歌,而是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深知并认同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经典语句。尤其是置身新世纪文学批评这种缺乏健康批评风气,缺乏成熟批评意识,缺乏科学可靠批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的不正常语境中,李建军尖锐指出:“批评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如其所是地说真话,这就要求社会必须给人们说真话的自由,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社会,他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攘斥佛老,定于一尊……”
我颇为认同李建军的观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非常匮乏的是真正的批评精神。何为“真正的批评精神”?用李建军的话语表述,它“不是由某种单一的精神元素构成的,而是包含了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如科学精神、宽容精神、人道精神、自由精神等。但是,在整个精神批评的多元构成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还不是这些精神,而是不从的精神、对抗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或者简单地说,是一种敢于为敌的精神。是的,真正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它的时代和文学的敌人。它与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迎面而立,以对抗者的姿态,做它们的敌人——一种怀着善念说真话,以促其向善推其进步的特殊的敌人。”用李长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叔本华等人的观点表述,真正的批评精神“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地了解并欲其普遍于人的宣扬热诚;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决断,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批评应当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暧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迂曲的说法”,“只有充满生气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充满热情、充满强调不满的人,才能写出充满生气的批评”。
李建军的批判精神和巨大勇气来源于鲁迅精神传统。他旗帜鲜明地声称“我们今天依然需要鲁迅”。“中国的事情,还是鲁迅先生看得最透。……鲁迅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我们的时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一个尺度,我们借此考察自己的生存景况,认识我们寓身其中的社会和时代内部微茫难辩的真相。”李建军将鲁迅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楷模”“先行者”。“需要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引领,需要他的声音和勇气,需要他的正直和无畏。”李建军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可谓是作者文学批评思想之大成的书籍,正如编辑者朱竞在该书“编后记”中所言,“在文学批评家们日渐失去个性的当下,李建军的个性锋芒更是异质性、批判性和对抗性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永不放弃高贵的尊严。……他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守护自己的文学信念。”
D
当然,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在《文学及其时代的敌人》中说,“真正的批评精神是包含了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如科学精神、宽容精神、人道精神、自由精神等。”但是,与中国当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身为文学博士的李建军,也许还没有成为一名文化修为足够成熟的个体,也还没有形成科学完整的哲学观 、价值观、文学观,他的文学观还存在比较片面甚至偏激的因素,这种情形源于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的价值立场不成熟、不完整、不辩证。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他会受到自己价值观、文学观、道德观的潜在影响,从而会出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及以道德批评替代文学批评,一旦发现作家作品出现道德弊端就实行一票否决,再提不起对其文学价值分析的兴趣的极端性偏差。
考察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本,似乎与其所认可的“真正的批评精神”的丰富多元,尤其是科学精神、宽容精神等明显有些相左。李建军的批评不留情面,直言无忌,这点非常可贵,也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极为稀缺的品质。但恕我直言,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他,似乎缺少了一点科学的辩证的审视能力和论说力量。不独笔者,亦有批评者指出,李建军对小说的定义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一切,这就暴露了他对文学批评内涵理解的偏狭与粗疏,某种程度上也拉低了他的文学批评水准。此其一。其二,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往往从局部而非整体、从个别语言、语法逻辑而非整体上的文学表达、美学逻辑、思想发现,甚至会从道德层面而非文学等层面来考察和评论作家作品。更甚者,有时会将文学与道德不加区分地搅在一起、混为一谈地进行道德化批评。当然,道德批评也属于文学批评内容之一,但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不能因为批评家眼中的审美对象存在道德瑕疵而全盘否定作家作品的价值,也不能将道德批评置换成道德化批评。此者,正如马克思在其《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所言:“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在李建军设置的个体文学批评语境中,只要作家作品涉及到性的描写,那么整个作品就都是不道德的,肮脏的,不值得肯定的。而从不考虑作家何以要写性,写性的历史原因和合理性何在。当然,像贾平凹、莫言等作家作品对于大便、鼻涕、屎尿、生殖器、性色、情事的不断重复、渲染、张扬,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给以严肃批判。但除此之外,认为他们的作品毫无可取之处,瞥见一只苍蝇就要扔掉一盘菜,发现一颗老鼠屎就要推翻一锅汤,这种批评做法,似乎也缺乏辩证法的精神。批评家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可否将缺点和优点剥离开来,可否将婴儿和洗澡水分开,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一股脑倒掉?这本是常识,无须耗费太多时间讨论。
以上所论,涉及到的话题乃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也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但是,“文学的道德化”和“文学化的道德”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厘清二者的关系,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同时对文学价值的甄别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说李建军所批判的当代作家对道德秩序违背的书写都是合理合法乃至正确无误的,其中不少的确存在比较明显的粗俗、低俗、恶俗问题;但也不能说李建军对作家作品中的道德问题书写的一概否定都是无无懈可击的,尤其是当他将作家作品中的道德问题与文学问题混为一谈,甚至以前者彻底否定后者的时候,这种批评就应该打上一个疑问号了。在此意义上,我倒觉得,李建军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批评结论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应该更多建立在令人信服的文学理论总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偏概全、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批评。这里,应该把个体主体道德观与作家作品中的道德伦理书写区别开来,把“道德的文学化”与“文学的道德化”区别开来,并对之进行学理性的评价与言说。
创作主体的艺术良知与社会道德良心之间的关系,历来非常复杂,既是长期困扰创作主体的一个悖论性问题,也是严重困扰一些文学批评者的认识误区。如何妥善处理创作主体以及批评主体的艺术良知与道德良心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艺术良知与社会道德良心的同构共建,窃以为是批评家李建军乃至更多从事文学批评的作者亟须解决的显在问题之一。
李建军对当代一些名作家的批评,的确存在上述问题,即抓住个别短板和薄弱环节,甚至抓住一些语法逻辑问题、错别字语病问题,对批评对象给以否定性评价,这与鲁迅先生“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原则不尽相符,无形中流露出批评家个人的情绪。80后批评家金赫楠曾撰文指出,李建军的批评病象有三:一是道德癫痫与文学洁癖。他片面地定义“小说世界本质上是伦理世界,只有那些包含伟大的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有持久和巨大的影响力。”“小说就是道德说服和伦理向善。”简单的道德主义与过度洁癖是李建军面对文学作品时的出发点。二是连环箭、板转以及“掌声和鲜花”,此乃李氏文学批评套路。所谓连环箭,就是对一部名家作品死磕,一而再再而三地撰文批判。还有扔板砖兼偶尔抽空送出点掌声和鲜花。比如他的少数表示肯定的文章和散见于年度小说点评以及季度小说点评文章中偶现的叫好文章。三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此乃李氏文学批评方法。“定性”分析法是指不厌其烦寻找小说叙述语法错误,然后归类定性。“定量”分析法是指罗列名家作品不妥用词和用句,然后用数字准确地表达。小说毕竟不是中学生作业,往往没有是非对错标准答案,该含糊时要含糊,该宽容时应宽容。文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有时正是其复杂性、多义性、模糊性和非技术性。李建军文化修养很高(博士毕业),但生活阅历极贫乏(同他批评的作家相比),审美情趣纯至洁癖,道德诗意特别丰富。本质上他是一个思想简单、自尊自大、毫不缺乏外在活力和道德激情(甚至严重过剩)的评论家,不仅远不是所谓“中国文学的良心”,而且还实在是一个值得警惕和质疑的不复杂但怪异的文学批评现象。(金赫楠:《李建军文学批评病象观察》)这种批评风格和姿态,应该引起批评家的自省。
E
在中国当代文坛,批评与创作之间关联性的断裂,一直是被人们广泛诟病的突出问题。批评的“自说自话”与创作的“自行其是”是这一格局给双方带来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当批评沉湎于“一味表扬”之时,也同时是创作“自感良好”而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感之际。一方面,是批评的绵软乏力疏远了丰富活跃的创作;另一方面,是创作的浮躁急就呈现为粗制滥造、佳作匮乏。“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文学批评只有从“问题意识”导入,以“价值关怀”应对,以求知、求真、向善为诉求,才能于创作有益。正如创作不能脱离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批评也不能脱离对作家创作的价值认知与学理建构。对于“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往往是充满变量的。在许多情况下,由这些变量而造成批评的复杂性,能够使批评者获得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但也有可能因批评者视野所限、定位不准而让人身陷沼泽、四顾茫然。文学批评无疑具有显著的“学问”特征。有人把这种“学问”概括为“求知之学”与“求真之问”,不无道理。文学批评的“学问”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即先“求知”再“求真”。批评作为社会公器之一,既不能“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问题意识”是其首当其冲的重要元素。
今天,我们在此讨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次对于文学批评的反思,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近年来出现一对悖论,人们把文学乱象的产生归咎于批评的堕落,归咎于评论家们把文学批评搞成了文学表扬;但如果有批评者动真格地批评起来,马上便有被批评者或他们的朋友跳将起来,给批评者扣上“酷评”“棒杀”“‘文革’遗风”之类的罪名。在这样的情境下,评论家们都学乖了,只想当“好好先生”,多栽花少种刺。是的,傻子都知道,得罪人的事情不好做,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骚,招人怨恨不说,还可能失去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和机会。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人人都知道文学有问题,作家作品有毛病,但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把问题和毛病当优点和亮点说。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只有找准了问题,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中,李建军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善于发现问题的“异数”。换言之,他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总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他最为人们所欣赏的地方,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最稀缺的意识。与他的批评短板相比,他的这种敢于亮剑、直言无忌更值得褒扬和珍视。
西方哲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文学批评是一项偏于理性思考的工作。它不是工作总结,不必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有评论家自我的独立思考、独特见解以及独创锋芒。在此意义上,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虽有其片面性,但他的真诚和坚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是屈指可数的,因而值得肯定和褒扬。其实,即便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的文学批评也不总是正确的,或有剑走偏锋和阐论片面的时候。但他们那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立场和态度,永远是文学批评者需要见贤思齐的旗帜和标杆。
中国文坛极度匮乏直言不忌的批评家,中国文坛也很需要敢于亮剑的批评家。因为有了这样的批评家,中国文坛才不至于彻底堕落塌陷,读者也才能在文坛充满阿谀奉承的雾霾中窥见那些“著名作家”“文学大师”皮袍下的渺小、庸俗。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李建军文学批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在想,如果李建军能够正视自我,扬长补短,深刻领会文学批评的辩证法,对当代作家多点“理解之同情”,其批评标准更趋于辩证、全面、公允,他的文学批评事业一定做得越来越好,并取得为世人瞩目的更大成就。

周圆 雁门雪 油画 50×7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