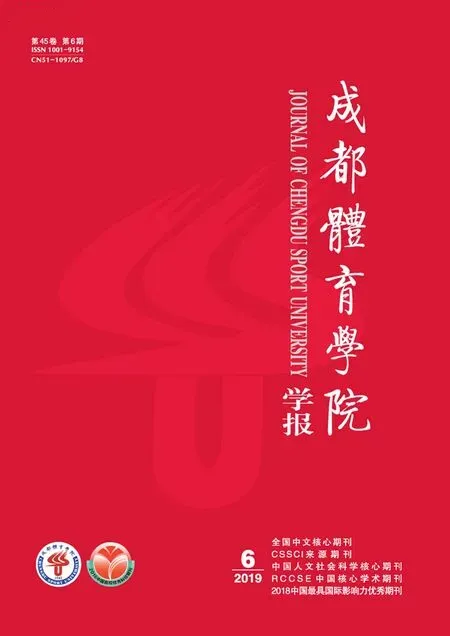论现代体育“文明竞赛”的历史生成
张 新
“文明”的反义词是“野蛮”和“不文明”,从人的行为举止来理解,“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的集合。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总是在塑造着更加“文明”的行为规范,尽力使人们表现得情感有节、行为有度,从而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而文明行为体现在体育竞赛领域,就是竞赛者以运动家的心态参与比赛,你不能输了比赛就恼羞成怒,向对手施以拳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尊重结果、尊重对手的风度。所谓体育活动中的“文明竞赛”,就是以文明的方式参加竞赛,其核心是体现出“fair play”精神,“fair play”有两层意思,从遵守规则层面讲就是“公平竞赛”,从体育道德的层面讲,就是“光明正大”地去赢取比赛。
体育竞赛与文明行为之间看似一个悖论,因为争夺胜负的激烈对抗最容易引发情绪失控的攻击行为。自工业革命开始,现代体育逐步形成了一个行业治理体系,各体育协会、职业体育联盟不断通过对规则、章程、仲裁等明文规定的修订,来整治违规、违德的不文明行为。其中竞赛规则针对运动项目的“玩法”,明晰了裁判判罚的尺度,避免比赛因规则争议而中断;章程针对运动竞赛的组织管理系统,界定了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和奖惩办法;相对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则根据规章来解决竞赛纠纷,处罚违规行为。这些有章可查的硬性规定和操作系统,对体育竞赛行为形成了强制性的约束力,其目的意义是倡导现代文明“公平竞争”的法则,并承续古老体育竞赛中逐步形成的道德传统,在现代体育竞赛中表达平等、友好、团结的时代精神。
体育“文明竞赛”的法则为何陡然在工业经济时代普遍确立,并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高颂的体育精神而畅行世界?本文的逻辑出发点首先是在体育竞赛悠远的历史中寻找“文明”的基因传承,在前工业时代寻找直接影响现代体育的行为道德风范。
1 古代体育中的文明竞赛基因
美国体育史学者阿伦·古特曼把资本主义时代早期发展至今的体育活动统称为现代体育,认为现代体育发端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然后传播至西欧、美国,以至全世界,而中世纪及其以前时代的体育则为古代体育。同时,阿伦·古特曼还持有一个重要观点:体育脱胎于人类的游戏,是本能游戏(Play)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有组织”的游戏(Games)[1]。的确,游戏活动与人类相伴而生,是体育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初级的体育竞赛游戏是个体之间自发相约的活动,而体育竞赛游戏过程中紧张、期待、欢欣鼓舞等情绪体验总是给人无穷乐趣,很容易吸引观众围观,发展成为在社会人群面前公开进行的竞赛表演活动,或者体育竞赛营造的欢乐气氛与国家庆典融合为一体,成为国家庆典的一个仪式组成部分,使民间的竞赛游戏演变而成公共体育竞赛。荷兰游戏理论学者胡青伊加就认为公共体育竞赛是游戏发展的高级形式,他说:“另一类得到高度发展的游戏形式,是在倾慕的公众面前进行正规的竞赛和优美的表演。”[2]那么,无论是民间随意的体育竞赛游戏还是公共体育竞赛,人一旦投入到这些体育竞赛活动之中,会形成什么样的基本范式并传承哪些文明竞赛的历史基因呢?
1.1 竞赛法则的约定俗成
动物和人的游戏都是天性所致,“人”一开始就与游戏相伴。游戏与功利性的日常生产劳动有本质不同,生产活动要直接创造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游戏就是人们“空闲时间寻找个人趣味的一桩事情,从游戏开始到游戏结束并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愉悦松弛或者表演展示就是游戏的目的。非功利性是游戏的一个本质特征,Sports的词源演进就印证了游戏的非功利性,port意为“搬运”“港口”,加dis否定前缀就意指离开劳动场地进入娱乐状态,由中世纪英语单词disports简写而来的sports一词泛指各类娱乐活动,至工业革命时期sports才特指体育运动[3]。而体育运动竞赛是游戏类别中有组织的高级形式,人们一旦摆脱日常生活轨道进入体育竞赛的游戏世界,就必须听从这个特殊行为现象自身规律的安排。
游戏总是在预先划好的场地上进行,竞技场、广场、赛马场、网球场、牌桌等,把日常生活隔离开形成临时的游戏世界,游戏者首先需要承认竞争对手的对等身份,否则竞赛的前提就不存在。最为典型的案例是15世纪法国的一个真实故事,法国诺曼底地区一个叫古贝维尔的庄园主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说,他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被自己的仆从撞断了肋骨,卧床多日却对仆从没有任何抱怨[4]。可见,游戏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有着自身的秩序。规则就是统辖这种特殊秩序的灵魂,哪怕是临时不完善的口头约定,参与者都必须遵从,因为游戏活动不同于被利益捆绑驱使的生产活动,游戏是易碎的,随时会由于参与者的违规败兴而宣告无法进行。
规则是游戏的前提,个体间随意的竞赛游戏都要遵从规则的约定,而体育竞赛一旦与国家庆典等社会活动相结合,上升为拥有一定规模的公共体育赛事后,这种规则意识就会得到国家、社会群体力量的强化。相比而言古代世界的体育竞赛发展不均衡,因时因地不同。古代中国的蹴鞠、马球、捶丸等活动,出现了文本化的比赛规章,单个项目的竞赛形制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备,只是阶层等级的壁垒分野制约了全社会竞赛共享机制的形成。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竞技是古代世界运动竞赛的发展高峰,古希腊把运动竞赛的快乐与宗教庆典需要结合在一起,赋予了竞赛一种“神圣”的社会功用,运动竞赛具有“娱神”的功能,赛会参与者的“赌注”是自己的名望,违背公平原则的人将身败名裂。古罗马第一次在城市大竞技场用职业竞技来娱乐公众,面对上万观众的彩票下注与自身的名利奖励,角斗士的勇敢与技能是赢得声望的唯一途径。遗憾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竞赛传承被中世纪蛮勇的民族征战打破,游戏竞赛形式重新回到民间散乱粗放的状态。但在竞赛游戏中埋藏着文明竞赛的基因,在其悠长又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竞赛规则的顽强生长。
1.2 骑士比武的文明礼仪示范
欧洲的竞赛传统被蛮族迁徙征战中断几个世纪过后,于中世纪中期兴起了骑士比武活动。骑士比武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现代体育直接相连,不仅骑士比武的英语专用词汇“tournament”沿用到现代变成“赛会”的意思,至今美国网球巡回赛等赛事还在使用这个词汇,骑士精神也成为现代体育精神的主要来源。现代体育之父顾拜旦把骑士精神看作是现代体育精神的同义词,认为高贵的骑士精神是一切耐力和纯竞技活动的基础[5]。中世纪的骑士比武活动在其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化的竞赛体系,同时在竞赛道德风尚层面给后来的人们示范了一种高尚的行为举止。
骑士比武经历了从暴戾向典雅的转变,一开始并没有多少规则约束与情感限制。11世纪在法国北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极其有效的新型骑兵战术,即一队骑士手持重型长枪一起冲锋。作为新型战术的训练手段,骑士比武应运而生,并迅速流行开来[4]。骑士们“将参与决斗野力全部宣泄到了决斗欲望的保留地,那便是由人类所开辟的竞技场,决斗因为隶属于自然法则,才显得格外的放荡不羁。”[6]早期的骑士比武像狂暴的战争演习,没有多少规则可言,对双方人数或武器装备没有明细要求,使用武器为真刀真枪,有时候群情激愤的平民观众也可能持械加入战团,很容易造成重大伤亡事故。13世纪中后期,骑士比武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一对一策马对刺比武中,规定了长枪刺中对方身体不同部位的记分办法,由此根据二人几回合比赛结束后的得分来判断胜负;在群体比武中,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1292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有三个关键条款:首先,骑士无论多富有,每人最多只能携带三名扈从上场;其次,无论骑士还是扈从都不允许携带锋利的刀剑或钝头锤;最后,现场观众和步骑仆从一概不许携带武器[7]。由此控制了场上对抗双方的人数,避免观众与随从加入混战。这个时期规定比武使用武器必须是钝枪头,并且要提供贵族身份证明。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从竞赛形式上把骑士混战变成了贵族专属的骑士体育。
与竞赛方式“体育化”演进相对应,是骑士文明赛风的逐渐形成。骑士阶层举止风度的一点一滴变化,源自于生活境况的缓慢改变。早期骑士基本上就是打家劫舍的一勇之夫,通过攻守战斗来分配调剂社会财富,杀戮抢劫完全符合当时骑士社会的道德水准,这种性格特征展现在比武活动中,就与后来的骑士精神大相径庭。12世纪英国著名骑士威廉元帅的两个案例,印证了当时骑士的一些道德缺失。一是采用诡计,把比武变成一场偷袭。英国的“青年国王”亨利在群体比武中多次吃亏,后来听取了威廉元帅的建议,假装不参加比武,等到场上的骑士打得筋疲力尽时,再带领奇兵出袭去窃取胜利果实。二是乘人之危,一次威廉元帅和他的同伴去饭馆吃饭,恰巧一个比武骑士在饭馆门前摔断腿,扑跌不起,威廉乘机把他俘虏了,用这名倒霉的骑士去换取赎金[8]。大约13世纪时社会力量与财富缓慢向大领主、国王方向集中,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骑士日益贫穷不得不向其投靠,成为宫廷侍臣或者拿饷的军官。于是欧洲各国的国王或大领主们的宫廷便成为骑士的驯化之地。与骑士个人微乎其微的自我情感约束比起来,宫廷社会的规制要强大得多。宫廷社会对内部交往的暴力活动有某种程度的克制,上流社会人际之间建立了一种美好交往的方式。人们的一举一动、一眼一瞥都十分讲究,需要在言谈举止中体现文明教养。勇敢忠诚、坚忍不拔的品质不再是骑士的全部美德,荣誉、公正、体面、慷慨成为“骑士精神”内涵中的部分核心价值。宫廷社会这些道德共识,对骑士行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采用不光彩手段取胜就会使自己和家族名誉受损。于是,骑士不再像早期那样乘人之危、恃强凌弱,而是在竞赛中显现出光明正大的品行,这些约束与品行也随时间一起传承至今天的体育竞赛之中。
2 体育文明竞赛的现代生成
中世纪后期,城市规模与货币经济日益发展,使那些主要依靠乡村庭院经济生活的骑士们被边缘化,他们不断感受到物价上涨与货币贬值的无奈。历史的前进终结了骑士的时代荣光,而市民阶层却作为上升的第三等级受到了历史的恩宠。市民群体不满足于平等原则只在上流社会的生活范围内实现,他们要求普遍的社会公正。城市人群新的社会诉求与情感模式,推动了现代文明竞赛机制的形成。
2.1 货币经济背景下现代体育伦理的蕴育
体育竞赛的发展历史中,商业活动与体育竞赛之间存在一种互通的共同法则,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呈现了两者彼此的紧密关系。古代希腊体育竞赛得以普遍流行,除了宗教祭祀赋予其神圣意义之外,城邦工商业经济形态中也蕴涵着内在推动力量。城市工商业者要求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契约关系实现市场交换,公平竞争是商业精神也是游戏竞赛的法则,也可以说体育竞赛是这种社会精神的载体和道德搬运工,两类活动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随着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盛,体育竞赛机制与商业经济秩序同生共进的趋势更加明显,甚至两类活动就生发于同一块场地上,通过词源考查我们可以隐约追寻到历史演变的痕迹。英语“fair play”意为公平竞赛,根据英语字典“fair”有多个意思,包括集市、集会、公共露天游乐场、美好的、公正的、光明正大的等等,在英语造词的意义引申中这些多层含义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特别注意到,“集市”与“露天游乐场”两个含义同出一词恰恰符合了当时城市的建筑格局。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平面布局围绕中心广场一圈圈环形展开,街道围绕广场呈放射状延伸。领主拿到国王的特许令后,除了建设城堡和铸币厂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赋税来源的市场,城市中心广场就是集市交易场所,同时因为是开敞空间,也就顺利成章地成为公共露天游乐场,足球、曲棍球等竞赛游戏时常在这里开展。可见,商业活动与游戏竞赛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必然遵循相类似的法则。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就是公正的、美好的和光明正大的。“fair”可以组合成商业用语,比如公平价格“fair price”,也可以组合成竞赛术语,15世纪英国诗歌中出现了“fair game”,16世纪末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约翰王》中使用了“fair play”一词。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fair play”的使用频率更高,到1792年,英国出版的第一本体育期刊就经常使用这个词汇[9]。“fair play”一词还传播到了西欧其他国家,德语中至今还在采用这个外来的英语词汇,标志着“公平竞争”观念在更广大地域的流行。
货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竞争的方式,?竞争手段文明化了,不再主要通过争夺土地等不动产的武斗方式来决定贫富,市民阶层的竞争是对市场机遇的竞争,通过经济手段来取得自己在同行业中的优势地位,这样的竞争方式把社会发展导向了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同时也引发了现代伦理观念的塑造。随着职能分工明细和学科专业发展,市民阶层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见识和教养,特别是经济条件优越的绅士阶层承袭了骑士贵族的优雅美德,这是一个贵族精神市民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体育观念生发的过程,绅士作为现代体育的开创者,树立了公平竞赛、尊重对手、尊重裁判等现代体育的道德准则。
2.2 工业生产背景下现代体育规则的诞生
与现代体育伦理同步发展的是运动规则的完善。“普遍的、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法律准则从属于工业社会所有制形式,法律准则的形成是以很高程度的社会联系为前提”。[10]工业生产的分工协同,商业交换的日益频繁,需要制订更细密的法律条文来协调监管。除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规范商业交换之外,改造公众的休闲方式也是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首当其冲就是对集市与街头的竞赛表演进行整改,立法机构从公共治安的角度限制随地进行的竞赛表演行为,1835年英国颁行的“公路法”授权警察可以监禁处罚这些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对于街头狂野的足球比赛与有奖格斗比赛等流行运动项目也进行了严厉打击。1839年英国又出台的“城市警察法”,授权房主可以在生活与营业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要求表演艺人离开[11]。中世纪式的集市、街头竞赛表演活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正规固定的竞赛场所,权利机构立法支持建设运动场、健身场所、休闲公园、林荫绿道等基础设施,使公共竞赛表演活动进入文明有序的发展轨道。
英国城市警察法和公路法的颁布,把集市、街头竞赛逐渐引向了专用体育场,标准的场地更需要规范的规则、章程来维护竞赛活动的内在秩序。于是,各运动项目逐步开始了对传统竞赛游戏的文本化规则改造,在学校操场、赛马场、公共运动场诞生了现代运动项目。赛马是中世纪就流行的古老运动,也是现代最早在标准场地进行比赛的项目,伦敦以北约105公里的纽马基特逐渐成为英格兰的赛马中心,1727年,纽马基特的工作人员约翰·切尼把赛志汇集起来出版了《切尼的马赛》一书,使竞赛有章可查,由此翻开了现代赛马运动的篇章。[12]足球同样是中世纪的粗野游戏,15世纪法国诺曼底地区曾经流行的苏勒球(Soule)比赛,两个教区各自上场的参赛人数都超过了500人,这项对抗激烈的游戏是现代足球与橄榄球两大运动的共同源头。184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们由于来自不同的公学,各校规则不同使比赛很难进行,于是他们讨论制订了著名的《剑桥规则》,框定了现代足球竞赛的基本范式,也使足球在运动形式上与橄榄球分道扬镳。拳击比赛在英国曾经是赤手空拳的暴力格斗,1743年,著名的拳击手杰克·布劳顿推出一套包括7条内容的规则,使拳击运动向文明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到1838年制定的《伦敦职业拳击规则》进一步降低了拳击野蛮色彩。其余如射箭、网球、击剑等运动项目,普遍经历了现代规则的重新设计。
有了标准的运动规则,使运动项目迅速跨地区流行开来,伴之而生的就是各类运动协会、职业体育联盟的先后成立。1863年10月26日成立的英国足球协会就宣称,其宗旨是“为了规范足球运动而起草一套明晰的规则。”[13]现代体育规则体现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科学精神,经过一个设计——实践——再设计的过程,运动项目的玩法逐渐完善,仿佛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通行。同时,针对运动竞赛中不时出现的不良行为,各类体育组织陆续制订了实施行业管理的相关章程。其目的用意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所描述:“努力在体育运动中发扬公平竞赛的精神,消除暴力行为;采取旨在防止危及运动员健康的措施。”[14]自此,标准化的比赛场地、文本化的竞赛规章、专业化的争议仲裁、国际化的协会组织等程序规范,构建了文明竞赛的现代机制,并依靠工业经济对外扩张的压倒性优势把这种竞赛模式推向了全球。
3 现代体育文明竞赛的当代发展
社会文明的要旨之一即是对暴力行为实施法规管控,使身体强壮的人不能随意对他人发泄攻击欲望。体育文明竞赛的意义,就是通过规则与伦理的双重管制,对竞赛情绪和行为施加长期有效的影响。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深层次理解当代体育竞赛中的诸多现象。
3.1 体育规则对暴力色彩的改造和保留
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攻击欲望,它与饥饿、情欲等其他情感因素构成了整体的心理状态,社会总是要设法建立一种强迫机制,把情感宣泄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同时人们基于对处罚的惧怕,逐渐会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心理机制,一旦有突破他们心理接受程度的出格行为,就可能产生厌恶情绪。各个时代流行的不同运动项目,通常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情感水准和审美情趣。今天我们如果看到盛大的罗马角斗比赛,在情感上会难以接受,但在罗马人看来却是视死如归勇敢精神的体现,角斗场遗址的文物发掘证明,女性观众甚至一边在看台上看比赛一边做着针线,反映了他们处之泰然的心理状态[15]。
冷兵器时代西方最为流行的竞赛项目,先后是角斗士竞技与骑士比武等战争模拟游戏,现代体育却朝着有节制的体能碰撞与人道主义方向发展,激烈的对抗项目都经历了规则化改造,比如现代拳击运动,1838年的《伦敦职业拳击规则》明文规定不能攻击对方腰带以下的身体部位,并宣布踢人、咬人等都属犯规,使拳击运动变成了人有节制的攻击与搏斗表现。现代足球运动也因为规则变化而日益“文明”,1848年的《剑桥规则》的一个核心条款,就是争夺时只能踢球,不能踢对手的脚踵,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在讨论这条规定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有的学生认为废除踢脚踵就是废止了该项运动体现出的勇气和胆量,但最终还是通过投票表决出台了“不能踢人”的规则。到1863年英国足球协会颁发第一套全国规则,进一步废止了绊人、踢人、推搡等粗野传统。[13]“文明”是时代发展的趋向,许多古代血腥的竞赛项目都被看作是一种陋习,或者消失或者得到了改造,“松子酒巷、刑场买卖、狂饮酗酒、兽奸、穿上带铁钉的鞋为奖金而进行致命的打斗,所有这些的消失都不足以哀伤凭吊”[16]。
另一方面,体育竞赛又适当保留了对抗竞争的暴力性,因为攻击欲望始终隐匿于人的天性之中,当社会武斗活动被刑法严格管控之后,体育赛场就成为社会许可的宣泄战斗欲与攻击欲的“保留地”,观众在“观看”中有节制地发泄了他们的情感。于是一部分运动项目保留的暴力性,就成为其运动风格的魅力所在。橄榄球被称为“百码战争”,美国体育史学者古特曼评论说:“在公园将一行人拦腰截住并将他摔在草地上是暴力行经,但中后卫球员在赛场上做同一动作就当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暴力。”[1]同样,足球比赛中凶狠的铲球,背后拉拽的战术犯规;篮球运动中故意在对手罚球技术不好的球员身上犯规,都是争夺胜负的战术需要,可以使比赛更加紧张精彩。一些运动项目甚至包含了规则允许的暴力形式,冰球运动甚至默许打架,但这种打架行为是中世纪骑士体面比武方式的现代翻版,一般仅发生在两名球员之间,开打之前还会用眼神示意通知对方,并且都会放下球杆、摘下头盔等金属器皿,避免造成过度伤害,偶尔打斗升级为多人群殴,裁判则有一套规则和办法止息纷争。当然,比赛场上的暴力性和运动员的暴力行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身体合理冲撞呈现出的暴力性,是为了让比赛更具观赏性,而比赛场上恶意报复造成伤害的做法,则属于暴力行为,将受到行业协会或者联盟的严厉制裁。
现代文明竞赛规则建立了竞赛秩序,“猫眼”等摄像技术的运用,使比赛判罚更加精密,电视回放功能为裁判二次改判提供了便利,也为体育仲裁机构提供了呈堂证供,那些在比赛中飞踹对手、向裁判吐口水等不文明行为都难逃“法眼”,必然会遭到禁赛、罚款的重处,违规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由此也会受到损失。而出于对违规处罚后果的畏惧,运动员的“暴怒”通常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了冲突升级和中途退赛等过激行为的发生,保障了体育竞赛持续有序地激情上演,成为当代人类的一场精神狂欢。
3.2 道德对体育竞赛行为的约束
体育规则是一种对体育竞赛行为的外在约束,体育精神是引导竞赛行为的内心驱动,哪怕符合规则的举动,一旦违背了现代体育道德原则就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在足球比赛中就经常出现这类典型现象,当场上有球员受伤倒地后,持球一方球员通常会把足球踢出界外,以便暂停比赛让伤员得到救治。恢复比赛后,获得掷界外球机会的一方球队,按理要把足球踢还给对方,这是一种不成文的约定。2012年欧洲冠军杯比赛中却出现反常,乌克兰矿工队在与丹麦北西兰队比赛时,矿工队前锋阿德里亚诺意外地抢断队友大脚踢还给对方门将的皮球,并且射门得分。根据规则进球有效,阿德里亚诺却立刻遭到对方球员的围堵谴责,阿德里亚诺没有违反比赛规则,但他有失“fair play”的体面,这粒进球也被媒体评论为“不道德的进球”。[17]
现代体育规则并不能制约消极比赛甚至故意输球,比如足球比赛中如果有意“自摆乌龙”,把足球踢进本方球门,现场裁判也无法根据规则实施处罚。可见在规则约定之外,需要体育道德的约束,2018年女排世锦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只要“故意”输给荷兰女排,就能够以小组第二身份进入四强淘汰赛,从而避开实力强劲的意大利女排,增加进入决赛乃至夺冠的机会。但中国女排没有想过要“故意输给谁”,在战胜荷兰之后,中国女排虽与意大利队苦战五局惜败,无缘染指冠军奖杯,却很好诠释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现代体育精神赋予了竞赛行为一种“正大光明”的风范,早期英国绅士在足球比赛中,当对方红牌罚下一名球员后,为了避免以多打少,本方会主动安排一名球员退场。上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球员容志行面对场上经常性遭到的违规侵犯,从来表现得不愠不火,被媒体称誉为“志行精神”。2015年12月16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一场自行车赛上,车手伊斯梅尔·埃斯特万在距离终点300米时遭遇爆胎,他只能扛起自行车跑向终点,竞争对手奥古斯汀·纳瓦罗拒绝超越,慢慢地跟随在埃斯特万身后。最终表现骑士风度的纳瓦罗只获得第4名,当埃斯特万主动把铜牌赠予他时却遭到婉拒,另两名超越的车手分获冠亚军,按照规则也无可厚非,而纳瓦罗的“古怪”行经却使他站上了荣誉的制高点,这是对骑士“体面”观念的久远继承,又体现了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一种精神追求。
4 结语
运动竞赛的基本形式是自古而然的,核心都是力量、速度、技能的较量,其有序进行的前提是竞赛者必须遵从规则约定,最终以一个不可预知的胜负结局给观众带来癫狂的情绪体验。所以,现代体育文明竞赛的形成过程中传承了人类古老规则意识与竞赛伦理的基因。但古代世界的审美情感与道德水准,使体育竞赛活动更多带有暴力血腥的野蛮习气,甚至伴有角斗、决斗等戕害生命的行为。现代体育的生成背景是工业生产方式带来的城市人口大量聚集,市场、财富、教育、娱乐的新格局要求建立相应的法治秩序与情感模式,尤其是生命意识与平等观念的高涨,使得体育竞赛也在历史的累积中发生了质变,高尚道德牵引在前,严厉规章约束在后,犹如两根缚绳制约了竞赛者暴力情绪的肆意宣泄,把野蛮的竞赛方式升华为体系完善的现代体育文明竞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