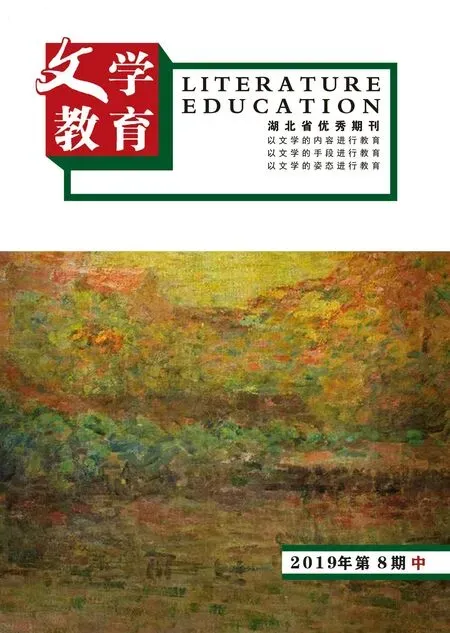中和之道,井然之境:《论语》中庸观阐析
程驰也
先民自古尚中和,视“中”为处世之道,“和”为立人之本。《论语》继承了先贤在体察自然万物的过程中所萌生的朴素中和观念,并将其发展延伸为一种以仁与礼为标杆的中正不倚的道德准则,成为贯穿于传统儒家道德精神的不可或缺理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先行性地呈现出儒家中庸思想的雏形。
一.《论语》“中庸”观的内在思想
《论语·雍也》首次明确指出“中庸”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此,孔子将中庸纳入个人思想体系的基本道德范畴,视其为德之至。何晏释“庸”为“常”,即“中和可常行之德”[1]。唐时孔颖达引郑玄对《中庸》篇名之解,指出中庸乃“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2],“庸”即“用”。宋时理学家则进一步诠释之,朱熹解“中”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为平常,中庸即谓不偏不倚而持中和谐。程颐释“中”为不偏,中者即天下之正道,“庸”为不易,庸者即天下之定理。今学者或理解中庸为“以‘中’的思想方法认识和理解事物,并将这种思想方法落实于行动”[3],“中”为“适当”义,“庸”即对“中”的认识的践行,同“用”。上述观点对“中庸”内涵的阐述在本质上有一定贯通之处,“中”作为“适度”理念成为中庸观核心精神所在,“中庸”可理解为不偏不倚、和而不同、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理,强调于日常生活中实现圆融自然的和谐之境。
二.《论语》“中庸”观的显性呈现
在儒学思想体系层面上,作为“至高之德”的中庸观表现为以仁为内涵、以礼为外化的道德理念,但它所具方法论性质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具有实践性的处世原则。因此,《论语》所蕴含的中庸观既是一种审慎平和的处世态度,也是需于生活中践行以知分寸尺度的实践性行为准则,从而在为政从教、交友处世、道义品性等方面得以具体落实与呈现。
(一)刑礼相济的为政治国之策
《论语·尧曰》引《尚书·大禹谟》之典提出“允执其中”,“中”为尧禅位于舜时所授治国关键,即欲使四海免于困穷,则必恳切坚守中正之道。孔子的中庸观念首先表现在为政治国之理上,可将其解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思想,意指为政须有宽猛两面,二者相济相协,依实情而变通,由此使为政治国之策抵达“宽猛相济”、“刑礼相补”的和之境界。
君子之于天下无适无莫,只恪守“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将中庸之理贯通于治国治民,但并未严格规定限制各种条框,而是以礼义为执政标杆,无所亲密或疏离,其中庸观可见于其在一定度域内的圆融平和。同时,孔子提出从政之“五美”观,即君子治理政务当遵从五种美德:给予百姓恩惠而无多耗费,使百姓劳作而莫使其怨愤,可欲而不可过分贪求,庄重平和而不骄矜自傲,威严肃立而不严酷凶猛,此为孔子以人本为度域而落实至政治的中庸理念,即于仁与义、刑法与礼治之间的公正和平衡。
(二)学思相合的从学教养之道
《论语》的中庸治学观可突出表现为其学思并重的思想。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p18)(《论语·为政》)孔子治学以学为根本,并济之以积极的思索,二者不可偏废,而又需有所克制。如在《论语·公治长》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虽为瞻顾周祥,但孔子则视思之至三者为太过,因思虑过多亦引流弊,反而有失,故主张“再思”,由此体现思考之于实践的中庸观念。
在学思相合的基础上,对求教者所询疑难困惑应从不同角度反复诱导,详悉其始末,“叩其两端而竭”,方可得明确譬解。孔子“叩其两端”的提出,表面上为对其教学理念的阐述,但从思想归属而言却为中庸观之表现。孔子就子路、冉有所言“闻斯行诸”之问给以不同答复,即出于对象个性不同特点而作不同解:使懦弱退缩者进,使好勇胜人者退,“约之于义理之中”,便无过不及之患。无论个人求学或指点他人皆需以此为鉴,把握两端之度以顺乎中庸之道,实现学思相合之养,此为中庸适度观在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上的生动呈现。
(三)和而不流的待人接物之理
《论语》的中庸观同时表现在待人接物的处世实践中。在处世方面,孔子强调万事万物均有一定度量界限,言行处事若“过”或“不及”皆未归于中道而偏离至德,故在行事上有“再,斯可矣”原则,在思想举措上有“过犹不及”说,面对对立矛盾的两端当以“致中和”调和,秉持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4](p97)(《论语·述而》)即立足于人与自然之平衡的中庸实践观,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4](p35)(《论语·八佾》)的中庸文艺观,无不体现出守持自然平衡的中和境界。
在交友及与人相处上,孔子亦有所判断与选择,所谓“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4](p50)(《论语·里仁》)即谓事君访友需晓中庸之理,过则烦冗、添辱或增疏。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4](p197)(《论语·子路》)“行”即“道”也,孔子指出当同合乎中道之人交往,若不可得之便择狂狷者。狂者激进,“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保守,“知未及而守有余”,二者皆偏于一面,过犹不及,不合中庸平和之道。在一方面,孔子批判“乡愿”等混淆善恶者为德之贼,肯定与行得其中之君子交往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孔子之择友观未流乎偏激,并不决然为实现中庸而中庸,而是与“狂”、“狷”者交往亦可,并非落落寡合,且对待不仁者也需采中庸态度,因疾之过甚亦引祸端。显然,孔子之择友观蕴含着入世济世的高远理想,同时也可从中见其中庸观在择友层面上的追求与贯彻。
(四)文质彬彬的君子品德之养
中庸观在人格修养层面普遍表现为对君子品德情性的培养,质朴少文则粗野鄙略,文饰过度则诚或不足,唯有文质相胜,方见君子风度。《论语》中对君子品格的界定甚多,如述从政之“五美”时所提“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p306)《论语·尧曰》),如言君子“和而不同”、“泰而不骄”[4](p200)(《论语·子路》),如形容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4](p240)(《论语·卫灵公》)等。
孔子自身亦致力于对中庸观的践行,其徒赞扬孔子作为师长“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4](p103)(《论语·述而》),其贵在温和,但温和中亦有严苛,举手投足均出于礼制要求,庄重威仪却显谦和,端庄矜持却不止于求恭,而是实现内心的安定祥和,三者对立统一,在协调与平衡中突出孔子“执两用中”的君子品性,也体现了孔子在自身要求上对中庸德行的落实。君子的中庸品德意味着在生活实践中尽心贯彻中庸之道使己自觉地近于至德。在平衡个人修养、调和内外关系的过程中抵达文质彬彬、张弛有度、兼容并举的中庸境界,亦唯此方可为真君子。
三.结语
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孔子以仁义为核心,继承先哲“尚中贵和”思想之精华,将中庸观贯穿于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使其成为象征至高之德的精神文化特质。虽明确的“中庸”概念于《论语》中只一见,但这一儒家所倡导的理性实践精神却贯通于《论语》之中,是孔子待人接物、立身处世、成德达仁的重要价值观兼方法论原则,更在传承中进一步为宋代诸儒延续发展为理学思想分枝,对社会道德表现和个人意志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论语》中庸观所倡“中和”理性精神并非生硬刻板的折中主义,而是实现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在此设想下,人人皆致力于对中庸德性的遵守及对泰然平和之境的追求,也为和谐社会的理想时代蓝图提供了思路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