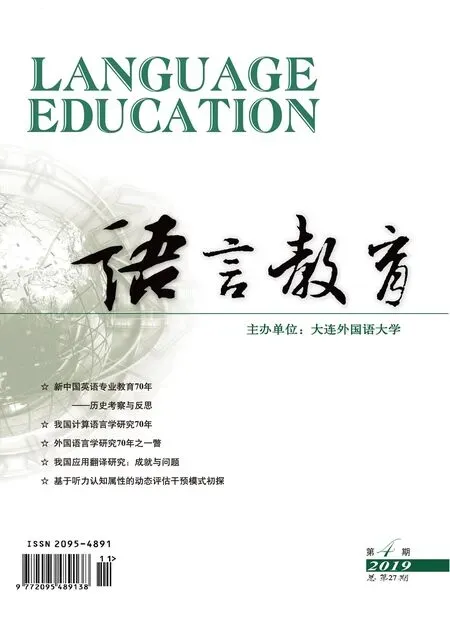“红色经典”批评语境与李民的翻译题材转型
李金树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1. 引言
“十七年”(1949—1966)是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红色政权主导国家管理,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构、强化、巩固其合法地位。在此时期,翻译被纳入计划化和组织化的轨道,翻译赞助系统高度“一体化”,形成了特殊的翻译和翻译批评语境。因此,“译什么”即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其中,李俍民对“英烈传”的翻译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建国初期(1949—1952),与成名已久的翻译家如梁宗岱、张谷若、卞之琳等相比,李俍民似乎籍籍无名,其翻译选材主要集中于儿童文学。1953年,他却凭译作《牛虻》而名噪一时,被誉为“国内有影响的十大外国文学翻译家之一”(刘立胜,2014:46)。目前关于李俍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翻译成就和翻译思想的梳理(如刘立胜,2014;温中兰等,2010;吴笛等,2008);二是其经典译本《牛虻》的讨论和阐释(如倪秀华,2005;卢玉玲,2005;朱安博,2008;刘嘉,2015;王东风,2015)。研究者大多聚焦译作分析,而较少(或几乎不)关涉李俍民翻译选材从儿童文学转向“英烈传”背后的历史隐情。虽有研究者认为,李俍民的“英烈传”翻译选材是受其个人生活经历、阅读趣味和家庭的影响,①刘立胜在谈到李俍民的“英烈传”翻译选题标准时,认为“这种选题标准与他一生投身革命事业及家庭革命传统分不开”。见刘立胜,李俍民翻译成就与翻译思想考,《兰台世界》,2014年第13期第46页;同时,李俍民在其《我的自传》中也表露了自己“英烈传”翻译选题的心迹,从行文上看,主要是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详见王寿兰编,《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289页。但考虑到“十七年”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李俍民的“英烈传”翻译选材似乎不应简单归结为译者的自觉行为,其抉择背后似乎另有推手,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本文将从“红色经典”的界定入手,通过缕析“红色经典”批评语境形成的脉络,探析李俍民自1953年起进行翻译题材转型的真正动因。
2.“红色经典”批评语境的形成
2.1 “红色经典”的界定
何为“十七年”间的“红色经典”,学界争论颇多,众说纷纭,似乎并未达成一致。“作为一种历史命名”(张立群,2005:70),“红色经典”有其特殊的内涵和指代。“红色”是指作品的政治倾向(阎浩岗,2009:1),指向“阶级、信仰、意识形态、权力”(何云波,2007:16);“经典”则是指作品在其生成的时代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与历史影响,以及它们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性(阎浩岗,2009:1)。还有研究者认为,“红色经典”是指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材以革命历史为主,内容主要是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孟繁华,2015:20)。
显然,所谓“红色经典”并非一般的普通意义上的经典,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学样式的标志”,“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田建明,2005:21)。正如张法(2005:22)所言,“红色经典”的核心意义在于“代表着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十七年”间,“红色经典”的形成,并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包括译本)经典化所产生的制约和驱动,“它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是在集权话语体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别无选择的必然结果”(赵学勇等,2003:52)。
本文所称“红色经典”,是指1949年之后国内影响广泛、以塑造和歌颂英雄人物为主旨的翻译作品(主要是苏联)和国内创作的文学作品。译自苏联的“红色经典”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幸福》《真正的人》《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暴风雨所诞生的》《日日夜夜》《前夜》等等。国内“红色经典”的范例即广为人知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①“三红一创”和“青山保林”是指《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等8部长篇小说。这八部长篇小说的“红色经典”地位,代表了主流政治话语对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的规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十七年”间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的走向。
2.2 主流政治话语与英雄叙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主流政治话语对文学主题和人物形象作了旗帜鲜明的勾勒和设计。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报告指出,文艺之“新”,在于“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等方面。报告强调,工农兵是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文艺的重点在于塑造工农兵形象,语气坚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的作品必须着重地反映这三个力量。……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与国家建设的主体的缘故”(周扬,1984:528-529)。
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成了时代的要求,并逐渐演化成官方叙述。“新的英雄人物”是大家关心和热烈讨论的主题。1950年4月1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中,特别列举苏联革命斗争文学的范例,如《铁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士敏土》等,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茅盾,1950:17),积极塑造英雄人物。各级报刊也纷纷载文,鼓励和助推“新英雄人物”的创作。1951年4月22日,时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的陈荒煤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一文,明确提出“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创作的方向”(陈荒煤,1951)。随后,他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创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典型》一文,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掘军中典型,书写英雄事迹。1952年,胡耀邦在《解放军文艺》第1期发表了《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一文,鼓励和倡导作家“表现新英雄人物”。这些文章引起了人们对新英雄人物创作的关注,《文艺报》甚至在1952年5月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转引自庄桂成,2010:124)。1953年9月,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表现新的英雄人物是“当前文艺创作的最主要的、最中心的任务”,并且指出“决不可把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地位”。郭沫若更是总结了“典型英雄形象”的人物特点,即: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转引自寇鹏程,2013:125)。在官员、作家、文艺工作者等齐心协力的“关注”、“热议”、“批评”中,创作或表现“新的英雄人物”逐渐演化成了“十七年”初期一场巨大的文学思潮。
英雄叙事在翻译界也得到了积极回响。《翻译通报》曾在1950年第1-6期连续刊出“翻译工作笔谈会”,发表诸多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的意见。在“目前急需介绍哪些外文书”项下讨论中,笔者注意到,“革命”或“英雄”的字眼不时出现在译介话语中。现兹举四例。
(1)目前急需介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湛著作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活动状况。(吴力生,1950:1950:34)
(2) 进步的小说,进步作家和革命家的传记,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的斗争史和建设经验的报告。(王宗炎,1950:38)
(3) 苏联及诸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期间宝贵的经验,描写在建设斗争中英雄楷模的文艺作品。(范之龙,1950:38)
(4) 希望翻译一些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名人传、革命史,也希望介绍一些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刘希武,1950:51-52)
革命题材和英雄人物在“十七年”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英雄或革命题材作品的青睐和译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红”流!例如,由梅益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仅1952年就出过50万本”,到1965年六月,该译本“共印46次,印数达136.9万册”。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亦分别于1956、1961年翻印过这一译本”(方长安 户松芳,2006:155)。因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说是“一本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教科书”(邹振环,1996:411)。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其他大量以苏联国内战争或卫国战争年代为背景,描写英雄人物英勇斗争的“红色经典”被积极译介进来。如《丹娘·索罗玛哈》《前夜》《恐惧与无畏》《战地日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的女儿(娜塔莎·柯芙肖娃)》《战士们》《暴风雨所诞生的》《金星英雄》《真正的人》《日日夜夜》等等。这批译介的“红色经典”对“十七年”的读者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①如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中指出:“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了愈来愈多的千千万万的忠实的热心的读者;青年们对苏联作品的爱好简直是狂热的。他们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当作自己学习的最好榜样。巴甫连柯的《幸福》,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都受到了读者最热烈的欢迎。他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人物,一种具有最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的人物。”参见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文学,1955年第1期,第8页。
对于政府赞助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新英雄人物的创造,对广大读者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道德力量的教育”;另一方面,“创造新英雄人物,还可以扩大文艺的表现领域,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的人民文艺”(古远清,2001:145)。因此,不难发现,无论是译自苏联还是国内原创的“红色经典”,都成功塑造了一位甚至是多位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恰好为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提供模仿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讲,将“红色”等同于“英雄”并不为过。创作或译介“红色经典”成了作家或译者顺应主流政治话语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一行为又强化和巩固了“红色经典”氛围的营建。
3. 李俍民的翻译题材转型:从儿童文学到英烈传
“红色经典”批评语境的成型促使“红色经典”成了确立创作或翻译规范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并构成“批评的参考框架”(佛克马,2007:18)。这一语境为李俍民的翻译抉择建构了充分的合法性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促使其调适自己的翻译选材策略。
据笔者统计,“十七年”间李俍民共翻译了外国作品76部,②因篇幅限制,76部翻译作品出版信息详见中国版本图书馆:《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涉及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五个国家30余名作者。在“十七年”初期,李俍民所译作品大都是外国儿童文学,接近40部。但自1954年始,李俍民新译作品共13部,其中儿童文学4部,占30.8%,英雄题材共9部,③这九部作品为:苏联毕尔文采夫的《柯楚别依》(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苏联瓦·贝柯夫的《第三颗信号弹》(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56年)、苏联柯季克的《苏联少年英雄柯季克》(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意大利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苏联柯拉斯的《游击老英雄》(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美国希尔德烈斯的《白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年)、苏联伊格纳托夫的《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第二部:克拉斯诺达尔的地下火;第三部:蓝色战线的崩溃)(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占69.2%,翻译选材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和调整。
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李俍民为何选择翻译这些英雄题材的作品?他认为,“以上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民族解放斗争、卫国战争和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或者烈士”, 这些作品都是“具有革命内容、于我国读者最有益的作品”(李俍民,1984:8)。作品的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成了决定是否翻译、取舍的标准。可见,对作品的道德诉求和翻译社会功用的彰显,作品的道德诉求和翻译社会功用的彰显,是李俍民审慎之后的终极决断。
上文已论及,主流政治话语对“红色经典”的宣扬,对“英雄人物”的赞许,促使李俍民做出某种价值判断。这里,笔者引用李俍民时隔几十年后,发表在《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回忆文章,然后再做简单分析。在谈到“在浩如瀚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为什么偏偏要翻译《牛虻》”时,作者写道:
梅益同志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我深深地迷住了……那优美、热情的译笔充分地表达了原著的精神,更使这部小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好些青年由于阅读次数而走上抗日与革命的道路。我喜爱这部书,也因此对它的作者产生了很大敬意,但同时在这部小说中却有一个问题使我无法获得解答,这就是牛虻问题……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说显然对保尔(其实也是对作者自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决心着手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牛虻那慷慨就义的情节和那充满必胜信念而又寄托着最深切、最真挚的爱情的遗书,使我留下了同情与痛悼的泪水。(李俍民,1989:283-285)
随后,他又谈道,
我的文学翻译选题的原则与信念就是:英—烈—传。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推动社会与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之所以要选择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英雄烈士题材的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主要目的在于“以书中英雄烈士的模范作用,从正面教育青少年读者,使他们懂得如何对待革命事业、对待人生、对待工作和学习,以至对待交友、恋爱和婚姻。”“我相信,对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在照顾他们物质生活的同时用大力进行正面教育,进行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品德教育。(李俍民,1989:288-289)
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李俍民的语录,在于其话语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作者承认对“英雄人物”的“青睐”是受了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甚至是“熏陶”。这恰恰印证了英雄题材的译作在建国初期所形成的辐射力,足见“红色经典”语境对译者的影响和制约;其二、作者之所以选择“英—烈—传”,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在中国的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普及甚至是灌输“英雄”、“榜样”的思想和理念,其目的在于“正面教育青少年读者”。可见,李俍民足够重视翻译的社会功用,凸显翻译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理念,应该说和“十七年”间对翻译功能的定位和批评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在1950年还在说“愿终身为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而努力”①据笔者梳理,在《翻译通报》总共20多期的文章中,署名“李俍民”的只有两处。第一处为综述上海苏联儿童读物翻译工作者座谈会的翻译动态;第二处即《翻译通报》刊发的“翻译工作者笔谈会”,李俍民的全部意见为:愿终身为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而努力。工作中的困难太多了,特别是“孔雀石箱”中的矿山工厂专门术语,与乌拉尔的土语,字典翻不出,普通的苏联人也不懂,最感困难。两文出处分别详见《翻译通报》1950年第4期第50页和第67页。的翻译工作者,在1953年后翻译选材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译者与主流批评“心有灵犀”,倒不如说是译者对主流批评的主动依附。显而易见的是,在举国上下营造出的宏大的“红色经典”语境中,留给译者选择和言说的空间毕竟是狭窄和逼仄的。由此看来,李俍民的“英烈传”选材,与其说是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倒不如说是“红色经典”批评语境规约下的“顺势而为”!这种“不谋而合”,有其个人因素,不容忽略,也不容置疑,但归根结底是时代语境与主流批评话语的倒逼使然。
4. 结语
主流话语对“英雄人物”的认同,为“红色经典”的粉墨登场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和精神基础,形塑了一种“英雄”的“时代精神”。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红色经典”,其落脚点均为现实政治,即通过“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价值谱系,强化新生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旨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利益。
李俍民以自己的政治敏感,通过“英烈传”的翻译选材,复原甚至建构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或模范人物,彰显了翻译叙事在译入语文化中的“道德实践力量”(刘小枫,2007:5)。也正是通过翻译,李俍民为自己的“英雄”激情找到了皈依的文字之所。翻译“红色经典”,是其审美意识与精神境界最为圆熟的表达和书写。李俍民的翻译选题原则,从最初的儿童文学转向“英烈传”,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文学趣味和个性审美,是一种主动策略,以个体呼应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此种转型亦是一种被动适应,是彼时“红色经典”批评语境规约下的翻译改写。因此,研究李俍民翻译转型的动机和规约因素有利于我们认识特殊时代语境中批评的制衡和话语的张力、认清主流政治话语和赞助系统对翻译抉择的建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