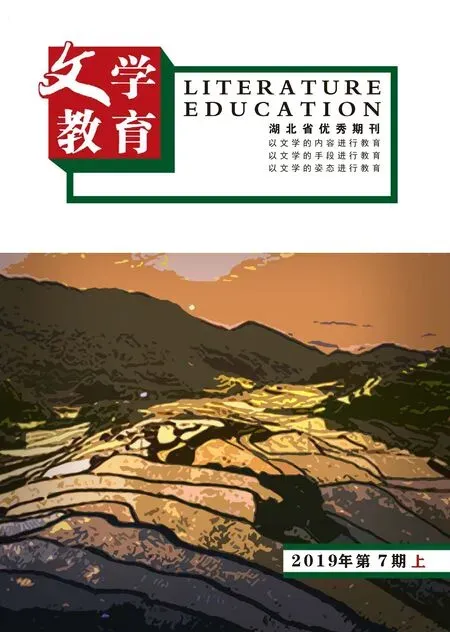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深圳文学的再生产
黄海静
一.引言
深圳,是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被誉为“创客之城”、“设计之都”和“志愿之城”。弹指四十年间,深圳作为中国南方大地一夜崛起的传奇城市,激荡着不计其数的象征这座城市名片的文学作品:有底层打工,述说都市生存;有校园青春,书写白衣飞扬;还有“深圳速度”,宣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深圳。城市与文学,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W·索亚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主义将空间意识和空间秩序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1]的空间批判理论,使得空间理论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掀起了一股空间转向之风。文学创作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场域,城市的空间生产也必然会根深蒂固于文学创作的土壤之上。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普遍的城市危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动态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统治的手段[2]。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精华,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答案。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城市空间分析结合起来,诞生了以戴维·哈维、亨利·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曼纽·卡斯特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3]
列斐伏尔首先意识到空间问题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巧妙地将视角转移到空间生产本身,将空间看作是社会巨大的资源——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过程一样,“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实质也是资本生产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社会、精神和物质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4]作用于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初步实现空间转向来进一步阐释后现代城市的本质。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给后来的哈维、卡斯特和索亚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哈维从生产的角度将地理学知识融入空间生产理论,认为资本(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在城市的兴衰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他的空间生产理论紧密围绕城市化过程。一方面,时空格局直接影响并主导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也反作用于城市时空的改造。在此基础上,他给出“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的重大结论和“资本的三种循环说”。
如果说哈维是从生产角度来研究当代城市社会,那么卡斯特则从消费领域出发研究空间问题。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深受阿尔都塞的结构理论影响。他认为,城市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系统,城市作为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体中发挥着巨大的消费功能,而这种集体消费也逐渐成为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力量。
紧接着,索亚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真实空间,而是通过意识和思维的加工想象,重新建构多重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景观。索亚极力反对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二元空间论”:非此即彼的绝对性,以移民文化在空间中的体现,揭示“第三空间”中不停转换和改变的观念、事件、现象和意义的社会环境。[5]
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断裂开来的一种新观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承和深化。戴维就曾指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将‘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城市空间’由此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6]此外,空间生产理论已走进地理学、文学、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视野,尤其是近年来空间生产理论延伸至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在文学、文化学领域掀起了一股“空间转向”研究的热潮,也逐渐形成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发展态势。
三.全球化下的深圳文学建构
在全球化资本积累高度集中和巨大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深圳文学在城市空间创造中渴望寻求一种象征身份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深圳文学本体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嬗变,使得文学植入空间成为空间扩张的强大动力。
1.身份认同:“文学深圳”的期待
深圳文学纷繁芜杂,在短暂的历史交汇中,似乎很难定义“文学深圳”。有人说,这是因为深圳外来驳杂,在各种异质文化冲突中很难找寻同一性和认同感。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认同感”是在话语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文化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得来。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依赖于“想象共同体”的催生,小说报纸等印刷媒介与“共同体”休戚与共,并在之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功用。[7]“文学深圳”的身份含混暧昧,它不像穆时英、刘呐鸥、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颇具西方摩登现代性的“文学上海”,也不似老舍、茅盾笔下颇有京城翘楚得天独厚的“文学北京”,这些地域文学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化身份和深刻烙印。因此,才有了吴予敏《渴望“文学深圳”的诞生》[8]和赵改燕《“文学深圳”的呼唤——深圳文学参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探讨》[9]等深圳学者对文学深圳的冀望。
2.形象嬗变:“改革之声——打工文学——书写青春”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试验田,凭借“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强音,诞生了风起云涌的“改革之声”文学作品。刘学强的《红尘新潮》极力渲染了“敢为天下先”的先锋深圳的青年形象。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借宣传邓小平南巡讲话营造加快改革开放进程的舆论环境,被誉为“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闻报道”,并成功入选广东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一步强化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城市面貌,生动地呈现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之初的时代巨变,满腔热忱、大刀阔斧投身改革的城市形象。
提及深圳文学,最为外人知晓的莫过于打工文学,已然成为深圳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的极速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罗湖、盐田、龙岗、宝安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不少的工厂,使得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深圳,诞生了一类特殊的群体:“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等等,这一群体不仅奠定了深圳“移民城市”的最初基调,还激发了大量的底层文学创作的灵感。代表作家有曹征路、谢有顺、戴斌、吴君、王十月等均将目光投射到深圳底层打工者的生活境况,记录了每一个打工者的辛酸生存史,向旁人娓娓道来光鲜夺目的城市背后无尽的悲情与无奈。
青春文学是深圳近几年新晋并备受关注的文学类型,成为新的城市主旋律。其中,在90年代初期带来较大影响力的莫过于郁秀的《花季雨季》,一度风靡全国,刊印量达200万余册,并被拍成影视作品,引起全国上下的轰动效应,自此,开启了深圳阳光写作的先声。校园青春作品的横空出世,不仅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极力认可,并且在字里行间的温暖文字中流淌出让阳光洒满深圳这座城市的热度,更集中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教养和格调。
3.空间转向:隐秩序的空间——同质化的空间
从全球化背景下深圳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的嬗变,我们可以看到空间转向理论作用于城市空间升级和文化转型的双重驱动力,并且这种空间塑造正从隐秩序逐步走向同质化。正如索亚所说,文化已经成为控制城市空间扩张、创造新空间形式的有力手段。
深圳从“海边渔村”、“边陲小镇”到改革开放,打工创业,这是其地域的特殊文化历史所赋予的,连结着深圳特定的城市空间所衍生的城市记忆和城市体验。打工文学很长时间在深圳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同样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的城市,却远不如十里洋场上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上海早已抢先完成了在空间塑造中展现近代艺术风貌和追求艺术真实的体验,而年轻的深圳城市空间的布局还刚刚起步,对文化和资本的追逐正驱使深圳城市创造出新的空间,从而满足城市现代居住人求异的需要。因此,现代深圳的城市资本扩张必将带来日益膨胀的空间需求,文化在走向大众化的今天,早已融入空间转向并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
深圳文化历经从无到有、制造繁荣、崇尚特立独行的城市空间塑造后,逐渐走向同质化的空间塑造,即遍布都市文化应有的物质化元素: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文艺清新的咖啡厅、劲爆火辣的酒吧等等,在统合了城市各种现代特色文化后的城市空间改造,名为走在创意求新的道路上实为让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变成了同质化的统一形态。正如索亚所说:“置身于购物中心和纵横交错的交通系统中,感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10]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置身被资本创造的不同历史文化的场域中,却毫无违和感地体验着似曾相识的城市现代空间。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深圳文学再生产
深圳文学在城市空间改造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担当重任,无论从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还是文学生产的内部规律,都与城市空间生产的现代流动性休戚相关。正是在这种文化与城市复杂互动背景观照下,推动了深圳文学的再生产,勾勒出全新的深圳文学图景。
1.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立市”
城市中定居的人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换言之,城市中有什么样的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伴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的涌入,给这座城市的文化基调抹上了“奋发”、“拼搏”、“创业”、“勇敢”等别样色彩。这些选择深圳背井离乡的“移民族群”所带来的多种异质文化的杂糅和冲突也使得深圳文化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造就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创业奋斗”的“移民文化”。但在改革之初,深圳曾被外界诟病为“文化沙漠”,在这里只看到资本商业熏心,却很难寻觅先进文化的踪迹。为此,深圳政府举全力突围“沙漠”瓶颈,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坚定“勒紧裤腰带也要把文化建设搞上去”的决心。从80年代的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大剧院、深圳大学、新闻大厦、博物馆和电视台等八大文化设施的建设,到90年代的关山月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书城、华夏艺术中心、有线电视台、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深圳商报大厦和深圳画院等新的八大文化设施的筹建,再到如今的深圳湾体育馆、深圳湾公园、深圳音乐厅、深圳歌剧院、深圳艺术中心等层出不穷的高阶文化设施的出现,从“深圳读书月”到“文博会”等文化融合创新活动的成功举办,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明程度正在新时代被不断刷新,先进文化像一剂强有力的粘合剂,将城市空间与文化生产环境交叠组合,共同将这座城市推至高度文化自信和现代文明的巅峰。
2.文学生产的内部规律追随空间生产的流动性:“市场化”——“资本化”——“文化产业化”
市场是深圳文学生产的中心,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状况,文学生产势必会受到传播、消费、读者群、批评家等市场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当文化热点从精英文化逐步走向大众文化的今天,文化的现代性受到“消费”、“娱乐”等新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文学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又必然会与销售、出版、广告宣传、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预示着文学生产逐渐从“市场化”走向“资本化”。资本一旦走向市场,通过资本的组织来完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并将之发展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组织严密、市场利润回报率高额的“文化产业”,这更揭橥了资本全球化下的本性——追逐高利润的产业化升级。
当文化由“市场”走向“资本”,再到“文化产业化”的生成,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空间生产速度不断增长,城市的空间更新周期也随之加快。因此,今天空间的更新交错已不单是时空的物理安排,而是与资本积累的弹性动态水乳交融。文化在植入空间生产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被空间生产所改造。正如深圳城市文化的更迭,当80年代的“移民文化”、“打工文化”、“改革文化”等文化冲击纷至沓来,新世纪初便迎来了“志愿文化”、“深圳先进文化”等新的呐喊。总的来说,在时间消灭空间、时空压缩的资本生产下,一方面文化不得不适应空间生产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文化同时也在时空中被创新、变化和替换支配着。
五.结语
四十年来,深圳文学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资本与文化整合的双重背景下,使得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学形象予以重构,并逐渐走向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解读下,文化在城市资本运作逻辑下的再生产,空间剥离了原有的物质载体而被各种社会关系所覆盖。深圳正处于城市化继续高速发展的迅猛阶段,城市的空间扩张更新与文学的空前发展构成一种复杂互动的辩证关系,在此过程中,文化生产一方面适应资本追逐利益而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空间生产改造文化光鲜的表征却依然不能忽视文化内在的审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