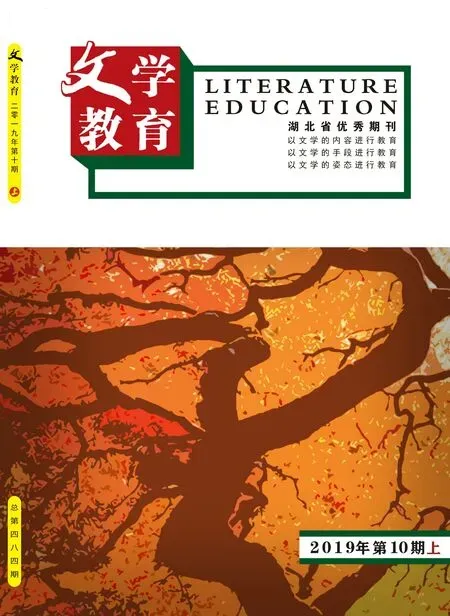创作主体视阈下南宋中期艳情俗词的文化生态
马 月 王佳蕊
隆兴和议缔结至宋宁宗下诏伐金的五十余年中,朝廷偏安,词坛中兴,晏安酖毒之下,曾被政局压制、为雅词排挤的艳情俗词重开新径,在热望与失望之绪相峙的中期社会中直诉心曲。与花间词相比,南宋中期艳情词有着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生态,这与其特殊的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笔者将从南宋中期艳情俗词的创作主体出发,研讨创作主体相关的政治背景、地域属性与其创作机制,以蠡测此时期艳情俗词的文学生态。
一.酣醉之时:士气雌伏的社会环境
南渡之后,随着山河破碎之日渐久,士人的热血渐渐被朝廷之偏安浇冷,沦肌浃髓的国恨亦钝化。虽然宋孝宗“恢复之志甚锐”,然而朝廷上下循默贪逸,便也难以扭转“士气伏不作”的大势。于此环境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望殷切,有“精忠自许,白首不衰”的家国责任感,一种是束手叹息,最终投身于自己的一隅天地中,只在烟火中偶尔悲世玩世。
患有集体怔忪症的南宋中期社会,无疑是冷者众而热者寡。无论是魏阙中人,或是江湖散客,体制内外的两大创作主体皆少有激声。但不同的创作主体所作艳情俗词虽大体皆妩媚之声,反映出来的心理机制与审美形态却因其阶级特性有所差别。
(一)体制内的士大夫
1.英雄失意,托志帷房
沉酣之世,官场犹有未醉人。他们坚持抗金的理想,有着“敢爱不货身”的使命感。但在举世鼾声中,孝宗尚且无力救世,这些英雄又如何免于失路。除了郁勃悲愤的抗金词外,许多名臣皆有艳情词传世,这些词多为“托志帷房”之作。如辛弃疾,其艳情词“深情如见,情致宛转,而笔力劲直”,词的如花色貌之下,都有如火肝胆,如剑铁骨。“我自是笑别人底,却元来,当局者迷”(辛弃疾《恋绣衾》),虽是少用意象直抒胸臆,却是对“香草美人”式的思君传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们写作艳情词并非忘世界,作醇雅之词时,是为退避浊世,刻意“落入俗套”时,也只是以“入世”的方式忧世戏世。实际上,他们依然在以换了声腔的低音在呐喊,缱绻之中暗藏不平之鸣。他们的艳情俗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表现,是一种通过虚构的女性声音所建立起的托喻美学,无论是词体生命痛苦的蜕变还是华丽的转身,皆类乎“基因重组”后的基因还原,是一种不自觉的超越又不自觉的回归。”
2.士子失语,寄情绣幌
孝宗即位后,高宗曾将一个太学生的“明日重携残酒”改为“重扶残醉”,看似风流,实际未易“残”的倾颓之势。光宁二朝靡落更甚,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的心态自上而下地形成。大部分“做稳了奴隶”的士子本就是疏离政治核心的寒士出身,具有“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二维复合的特征”,其积淀的平民世俗因子使其喜以艳情俗词吟咏自娱,“拿自己所能感受到的快乐的强度和限度来衡量人生的意义,最终把人生的乐事缩小到花前月下、樽前和歌女的樱唇上”。如“烟花不是不曾经,放不下、唯他一个”(曾觌《鹊桥仙》),对战局失语的士子们只求官能享受与刺激,不问社会与将来,由此产生的艳情俗词,便纯为风月作,毫无家国感。
(二)体制外的闲散客
中兴词人群中,学者官僚型文人依然执文坛牛耳,但江湖游士也占有一席之地。回避、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让更多平民有机会依违科考入仕,“国家举场一开,屠贩胥商皆可提笔以入”。平民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因此提高。然而,有限的官职致使大量寒士只能布衣终身。《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太学”载云:
(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壬申,时国学新成,补试生员,四方来者甚众,几六千人。(崇儒一之三五)
(孝宗淳熙二年)九月十九日,礼部侍郎赵雄言:“近日太学补试进士,多至万六千人,场屋殆不能容,理宜裁节。(崇儒一之四一)
(宁宗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千余人,分六场。(崇儒一之三九)
南宋中期考生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带来员多阙少的矛盾,据记载,“今三岁诏举进士,州以名闻者数十万,礼部奏之,而天子亲为发策于廷,去为州县吏者数百人。”如此比例之下,大量原有欲事朝廷之才学的寒士只能另寻他路,“代笺简之役,为童蒙之师”,为“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游荡江湖时,朝堂国事已远,词惟写身侧“俗”事,不思教化“雅”义。大部分已为“稻粱谋”磨平棱角,自弃“外王内圣”的儒士要求,少部分偶以游戏之声叹世,以艳情俗词呈示对部分士大夫式雅词的叛离。“你又痴,我又迷,到此痴迷两为谁”(石孝友《长相思》)“长忆当初,是他见我心先有”(赵长卿《簇水》),都以浅俗的口吻直诉不合中正的深情。因此,南宋中期词的创作中心下移,词作有平民化、世俗化甚至商品化的趋势。
二.婉娈之地:批风抹月的南方传统
江湖内外的词作虽有差异,词人寄身的江湖却相对恒定。“东南妩媚,雌了男儿”,讽彼时柔靡,亦说明了南宋中期词作的地域属性。中期三朝,南方乃“婉娈供养”之地,在缠绵之中孕育批风抹月的词作风格。
据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考证,两宋有籍贯可考的作者为880人,其词作量为17933首。其中南方浙江、江西等11省市有746人,占籍贯可考的作者总人数的84.8%;其词作量为13939首,占词作总量的77.7%。
籍贯可考而又可以确定其生活年代的有698人,其中北宋的南方人为216人,北方人为79人;南宋的南方人为362人,北方人则仅有41人。在北宋,北方作者占1/3;到了南宋,北方籍的作者所占比例仅为1/10。无论江湖内外,南宋词作者有九成为南方人,中期词人集中在浙、赣等地。
由此可见,南宋中期的词人大多出生或久留于南方,其词则承继了“南方文学”的传统。“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恰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
南宋中期的词坛其实是以临安为中心的南方词坛。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刻书业,“销金窝”式的市井与青楼产业,都为艳情俗词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词人们在南方奔走红尘,或是书剑飘零,迷花殢酒,或是狎妓冶游,买笑当歌,语俚俗而情猥冶,“如秦楼楚馆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1]不求格调,只为南音嘌唱。南方文学“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的风格凸显,而这些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又使汉魏遗轨荡然扫地,淫言媟语流泻南方,更与风月之地相缠绵,至元代北曲出世,文脉方转。
三.冶荡之音:阴性书写的审美范式
词与南方之地域密切相关,也与南朝民歌、南唐《花间》有着血缘关系,承绍着“要眇宜修”的文学家族血脉。沉溺于云痴月倦的南宋中期也同样长吟艳情之声,且仍有“词作男子而作闺音”[2]的特色。于血色花颜同艳的年代里,这样的冶荡风流之音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实际上,正与南宋中期复杂多元的创作主体相合。
于少部分托志帷房的士大夫而言,艳情词是向君王达情的文化胭脂。侘傺困穷之思郁结而不得发,政权压制下激声有限,有如蚌病成珠,艳情词便成了言志诗的变体。这样的词,虽说表面嬉乐于男女情事,俚俗平白,本质却合了“雅”的范式,作为“俗词”的纯度并不高。
但对大部分二维复合的士大夫与游士而言,艳情俗词正是熏香拘艳间直抒胸臆的佳径。他们扮作怜香惜玉的女性角色,作有情之声,纵无拘之态,几乎纯为娱宾遣兴,在不饰文辞、亦靡亦薄的簸弄风月中,常有至真之情流于肺腑。在南宋复雅传统之下,这些人的“公然走私”,无疑是在理学观念的威压之下寻找心魂的空隙,以“出轨”释放压抑。他们的艳情俗词往往被认为词格卑下,情无节制。有人区分情语与绮语:“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徘。”其实,绮语正因“不端”而真,不节制而深,是死水微澜里的滔天爱恨,可抒真正的“性情”。词坛常要求“中和”而免淫,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但尽脱情之缚,又何必为“词”,雅俗之争便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南宋中期的艳情俗词虽有创作主体避难声而自醉的嫌疑,但仍然有鲜灵爽直的可取之处。破除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那些花前月下的情事,在战火隐现时仍然纯挚,其实是一种个体生命力的张扬与情之本体力量的显现。
四.结论
南宋中期的艳情俗词有着特殊的文化土壤。在创作主体的视阈下,这些艳情俗词的作者在国仇未报、冗欲已生的政治环境与万马千军独过几人的科考竞争之中有着多维的身份背景与文化心态,使得南宋中期的艳情词因特定的心理机制而与寻常的花间声腔有所差别。这些创作主体的南方身份为艳情俗词的风格提供特定的文化源泉,南宋中期的创作心理又同阴性书写的审美范式水乳交融,共同构成南宋中期艳情词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