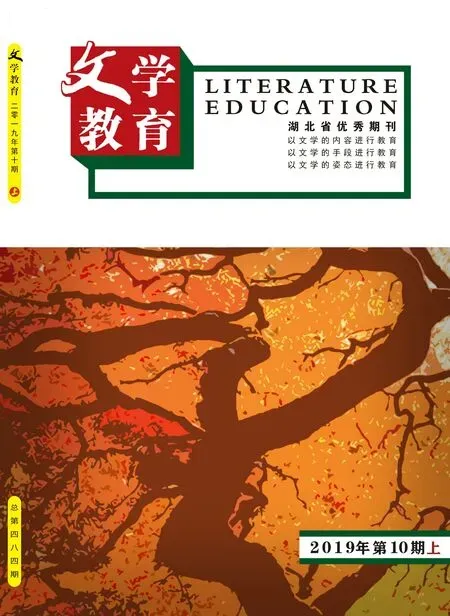论方方《风景》的叙事魅力
王安荣
方方在《风景》中给读者展示出人生风景,作者从生活的最底层切入,去描写生活、描写人生,展现人生经历。方方认为:“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1]方方着力表现人生风景的同时,也以着独特的叙事魅力在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探讨《风景》在叙事方面的成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方方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
一.特别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文章的讲述者。《风景》的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我”,在文章开头方方引用了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的一句话“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2]这句引言中的“我”就点出了文章的叙述者,他以一种高出生活的姿态看着一个奇异的世界、一段奇妙的风景。关于“我”,作者用冷静的语言写到“父亲买了木料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把小婴儿埋在了窗下。那就是我。……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忙,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3]
作品借助了一个亡婴之口“我”(小八子),讲述了这个居住在汉口铁路边上的棚户家庭,十一口人住在仅有的十三平方米里的几十年间的人生故事。方方采用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亡灵视角。“我”在出生半个月后就死掉,但因和父亲同样属虎,且同月同日同一时辰的生日而格外受偏爱,“我”是一个得到父爱的亡灵,得到了哥哥姐姐们一生都在渴望的父爱。方方采用的亡灵叙述方式,使作品带有一种悲凉感、沧桑感,整部作品始终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在引导着平凡人物的人生轨迹,这也就预示了作品主要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的悲剧色彩。
《风景》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父亲、二哥、七哥。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生活道路都在亡灵视角“我”的讲述下平缓地展开。父亲沿袭了他父辈的生存理念与人生理想,他一生都信奉力气与拳头,脾气粗暴,仅有的温柔都给了死去的小八子;他与妻儿的相处模式往往是以暴力为主,教育儿子、解决邻里问题都以拳头为主,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老一辈棚户居民的代表。二哥是一个与棚户家庭格格不入的青年,他对生活抱有积极的热情,时刻渴望着冲出这个令人压抑的黑屋子。他勤奋好学,是一家子中最具文化气息的人物,同时他身上还散发着原始的善良,他向往爱情,最终为了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七哥小时候过着屈辱的生活,这让他渴望过上一种受人敬畏的生活,这一信念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在经历灰暗的童年及潦倒的少年之后,一个人孤独地去小山村开始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因在夜晚梦游而被村民当做鬼,进而村民为了躲避这个白色的鬼魂而把他保送到“北大”,由此七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同样,五哥六哥辞职干起了个体户搬离了棚户区,做了汉正街的上门女婿,从此腰包鼓了起来,腰杆子也直了起来。通过“我”的叙述,兄弟姐妹的人生成为不同的风景,在每个兄弟的故事中都寄予了作家对现实人生及生存意义的思考。
《风景》以一个亡婴“我”的眼睛来看他家庭的变迁和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其实,死去的小婴儿本来是没有正常人的意识和感受的,作者却给他赋予了无所不知的能力和敏锐客观的观察眼光,让他在岁月中同兄长们一起成长。这种独特的亡灵视角被赋予了全知全能式的通晓全篇的叙述能力,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话语权威性,他仿佛高高在上,俯瞰一切事物。
作者让亡灵站在作品的上空,用神灵似的力量在观察着人生风景,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面对生活时,我们的内心就是观察这个世界的俯瞰式力量,突破了心的束缚,也就做到了冷静地面对人生境遇。
二.陌生化写作
《风景》的叙事魅力还体现在“陌生化”的写作方式,方方在作品中集中表现“死亡”与“异化”。面对残酷的生活与险恶的生存竞争,《风景》中的主要人物选择了两条路:“死亡”,梦想破碎后的选择;“异化”,挣脱残酷人生的另类死亡之路,虽然躯体仍活着,但内心已失去人生的温度。
方方在《风景》中突出表现了典型的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力,二哥和七哥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死亡”,一个“异化”。《风景》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新写实小说往往把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推衍为创造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把强词的重心移到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上、移列了人的特定境遇上’以达到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再现。”[4]作者通过陌生化的叙述方式,让小说人物在真实现实环境中被死亡、被异化,进而引起读者的思考,为何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环境能造就成令我们陌生的人生轨迹。
“死亡”的代表人物是“我”的二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脱离棚户区的生活习惯,开始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只有知识与爱情才能够让生命存在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对杨朗的爱,紧紧围绕着杨朗最初给他的印象“不是死,是爱”。他为爱自杀,不愿意接受杨朗廉价的敷衍之爱,他选择死亡,选择死后的孤独之爱,也就完成了他一生所执念的“不是死,是爱”。方方通过陌生化的叙述方式,展现出一件件死亡的事件,进而突出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别样的人生。像二哥这样的人物,梦想已经破碎了,就不愿痛苦的活着,甚至连一晚都熬不过去。既然生存的意义已经被剥夺,还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二哥呈现出来的悲剧人生。然而,谈到“悲剧”,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是惟一受到父亲喜欢的孩子,是那个暴力家庭中温馨和希望的象征,但却根本没有来得及参与现实中的任何事情,便悄然离去。“我”的早夭,似乎可以被看作是美好的消逝,也是一种人生悲剧。
“异化”的代表人物是“我”的七哥。他善于隐忍能为了人生利益不择手段,他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七哥的童年是在漆黑的床底下度过的,听着火车与轨道相碰的轰隆声。“够够”是一位带给他温暖和希望的女性小伙伴,她的笑容也是七哥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然而就这样一位美丽女孩却被火车轧死了,这在七哥本就痛苦的童年中压上了一道沉重的心理阴影,痛苦、灰色、冷漠。
这个棚户家庭是七哥人生痛苦的发源地,他的生命无人关心,父母亲打骂、哥哥姐姐欺负挖苦,小小年纪就上街上捡菜叶,去黑泥塘挖藕。二哥是唯一能带给他些许温暖亲情的人,恰是如此温暖的人却为了爱情选择自杀,二哥的“死亡”加速了他的“异化”,他开始为了摆脱棚户家庭而向上爬,为了改变人生道路走上了一条条“捷径”。但七哥的“异化”道路走到最后却是悲剧式的、无幸福感的人生,是一个外表光鲜亮丽,内心空虚无爱的孤独之旅。正如文中所写的“悲剧总比没有剧好……有魔鬼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细读作品,我们或许会问,方方为什么不把七哥塑造成一位在平凡生活中愈挫愈勇、正面积极的形象,为什么让七哥的人生充满了对现实的妥协无奈,充满了争名逐利的野心?其实对于棚户家庭来说,生活本就是残酷的,七哥的人生最终进入“异化”的轨道,或许是更能引人深思,把现实撕裂开,不完美的终结往往能惊醒人类。
三.隐含作者与叙事者
《风景》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也是作品的一大亮点,探讨隐含作者能深层地了解到方方对人生境遇所做出的哲理性思辨。
隐含作者往往表现作家冷静客观的人生态度,同时又通过作品叙述者的口吻来表现作家的道德立场、人生观点。在《风景》中,方方表现出对居住在棚户区的下层人民生活的深深同情,同时通过对一家七兄弟生活变迁的描写,展现了生活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写出了不同的人生风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隐含作者是更真实的“深层的我”。同样,方方在描写“死亡”和“异化”的人生时,深层地显露出她的人生信条和道德准则。方方淡化诗意性写作而强调真实,把生命中的悲剧色彩放置在人生艰难卑微的生活琐碎中;方方关注社会化的人生境遇,关注底层人生中最常见的已消磨掉的现实悲剧。
在叙述文本中,隐含作者往往借助叙述者的口吻,表现出他对故事人物的基本看法,隐含作者也往往冷静站在事故背后,不作评判,让读者在叙述者和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现隐含作者的基本立场。
作为《风景》中的叙述者,“我”所有的思维都是外界引发的,“我”的思维背后透露出隐含作者对人生风景的领悟,如七哥所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途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绿肥绿肥的呢?”[5]“我”作为叙述者,不参与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却在整个文本中无所不在,“我”洞悉一切,见证了兄长们人生境遇中的每一个风景。
隐含作者通过“我”的叙述视角,塑造出一底层人生的风景,这里有文明与愚昧、有积极进取、有人生肆意,也有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隐含作者让“我”在现实人生中看到时代对于原始家庭的冲击与改造。三哥把“我”带走了,“我”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风景》中的人生状态都是“我”眼中的风景。隐含作者令读者更深层地体会方方在文章背呈现出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向读者传达出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即生命虽然短暂,而人生的风景却未曾枯烦。作为生命个体,我们要想清醒地走过宝贵的人生,必须具备一个冷静的心态,进而去观察这个变换无穷的人生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