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里风情
刘鹏艳
桥上生明月
一座桥,连着我家和对岸的娘家。河是护城河,远远地溯上去,时间的那头,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以河为界,这边是城里人,那边是乡下人。到我结婚的时候,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摊大饼似的摊到了乡下的乡下。这时候河对岸的房子也很值钱了,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父母怕我远嫁,执意让先生把婚房买在娘家附近,正巧对岸几座悬剑似的高楼拔地而起,沿着马路排出一种睥睨老城区的气派,于是就下了定。在父母看来,这座桥造得好,挺有仪式感地搭在具有某种人生隐喻的楚河汉界上,即使闺女嫁出去,抬抬脚,也就回家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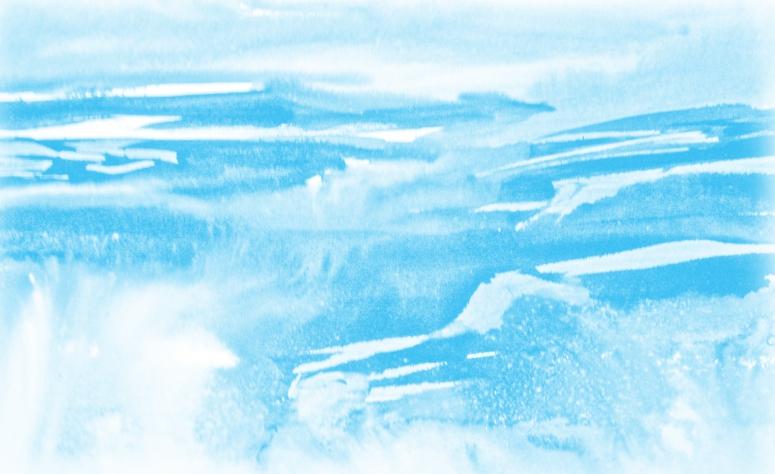
这座桥有年头,往上溯,不同的年代叫过各种名儿,延安路桥,芜湖路桥,大洋桥,通津桥……不过让此桥闻名遐迩的,还是“孝肃”二字——为纪念宋朝名臣包孝肃公,这座横跨合肥南淝河近千年的桥梁于1990年复名为孝肃桥,站在桥上,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扑面而来,“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孝于人民,肃于律己”,一座桥见证了淝河两岸的巨大变迁,但始终不变的,是包公故里老合肥人的“孝肃”精神。
古庐州水多,桥自然也多,但一座桥和一位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唯此桥得天独厚。据史料记载,孝肃桥始建于宋代,1309年重修,1496年复修,清康熙六年(1667)和道光四年(1824)又两度复修,光绪十三年(1887)再度续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达到六级航道标准的桥梁,是历经战乱和洪水后反复重建和改建的孝肃桥。
孝肃桥曾入选合肥“十佳老地名”,提起它,合肥人总是会感到无比亲切,而于我,这座桥更添了一重温馨的味道,因为,抬抬脚,就回家了。
我家在桥东,娘家在桥西。我若回娘家,往往是迎着夕照;父母若来我家,多是与朝阳打个照面。为什么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邂逅同一颗太阳呢?“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把女儿嫁出去的那天,娘家多半是这样悲戚忧伤的场面,好在一座桥飞架东西,使父母的牵挂得到某种具象化的安慰,他们从此把对女儿的照顾,扩容到了女儿的新家。有了宝宝之后,父母总是每天一大早就从桥上过来,比女儿、女婿上班打卡还要准时;而我从桥上走过,西去娘家的时候,必是暮色四合了,父母已经做好一桌可口的饭菜。这样日子细碎的烟火人家,在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代中国家庭里,真是适宜极了。父母一辈子都在为一个孩子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似乎从未想过让自己光荣“退休”,或者更新换代地被别人挤“下岗”,辛苦是辛苦了些,可还有比这更甜蜜的事业吗?
我们一家在桥上走过了许多日升月落的日子,渐渐地,孩子也会走路了。我会站在桥上指给孩子看:西南面是万达广场,广场后面是姥姥家;西北边儿呢,是威斯汀酒店,酒店再往西走,就是包河公园;东南角儿,是咱们家,后边是和平广场;往东北,那片儿是坝上街,老合肥的东大门……咱们站的这座桥哇,叫孝肃桥,孝顺的“孝”,严肃的“肃”。我拉着他的小手,摸摸桥头赵朴初先生的题字,“孝肃”二字隐在朦胧的月色里,虽风尘仆仆,却熠熠生辉。
月在桥上,桥在水中央。天空是墨蓝色的,河水也成了一条泛着鳞光的墨蓝丝带。
“妈妈,月亮。”他仰头对我说,葱段儿似的小手指,勾了勾那半轮明月。
“被吃了半边儿的月亮。”我和着他清脆的童声。
“刚才还没呢。”他很惊讶。四周高楼林立,繁华的商圈霓虹飞彩,那些高大的楼宇把天空切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我牵着他从高楼的缝隙里走过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月亮害羞的身影。
“刚才,是谁躲在楼后头吃月亮吧。”我笑着说。
城市的发展太快了,快得让我们很难在市中心找到一片抬头就能看见月亮的空间,这座桥,是个例外。我要感谢这座桥的宽广,在拥挤的城市中拉开一条河的距离,让孩子快乐地走来走去——走到桥上,抬起头,就可以看见害羞的月亮。
月在桥上,桥在水中央。这边风景独好,美得像是一部童话。
小巷的前世今生
这条巷子挺年轻的,按流行的说法儿,得算是90后。在巷子口住了几十年的张新春老人指着这条巷子告诉我,九十年代以前,根本没得路,这后面就是高埂代。那么前面呢?前面是名噪一时的“二码头”。1979年就在码头上扛活儿的张新春,还记得当年千帆竞渡、人流如织的繁忙景象。在他看来,没有“二码头”,就没有航运巷,这条不足五百米的巷子虽然年轻,却沾着老码头的水汽儿,每一盏水雾氤氲的路灯下都有故事。他和八十六岁的张定国在巷子口聊上了,两位老张都是海事局的老职工,忆起峥嵘岁月,话匣子怎么也合不上。
“对面是货運码头,往北是客运码头;巷子这边是仓库,那边是候船室……”说起当年南淝河畔漕运的堂皇气象,两位老张都熟,都不甘落后。他们是看着这条巷子“长”起来的——起初零落的几间茅草屋,三三两两垛在码头附近,都是装卸工人图方便,临时搭起来的容身之所;渐渐地有了规模,公家开始建房,作为福利分给职工;然后地就热起来了,修上了路,宜商宜居,自成社区……如今的航运巷被列入市政“慢行系统完善工程”,也就是说,往后再有人走在这条巷子里,脚步会慢下来,心会静下来,品咂出水城庐州的余韵,“淝水之滨,淮右襟喉”的味道。
这是一条有文化的巷子,东起巢湖路上的老码头,西接南北一号主动脉马鞍山路,“携水运之便,揽文史之重”。街道文化站的许瑶拿出了航运巷的规划图,指着即将呈现的广场景观墙,向我展示这项耗资百余万的工程,如何打造一条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船形座椅、塔灯路牌、舵状浮雕、橹、锚、帆樯……当一条巷子遇上老码头,光阴里写满了舟楫的传奇。
最早可能要追溯到隋唐时期,周遭各县漕粮大都通过合肥由水路运抵京师。唐代以降,水运日益发达,南来北往的粮油棉麻、家禽家畜,皆经由合肥水运集散,故此地码头众多。不过一直到1953年之前,这儿还是个自然形成的土码头,极潦草地用两个土墩儿隔开,再延伸到几个泊口。即便是这样,巢湖路上的“二码头”也已经名声在外。这一年的年底,市航运管理部门扩建码头,一个二十五米直立式货运码头和一个十七米斜坡拾级式客运码头应运而生。与此相配套,市里成立了一支专业的装卸队伍。张新春的父亲就是巢湖路码头的第一代装卸工。当时还没有吊车,码头工人要搬货运物,完全凭借人力。一袋货物重逾百十公斤,装卸工人得背着它走上三十多级台阶上岸,再运往仓库。一船货六百吨,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要背上整整两天。到了张新春这一代,新添了变幅式起重机,在码头上扛活儿可轻省多了。不过他没有父亲那么幸运,能在熟悉的“二码头”热火朝天地干上一辈子——不仅仅是因为后来居上的全机械化操作代替了人力装卸,还因为市政府为治理污染严重的南淝河,于上世纪末禁止上游客货运通航,使昔日舳舻千里的航道变成了一道寂寥的河湾。码头渐渐长起了荒草,曾经帆樯如云的显赫与繁华如秋后的叶,一片片凋谢在光阴里,终于婉约地成为一具沧桑的标本。
张新春说到这里的时候,唏嘘不已。已经五月了,巷子口的风浩荡起来,他没怎么把许瑶提到的“水运文化主题街巷”的规划听进耳朵,毕竟年纪大了,他的青春和回忆都留在世纪的那一头。相比之下,年轻的许瑶对未来的热情更能让航运巷借历史的包浆重新焕发出光彩,她和崭新的合肥港一样,因为历史赋予的新的时代责任,更加兼容并蓄,通江达海。目前,作为全国28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皖中最大的水路货运集散地,合肥港已经成为集装卸、堆存、仓储和中转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港口。虽然承载了无数装卸工记忆的巢湖路码头被关停,但合肥的水运事业并没有停滞不前,相反,它以巨大的吞吐量显示出新世纪航运里程的非凡活力。淝水南去,风华依旧,而在一条叫航运的巷子里,那些关于水城庐州的老人、老故事、老物件儿,因为被注入了年轻的活力,亦将在不老的时光里栩栩如生。
一杯舒茶可清心
舒城离合肥不远,五十公里,若驾车,一个小时便到了。但很少有机会专门花上一个小时,去五十公里外的舒城。因为若是为了摆脱“眼前的苟且”,追寻“诗和远方”的缘故,我们往往又会走得更远一些。这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说,多少也算是一场奢侈的旅行,我们不愿把“去远方”的态度圈禁在五十公里的范围内。所以虽离得不远,迄今为止,我与舒城也还是第二次见面。
距上次见面,总有三五年了,我不记得具体的情节,如果每一次和一座城的相遇都算是一个故事的话,那次的故事情节总归是很潦草的。或许可以借用一句德国谚语来概括我们的初识——“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这句话,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引用过,这使它带有某种文学的印记。所以,对钟情于文学的我们来说,似乎第二次相遇才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舒城在时间的纵轴上远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西周武王克纣后,封功臣偃姓子爵于此,立为舒国,后分立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史称“群舒”。舒城县,正是泱泱古群舒的一部分。省略掉汉唐明清的气象,把历史的镜头拉近些,这里是红二十八军、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也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指挥机关的驻扎地,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到皖中、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挥中心,舒城在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由于近年来从事长篇纪实文学《万物慈悲——中国乡土理想纪事》的采创工作,我在鄂豫皖的群山遄水之间往返多次,却与舒城并无太多的交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次舒城之行,无疑是对创作的有益补充。不过那将是另一部长篇叙事将要完成的浩大工程,在这篇小文中,我只想谈谈春天,谈谈一杯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们浮躁之心的荡涤。
第二次和舒城相遇,是在一个草长鹰飞的春日。这个季节赋予生命很多想象,天然地具有饱满的构图和多汁的色彩。那个叫舒茶的小镇尤其让人耳目一新。远远地,层层叠叠的茶田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地方,梯式的种植带像是一条条绿色的丝绦,依次围绕着正在苏醒的山体。红日照在山坡上,无边的绿意生机勃勃,仿佛六十年前喷薄的模样。这里是舒城的南大门,绵延着大别山的东麓余脉,当年,由于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作出了“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重要指示,舒茶的名字因此响遍全国。
《红日照舒茶》,是1971年小学语文课本上的必读篇目,不知那时读小学的整整一代人,是否还记得舒茶人民在荒坡野岭上开辟的神话。如果没有那些年开山凿石的艰辛,舒茶镇不会是现在兰麝芬芳的模样,梯田和水库,成就了舒茶的万亩优质茶园。当年伟人挥手遥指的青冈岭,如今已经是道道碧色的云梯,于白云生处映山红遍,成为舒茶独树一帜的地标。
站在九一六茶园的梯田上,及目是一片开阔的丰饶,远处,高楼林立;近处,茶香醉人。对于舒茶人来说,“茶园”与“九一六”,是一对分不开的历史词汇——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发出多多开辟茶园的伟大号召,舒茶从此名扬四方。作为曾经具有标本意义的人民公社,舒茶的“青冈云梯”是一个鲜明的红色记忆;而作为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现代旅游景区,“青冈云梯”则俨然成为绿色发展的一例活标本。驰骋在青山绿水间的想象,让我激动不已,一甲子弹指一挥间,我们也许错过了某些重要的历史现场,却与历史的发展迎头相遇。
在九一六茶场的休息室里,我与一杯清茶相谈甚欢。
舒茶,兰花茶,外形芽叶相连似兰草,冲泡后如兰花开放,兰香四溢。一杯汤色清亮的小兰花,能勾起舌尖和记忆的回甘。
歷史已然成为过往,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某些东西,却如茶之甘香,值得慢慢品味。在绕鼻的兰香中,春光正好,而我相信,一颗初心,尚且年青。
多年从事叙事学研究的我不善抒情,此刻却诗兴大发。也许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但我愿意手握一杯清茶,完成一场诗意的表达:
清明前后
采茶的姑娘开满了山坡
那本是最古老的语言
如今却要经由某种仪式
说出现代化的礼节
我独爱那姑娘
眼里盛放露珠的姑娘
穿过斑驳的光阴
发梢撩起,便流连了三千年的芳华
如一朵幽蓝的兰
由一杯茶去解语
是不够丰赡的,尽管
量杯精准无误
载浮载沉的叶片
早已说尽了从春到秋的童话
——以舒城县开展精准扶贫为例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