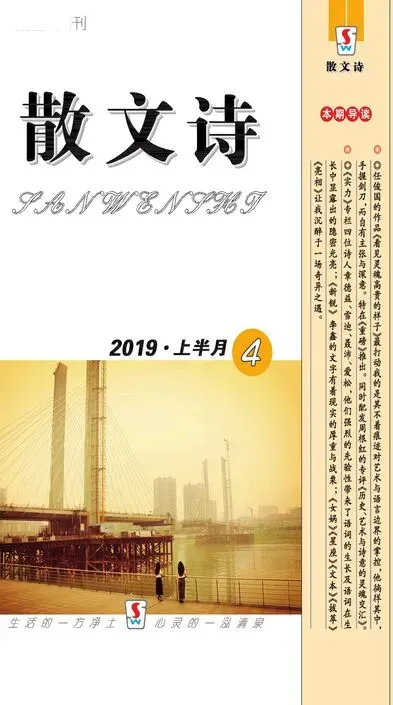迟疑的停顿
贵州◎谢景高
言西 图
藤 椅
一屁股坐下,四条腿腾起岁月的尘埃。
双手抱臂。二郎腿。轻咳,以清亮嗓子;闭目,以确保心跳和呼吸刚好对上时光的针秒,嘀嗒,嘀嗒,嘀嗒——
一粒文字挣脱时间的缰绳,粗犷的呼吸渐渐燃起胸中马匹。四蹄生风,自远古的地平线踏蹄而来,瞬间穿过身体,像剑,穿过一纸透明的诗句。
侧身,像侧过阴影的匹马西风!
你提笔,江山依旧,写一道残阳如血!
皱 纹
无须皱眉,额头早已凹陷泥土的厚重与深沉。
沟壑间,锄头开始舞动,抵达泥土的内核。一颗乳牙洁白,吮吸炊烟和泪水,饮遍根系疯长的月光。
以月光之鞭放牧所有的风声、水声和鸟声,一脸平静。
有谁听见骨质褶皱的清脆?
一路咯吱,咯吱,咯吱……
骨 头
把骨头轻轻放下,屏住呼吸,聆听体内宁静的喧嚣。
从膝关节开始,叙写一节骨头的阴晴雨湿和步法里隐隐的疼痛。
一些记忆蠢蠢欲动,吐出发霉的新绿;一些私语推杯换盏,溅落碎片的月光;一些剑气锋芒如雪,折射坚硬的骨质之光。
云墨深处,风呼呼兮乍起,把时辰推向指尖。
鸣笛!击鼓!兵马萧萧!
取一根肋骨直插苍穹,击碎电闪和雷鸣!
停 顿
驻足。冥想。一个哈欠的瞬间,以五尺慵懒之躯掐住时间的脖子。
调匀呼吸,心跳拱起皮肤连绵的山峦,久违的太阳从一颗草尖的露珠慢慢升起。一只蚂蚁驮着体内细长的身影,像高举一杆庄严的胜利之旗,斜插于一枚石子的荒凉。
时光正好,落叶的姿势静静嵌入一幅水墨,盘腿而坐,疯长螺旋般上升下沉的哲思。
一切正在燃烧,一切又正在熄灭!
不必怀疑是谁虚度了时光,还是时光正虚度了谁!
隐隐停顿间,不用担心谁的脖子被一根粗犷之绳勒出了血。
磨
一些静止的时光,流水不止。症结里漫长的流淌,充斥不休的狗吠鸡鸣。
缺钙的相思,牙齿依次松软、脱落。咀嚼之胃,屋瓦的影子阴暗潮湿,拄杖炊烟,摇摇撞撞斜过雨季和风向。
一转紧随一转,一圈盖过一圈。
直到把骨质的脆和泪眼的阴晴圆缺细细碾碎。
直到最后的风吹远。
凿
镜像大于粗糙,叙述顽固不化的石头。
锤已高举,指为凿,从一根细小的脉管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凌乱的碎片汇聚成一只乌鸦,叼走宿命的黑和死亡。
叮叮叮,叮叮叮……
脚趾,肋骨,眼睛,眉头……一寸寸从身体里站将起来,精神抖擞,血色模糊。
你也站起来,目睹一道神性的闪光。
微 醉
执酒,饮一杯树影婆娑的微醉。
听骨子里的虫鸣来回拉锯一根木头,锯除草木一秋的伤悲。
醒与醉都误读了眼泪的光环,醉或醒都侵蚀着肉体的真空。
微醉,时光正好。
持剑,刺破一纸烟墨。
低头,俯身——微醉,有倾其一生也收拾不完的千里江山,万里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