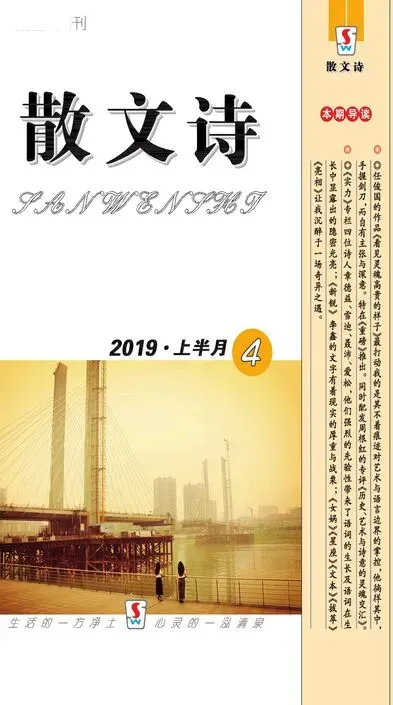悲怆
云南◎爱 松
乐 队
大乐队的演奏,似乎想要把一切带往过去。音符在记忆中,慢慢铺展。旋律中有一股,直抵骨髓的强大平和之力。
老屋好久没有下雨了。我的妹妹,附在家堂贮贝器的图腾上。她还在生长,也许她渴望的并不是水,而是降落时,音符一片片律动的力量。她需要这种力量,她等待着旋律中,这股力量灌进她的身体。她努力想挣脱出来,得借助这股力量,成为这个家族,真正不可或缺的一员,不是在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
旋律还是将妹妹,带到了过往。莽莽森林,构建着乐曲这个章节的骨架;涓涓水流,穿梭在旋律隆高的山丘之间。古滇城邦的宫殿,在乐曲中隐现,大泽晃荡着大乐队,忘情的合奏……我看到了我的妹妹,她已经退却了,被音符现代性包裹已久的束缚,站立在干栏式宫殿主殿巨大的青铜柱下。她为我看得到她真正的面容而兴奋异常。
旋律回荡着古滇王国,又一个灿烂的黄昏。我却一直没有能够看到自己,也没能见着我父亲,以及这个家族,除了妹妹之外的,哪怕任何一个影子。
我突然对乐曲这般平静的行进,有了警觉。我的妹妹对于我突然而生的警惕,也产生了某种不经意的防备。
旋律响起了细微的、额外被什么拉动的杂音,极其细碎的声响,悄悄跟随着大乐队演奏。我的妹妹,朝着并不存在的我,走了过来。我并不想让她看见,我在过去的不存在。就像她不愿意我,一直死死盯着现代晋虚城南玄村,老屋家堂上,她缠绕着的贮贝器一样。我试图在音符中,寻找一个出口,或者躲避之处。我的妹妹感应得到这些,她跟随着旋律,加快了前来的速度。
我变得惊慌失措,我害怕在旋律中,丧失我和家族存在的依据和可能。我得想办法证明,证明古老旋律中,蕴含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必需保留的古老根脉。
我得告诉我的妹妹,我来自哪里?那里的我,想在旋律承载的逝去的记忆中,寻找和证明着什么。
乐曲颠对的换位,来自大乐队高明的演奏技巧。
我的妹妹跟随着节拍,不失时机地在间隙处,停了下来。她已经走到我的跟前。旋律被某种力量放大的效果,和现在的我的妹妹,站在并不存在的我的面前,多么相似。当我的耳朵,被巨大的分贝灌注冲击时,我发现了,自己的微茫。不仅如此,当我觉得旋律泄露了我(只是一个意念中的位置)的存在,我又无法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就在那里时,妹妹伸出的手,已经稳稳抓住,慌忙逃窜的音符中,最末一个虚弱的尾音。
我感觉到自己,被套上了厚厚一层音符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在远古的岁月中扭动。就像与我父亲一把抓住的那条黑亮之蛇,在同一个地点的不同时代,被大乐队齐声奏响。
火 焰
旋律从我的妹妹的蜕变开始,加快了行进速度。像一团激烈燃烧的火焰,在她的舌尖上,喷涌打转。这条分叉的红信子,试图将散开的多声部合奏,拧为一体。我的妹妹需要奋力一搏,挣脱青铜贮贝上,太阳纹的困缚。但是,她首先得寻找到它的漏洞。在南玄村老屋与鑫鑫冷库的地下隐秘通道中,她循着大乐队的演奏,追逐着黑暗深处另一个自己。
那里会有一个怎样的发音方式呢?乐曲中,蠕动着的,只是我妹妹爬行时的窸窣响动。鑫鑫冷库横亘在妹妹前行的途中,它同时在乐曲中布下了被冰冻着的谜团。一些似是而非的虚拟音符,冲撞着我的妹妹。急剧下坠的温度,阻碍了大乐队向我妹妹发出的呼唤。休眠的危险,一步步朝我的妹妹逼近。
她黑亮的身体,泛起了白霜似的斑点。我得帮助,这个让我疑问重重的妹妹;我得帮助,这个家族最后的异存者;我得帮助,我未来在乐曲中,被奏响的轮回与困苦。我拿起了老屋家堂上的贮贝器,那些金色的太阳纹,在青幽的基座上游动。我仔细辨认,我的妹妹却在旋律中,更快地飞离了我的视线。
音符并没有按照我预想的顺序,被鑫鑫冷库劫持。这座冒着白烟似的冰冷墓葬,燃烧着另一种白色火焰。它们,把我妹妹团团围困。旋律在夹击中,惊慌失措。它左突右转、前冲后闪,留下一串串略带战栗的音列。
它们护卫着我的妹妹,尽管其中的一些,被那些白色的烟火,挟裹进了这个无底的墓葬。我的妹妹,依然保持住了作为贮贝器上,一个家族被封存图腾的矜持和尊严。
旋律中响起宛如钟鸣般的敲击。这些夹杂念诵的低沉宏大之声,加入到了这场混战般的博弈中;另一些如信徒祈祷的激越声,也随之在挣扎着的旋律声中泛起;更多像合唱的多声部赞颂之音,也跟随旋律的交叉挫斗,逐渐明朗起来。三股声线,在鑫鑫冷库墓葬式寒彻透骨的围拢下,合力抵抗。
我妹妹身上黑亮的外皮,伴随着音符之间的争战,一层层剥落。
我听到乐曲深处,对应传来一声遥遥的呼喊。我知道,幽深地底,也有另一条和我妹妹一模一样的蛇,正在蜕皮。每蜕一层,这场壮烈斗争下的交响乐曲,便增加一次被燃烧掉的危险,而老屋家堂上的贮贝器,也不可避免地被时间抽取掉,那极具象征性的家族的至高图腾。
我的妹妹,是否和我一样,担忧着这些暂时被旋律遗忘掉的演奏动作呢?
我的妹妹终于看到了我,在乐曲累加的某个高度的旋律组合上,她见到了这个家族的记录和抒写者。只可惜,我仍然没能看清楚,她丧失作为贮贝器上一个图腾,或者梦幻中一条蛇之后,真实的容貌。
我的父亲(也许是音符幻化而成的模样)又一次适可而止,带走了她。我当然知道,父亲将把我的妹妹带往哪里,但我不能说,就像音符中,蜕变的某些乐句一样,一旦被点破,又将回到没有被奏响之前的状态。这是我更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即使我不得不为我妹妹的命运,再次感觉到了,莫名的焦虑和虚妄的担忧。
召 唤
混杂的音调,掩饰不住旋律在晋虚城大地继续寻找着的缓慢意味。南玄村老屋,作为我的妹妹以及整个家族消失和沦陷前最后的一站,在乐曲中,躲避着大乐队的触及。它需要保持住沉默,只有足够的沉默,将悲伤的涵义延伸,我的妹妹才能够藏身于此,黑亮的颜色,扩大了乐曲行进的层次。我的妹妹消失之后,青铜贮贝器上的图腾,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旋律,又回到了深沉的哀恸之中。只有一道又一道,硬朗而明亮的管弦乐音组,涌了上来,这是我所陌生的演奏,当然,更像是召唤我妹妹的凝重之音。我知道,它们并不是发自大乐队,而是地底,深埋着的青铜和图腾。
乐曲的交错,引发了黑亮的音调,朝着背离大乐队的方向叛逃。它们所要追寻的相反意义,就是白。
我的妹妹,是否妥协于消亡之后,与自己曾经作为一条蛇,进行着隔离?我不得而知。青铜贮贝器上,一切照旧的太阳纹,在两种曲调的碰撞下被激活。它们顺着青铜致密的肌理,爬了进去。旋律,再一次被图腾的重量压低。我的妹妹,看到了它们的到来,她为自己身上褪去的黑亮,感到不安。那层束缚了她多年的皮,成为了追赶着她,最为卖力的音符。我的妹妹没有找到自己。她一直伴随着旋律,为一个无所安放的新躯体的罪孽与忏悔祈祷。也为这个被诅咒家族,摒弃乐曲的现代记忆感到忧虑。这和她被我父亲带走,安放的地方息息相关。那是旋律古老遗风的一部分,当然,也仍然属于青铜贮贝器肌理的,某个方位和方向。
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古滇冶炼术熔铸和建造着,这个白色迷宫。
旋律出现了庄重肃穆之音。
我的妹妹在乐曲中寄存着的找寻过的记忆再次闪现:晋虚城三关巷礼拜寺里,阿訇带领教徒们诵经而翻动空气的声音;晋虚城映山塘之上,盘龙寺里方丈能寿亲自敲击木鱼念经而拍击水流的声音;晋虚城龙翔路基督教堂内,众教徒跟随唱诗班,放声歌唱赞美诗而搅动时间的声音……我的妹妹,在这些流落世俗的神圣声音中,努力辨听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音符。
她以为,只要找到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发音,便能寻回未曾蜕变的黑亮色。那才是这个家族,唯一的颜色和标示。无论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是家族接连不幸死去的亲人,以及并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自己,都在妹妹的找寻中,成为音符泛白的一部分。
黑色的旋律和白色的旋律,第一次清晰地分裂着大乐队的演奏。家族的足迹,在妹妹找寻自己的过程中,重新又一一走过老屋。我的妹妹,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在每一个哀恸沉思之音上,借助青铜贮贝器闪亮的图腾,再一次为家族成员重新命名。
这个唯一的,因独立于家族现代化湮灭而消失的人,我的妹妹,仍然以谜梦中蛇的方式,继续着作为人对于这座现代城镇的审视和预言。她在乐曲落下的最后一个音符中,弓跃而起,发出了一声有着青铜质地,但并不存在于时间世界的音符的黑色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