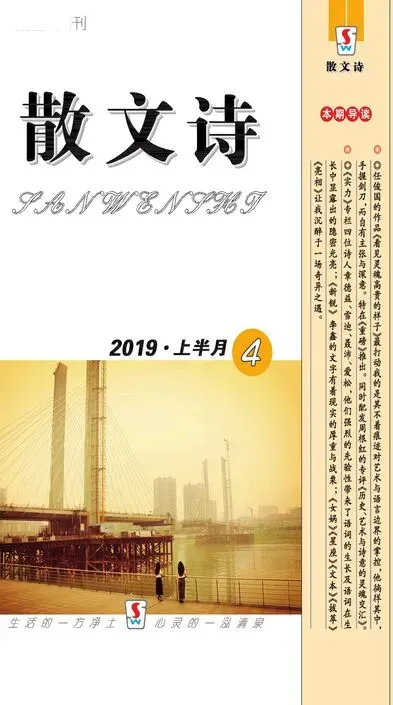章德益散文诗
上海◎章德益
钟道生 图
动物园物语
一个人是一座完整的动物园。头脑是笼子。思想是飞禽。欲望是隐形潜伏的兽。人性是动物园四周环绕的假山、喷泉、锈铁围栏与装饰有广告牌的塑料花园。四周经过的人都是动物园爱好者,他们每天穿越我生命的围栏参观我的存在与欲望。身体像一道低矮围墙沿我影子的地势在内心地貌中蜿蜒,环护着一个人小小的隐私与自我。我孤独的影子是动物园里最年长的管理员,每天无日无夜地巡视园区,还必须在月升时刻用一把钥匙把所有猛兽锁牢在我的七情六欲与喜怒哀乐里,防止人性出逃而成兽性,或者兽性出逃而伪装成人性。给动物送食料的高大货车每夜穿越我内心的后门进入动物园 (那里有我的一张面具看门)。那时,送货的司机会听见猴山上一声又一声模拟人类箴言的叫声。那是我新写的诗句。
城市夜曲
夜。众多眼睛划着手机的舢板在城市大街的五光十色里漂流。
从面膜里升起的苍白面孔,散发着水母与海蜇的淡淡腥味。
美人鱼一尾一尾从口红与胭脂盒里游出来,登陆成脸上的嘴唇,或者搁浅在柜台与酒杯、钱包之间,吐着鱼族的泡沫。
领带垂钓红唇。眼神波诡浪谲。口袋是漩涡,手势是漩涡,人心也是漩涡。漩涡里漂流的咖啡杯与烟灰缸都是沉船。霓虹灯把漩涡上的钢筋水泥都装饰成空中的珊瑚礁。
月亮在垂钓诗人。但它只钓起一件老式风衣。风衣口袋里探头出来的宠物狗咆哮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钟摆对着暗号。
春天随想
毕竟是春天呵。连昨晚留在我家阳台栅栏上那个翻墙而入的贼人的三只指纹,也嫩绿成三片美丽的树叶了!
当我把它们摘下交给警察时,警察们手握这三片临风摇曳、幽幽飘香的滴露指纹,啧啧称奇!竟也嗅闻着,欣赏着,惊诧于春气之浓烈。
此案告破时,已届秋季。
想那被抓获的贼人,已烂熟成一颗人类的果实了。
街头买菜记
出外买菜,与人讨价还价。也许因为久久谈不拢吧,那菜贩子一怒之下,就把我一把拎起,塞进他手心那只电子计算器里。他恨恨地揿着那计算器上各个加减乘除键与数字键计算着我。我于是在那计算器里一会儿变成白菜价,一会儿变成番茄价,一会儿变成冬瓜价,一会儿变成洋葱价,一会儿变成老韭菜价,一会儿变成蘑菇价。呵呵,一会儿……一会儿……哦,我眼看自己快要变成臭豆腐价、臭鱼价、烂虾价,甚至猪蹄价了。我急得在那计算器里边挣扎边喊道:“呵呵,我买了,我买了,我不讨价还价了……”于是,那菜贩子大度地松开手,把我从计算器里假释了出来。我于是提着满满一篮用自己的挣扎之姿标出生命价码买得的菜蔬回家。一回家,我就变成了一棵最便宜的大白菜,被我太太种在了床单上。
显影液
朝木乃伊身上滴一滴显影液就显现出一条风干的尼罗河、一座金字塔、一队骆驼与一棵飞翔的棕榈树。朝死者的影子滴一滴显影液就显现出一蓬胡子、一个名字、一只手的骨骼、一群细菌与一颗大理石的心脏。朝脑子里滴一滴显影液就显影出一轮太阳、一艘船、一片沙漠、一座迷宫与一只遍身长满苔藓的蜥蜴。朝一粒骨灰里滴一滴显影液就显现出一张婴儿脸、一个笑容、一滴精液、一只乳房、一朵火焰、一只子宫的剖面图。朝一条干裂的河床里滴一滴显影液,岩石里就游满了鲜活的鱼,从金鱼到鲸鱼。空灵的水在空中舞蹈,但不留下水渍。
而我朝我的灵魂滴一滴显影液,却什么也没有。空白。只有一尾透明的咸鱼游在一块盐晶的水晶墓中。远方是无边燃烧的腐烂的海洋与地平线。
钟表店
岁月能修吗?记忆能修吗?滴滴答答的时间之逝水能修吗?你看,闹钟已被拆卸,钟罩已被摘去。钟盖已被卸下。十二个时辰在空空钟面上冰冷窒息,胡乱排列。时针枯萎。秒针逃亡。分针骨折。钟摆缠着绷带,一瘸一瘸。钟锤口吃,支支吾吾地胡乱报告着不知哪个世纪的钟点。一大堆钟表发条如造物主消化时间与人类的小肚鸡肠,狼藉一地。是闹钟吗?呵,那曾经振聋发聩的满屋吆喝呢?那曾经满世界导演历史悲喜剧的精准报时呢?时间的庞大阴影里枯坐着钟表店老板的瘦小背影。从背后看,像上帝。从前面看,是魔鬼。
假肢颂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假肢生活,或者说,假肢寄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与假肢互为连体。
有时在寂静里,我能听见我体内假肢的呼吸,咳嗽与自语。混浊而沉重的声音。那声音缓缓弥溢开来,化作我生命之节奏与生存之补充。
我们制造了假肢。假肢也制造了我们。沿着假肢的道路,我们不断完善着自己残疾的方式与病态的存在,以使我们的残疾有一个神性的轮廓与人格化的定义。
有时,我们也感受到自己在反抗假肢,或者说假装在反抗假肢。但我们必败。最好的选择必是妥协,与假肢妥协,与残疾妥协,与这病残的世界妥协。
因为我们无法拒绝,必须如此。假肢最终战胜真性情与真灵魂是必然的。
假肢内部的血液流动声是我们的吟诵与歌唱。啊,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吟诵与歌唱!从更高层次上来说,这歌唱是必须的祈祷词,是我们生理习性与精神惯性的祈祷词。我们必须更像假肢或者让假肢更像我们。这是假肢与人合二为一的进化之路。
哦,假肢入侵了我们。假肢同化着这个世界。假肢征服着人类的精神史与文明史。我们与之共谋。因为我们有一个假肢的神与一个假肢的上帝,有一个假肢的天堂与一个假肢的地狱。
电灯泡
电灯泡是黑暗中的玻璃子宫。
火焰在里面等待分娩。
我知道,那是一次人工授精后完成的杰作。光是其中身份不明的私生子。如果对光进行DNA测试,就将发现所有的蜡烛都曾是它的母亲,所有的油灯都曾是它的父亲,所有的黑暗都曾是它的保姆,所有的X光都曾是它的教父!
把电灯泡像婴儿一般小心翼翼放进灯罩的摇床里,给它喂奶。
文字与血就是奶!电灯泡突然真的像婴儿一般啼哭了起来。
那不是电灯泡在啼哭,是我屋里一只早已定时的闹钟突然苏醒了过来,准点尖叫了起来!
屋内突然一片……盲去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