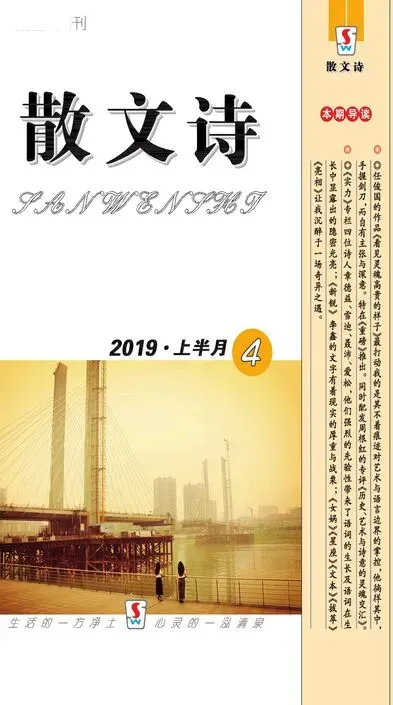历史、艺术与诗意的灵魂交汇
◎周根红
对历史的诗意书写,对艺术作品的诗意发掘,是散文诗(诗歌)写作中最难把握、也最难突破的题材。曾几何时,这类题材却大量泛滥于散文诗(诗歌)作品之中。其问题也较为普遍。它们往往容易流于对历史事件的“情景再现”,或对原文本的“语言翻译”,因此,很多类似的作品大多是一次写作的旅游观光和文本导读。
任俊国的这组散文诗,迎难而上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具有较高难度和写作风险的题材,着实表现出诗人的勇气和信心。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他的这组散文诗虽然写到了历史,写到了艺术,却又真切地超越了历史和艺术。它不是对艺术作品的简单描摹,也不是对历史账本的现实检阅,而是通过对意象系统的重建和深刻的思想创新着原文本的呈现方式,并加强了历史的深度,从而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历史、艺术、诗歌交织的多元体系里。诗人通过对《抢掠萨宾妇女》《抢掠波吕克塞娜》《圣十字架传说》《大卫》《帕修斯》等作品的诗意再造,对战争与和平、抢掠者与被抢掠者、放逐与坚守、高贵与谦卑等内涵进行了多向度的书写。
这组散文诗也表现出诗人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文本转译过程中写作技巧的纯熟、敏感和独特的把握。如在写作《大卫》雕塑时,诗人选取了观看大卫雕塑时“45度的最佳仰角”;在写作赫剌克勒斯雕塑时,聚焦于艺术家“如何表达一支离弦的箭”;在写作六尊图拉真时代雕像时,侧重于人物的安静和凝思;在写作帕修斯雕塑时,着重于铜和锡的比例……这些角度和细节的选择,较好地避开了对艺术作品进行诗意转换时 “全面解读”的写作范式,而是通过选取关键性的一点深入挖掘,既节约了笔墨,避免落入类似题材写作的俗套,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所选择的这些切入点,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核”,是诗人进一步追问和提升的入口。因此,艺术作品不过是诗人写作的一个突破口,历史背景也只是为进一步提升诗歌思想的底色,诗人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追寻和灵魂的坚守。诗人试图在艺术作品的文本表达和造型审美中,寻找到遗落在时代历史中的精神印记。
诗人北岛曾经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苏格拉底在回答别人的诘问时说,尽管地球上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仍将按照这座城市的准则行事。说到底,这个“世界”和“城市”,只是一种存在于诗人内心的空间,是一种具有高度精神化的空间。正是基于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建构和灵魂的安放,诗人从艺术和历史中不断走向“高贵的灵魂”和“高处的精神”:从《抢掠萨宾妇女》雕塑中诗人发现了 “那个看不见的旋转中心,叫和平”;从《抢掠波吕克塞娜》的雕塑中反思雕刻家对历史的抢掠,对观看者灵魂的抢掠和对作者的心理抢掠;从一座卓立的塔和但丁的艺术中,表达出“高处”的追求;从“阿诺河水的声音”里,烛照出圣十字教堂流淌的信仰;从《大卫》雕塑中看到 “灵魂从天堂回来,人性开始觉醒”;从帕修斯雕塑中的铜和锡的比例,传递出思想和技艺的炉火纯青……从这组散文诗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刻地领悟到作者所追求的灵魂和情怀。
用厚重的历史背景,提升时光沉积后的艺术品质;用诗歌的语言,实现艺术与诗歌的交相辉映。历史和艺术所传递出的思想,是阿诺河;每一位艺术家和其作品,其实就是一座桥。诗人对历史和艺术的写作,其实正如他所说的,是一次致敬:“向老桥致敬,阳光一直陪我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