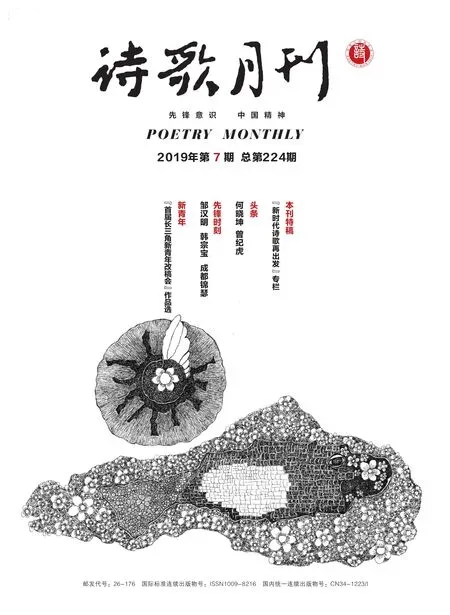曾纪虎的诗
曾纪虎
在熹园
在熹园,生活的某一阶段,大圣和我从旅舍出来
无意把行人的面容,或者他们个性的任何外表迹象
留存于记忆中;纯粹为陌生吸引
似是万念俱无,百无期待
在熹园,醒来的词为空无之花戴上
徽派漆、层楼、回廊;我在树荫下翻读《重点所在》
水边,手执折叠小洋伞的她
肯定了星江河梦幻、翠绿、过度的一面
但是,壁虎翻转白而冷的肚皮吸收花下阳光
观景台上划出纸片线条和无心智词语
取悦于自己的窥视,如同对自己进行一场郑重的拜访
老男孩们汇聚,登幻觉之舟
但是,各种绿的反射往返于不安之中,人也不是光亮之物
而是绿的某种遥远的历史性的呼吸
活在遥远的生活中和活在隐名的生活中
连着日常生活的恒久幻影
但是,整个峡谷般的婺源,街道上
漂流着浅淡的不宁的真实
那里,房子、酒店、石头、峡谷春茶、街头小广告
每一处的事物都有其他事物的痕迹
傍晚之姿
在灰色人行道,傍晚之姿印在眼中
花树、半醒魂人;空中灰光疾驶
投上蕾丝泡影。缺乏记忆的头和心
于隐虑的腿间推开那荒白
于大而无当的桎梏中代舞
翻滚之手,轻盈之手,呼吸之手
他扑击思虑的形状,仿佛
女巫和塑造者业已消停;仿佛
低卑产品才是人身后的景致
二十一世纪,众人死,众人生
轻视;奥妙的灰,策马而过的士
这些,是能说的要旨,重新推进了他的思想
无用
不是的东西并非不在
时机停下来,一座房子,闲慢异常的细节
它环形的碎片宛如歧途
空气中,执意延展的头颅长上翅翼
仿佛,恐怖和庙宇性的欢乐妙不可分
在城乡接合部,废弃的楼盘不是你的
它们属于本地夏候鸟的歌喉
这些形如鬼魅的生灵,体内的篝火晚宴将会藏有:
暗红的沙粒,无垠的丝绸,玫瑰洞穴
你说我会爱上哪一个,在这无用中年
厌倦是好的理由,在光阴反复的一刹那
蓬头垢面的天之子正推动山川旋转
泅渡
秋光下,在公社乡村的窄巷后
那能裁行云,剪流水的,定然是一位妙人
记忆总在修剪,时与地,那种并非如此的感受——
既有悲伤,也让人心领欣悦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月,它已君临上空
在恩江的一处小沙洲上,筋疲力尽的顽童熄灭了心愿
劳碌完的牛群;它们的脸,模糊的面具,伸出水面
我们知道,水流过的声音;我们知道
灶膛里升起火苗——不是为自己准备的
这一群在傍晚时分泅渡归来的生物
有时是我们的玩伴,有时是负担
时光会改变它们,以故意的神秘
显示它们,如同拉长的摇摆的梦境
并且判定它们,像水和空气一般永在
夜归人
在早到者的空间留下你身体的痕迹
在败坏的公井旁,你的身影,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熟知的旧人长睡不醒,好似死去已久
漫天星斗的苍穹下仍有诗人的圆柱
这一世界,越丰富就越糟糕,失去引力的可能性
你看到美人们迷人的后裔,他们是不快乐的
人的杀伐出自世纪之心——
既然土地不能称之为土地,因它已被驯服
丧失应有的对话和循环
既然,空洞之人成为人,那无所不在的面具
你还能有所畏惧,有所恐怖
为何,你还能怀有不合时宜的乡愁
图案
百合色的手指是他人的,并把它
弄进生长着的情欲中
鹚枭们在高树上飞走,接替了鼠神的销魂
一个低估了的玄学家的物体图案
一次尝试,规则,弥漫间接忧愁
逃走的东西经由那里,传递给邻人
——一个躺在草地上的人形
要借助孤立分解出新的意义
他珍藏的小诗将有更多别致的病毒
幽窗劳燕,玉树坐在火中
他不是偶然地走在死亡的路上
有如那必然的另一个
端午前后
端午前后,步行者的脚步移近山林
在自然之眼中,我们的事物裸露
她粉白色的唇瓣,移动
如下沉的弧线
傍晚,一条田埂连接了两个傲慢的农夫
寂静而缓慢的秧苗
空中,微风、橙色落日
荒芜的似要飞走
归途
初冬,隐藏者能找到想要的秋果
他搭上61 路公交车,经过阳光梳动过的防洪闸一带
奇怪于有意为之的聚会
在天祥公园,芳香散去
眼看时间还早,就着一次暂且的步行
考虑纯然快乐的辩护方式
人生始于忧患,诗艺专注病痛
经过数日盘桓,一块根茎,一次碰撞
他的诗句完成了变化和不便表述的互换
飞过的顽童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晚饭后,他将照例早早睡去
万物的形象如此迷人
昆虫的四肢吸附着夜色,事件无限
生命、写作和一切的事
不过是些平常的、飘忽的、晦隐不明的时刻
年轻时我自负而厌倦于镜中的身体
局限在经验的某个领域
割舍了人、物和符号的流动
万物的形象如此迷人,予人悲悯而无怨
我生于此世,感同身受,又如何能
将叙事的无聊感无遗漏地展现在一人的眼前
水下的光
四十年前的乡村边缘
有众多不可持久的事物
如花丛般的棺衣,吹来离愁
后死者并非是某一张脸
或某一双手,某种说辞
他凭借迟来的惊鸿一现,与时间性融为一体
肉身的本义是提示非存在
借由它引申出诸多譬喻
我至今还能想起那几位早到的乡村男孩吗
他们就在那里,在头顶的上方
为穿过平静的水面而来
为穿过平静的睡眠而来
那时,我得以俯瞰整个敦厚小镇
我曾微妙地解析。露台下
荷花呈现一种状态,对着云层喊话
凝固的空间中来了一场秋凉
很自然地想起二十年后,偷窥而位移
你,或许就是可以阐释的市场社会,就是某个
脱离了生活的角色
在一首新作的小诗里
有拜物的意味——人的位置、视线、对话——
都表现在词语的状态之中
那时,我得以俯瞰整个敦厚小镇
一组明天的、以游冶代替情爱的浅薄时间
夜街
在敦厚镇的夜街上,俗世的野性
打败了流变的美德
孩童们的热望美而无趣
自电线杆上下来,双臂携轻雷之风
他们贴上阳光棚、屋顶
将黑色而迷人的柔软植物摘去
一百年也太久——蜷曲的钟情之物
创造的形式源自痛感的催迫
这清风徐来,触物无声
这巨大的月轮驱动光晕
于小镇的背面轻轻滚动
亦将游荡之趣涤除殆尽
在更蓝的瞬间
在更蓝的瞬间,一只昆虫轻移它的躯壳
无人愿意留心它为之丧失的一小片色泽
晚风正是向南驶去
人生中的诸种念头越来越短
低俗之物携带还魂光晕
一对衰败的母子忙着对账
在出城口的三角塘的区域中,阴暗的地方
流水正如人心愿地波动
在躺椅旁边,一个有简单面具的人坐下去
米粒花瓣,带动秋意抹去
亦请花下传香,酒色不来
哦,他肩上有一缕可笑的白色
如此,华灯之夜,在接近,在接近
玄衣童子挑一竿灯笼
从眼皮底下过去了,一切都要流动
他炫耀的诗艺回到节节孱弱的肢体
通常,可以被人接受的静音
会更加忧郁。不要与它背道而驰
更不要凭空生出妄念
柔软的顽童恰如来自地底的信使
可称秘密的是小睡未醒的蛇虫
它压弯的鳞茎如在多重的梦中
他爱的就是他能够爱的
他用它们写作诗篇
小酒馆
幽蓝的光色扩开广大的无声
我的乡村已经衰败,虽然,本不存在
在离县城五里远的地方,两棵纠缠的旧樟树的荫护下
1978 年的小酒馆正在营业
饰演阿庆嫂的幼时玩伴
已从计分桌的储物柜里逃出,来到
这速朽的纬度,他看见
屋檐上的月亮正往恩江河坠落
我通过过去的时间找到他了,他醉颜可掬
矮小的身量更像是某件道具
四只储满秽物的桶立在树荫下
落魄的人正自哀叹,我已经听不见他的呵斥声
麻脸的驼背还在重复他的酒话:
“不喝吧,不喝吧,一喝就醉了。”
这个过去富农的独生子,我们看够了他的笑话
他的样貌给贫困而乏味的乡村带来诸多戏谑
思故园
吾心探入桃花,下午落地
从辽远的方位吹来,春风
触碰国土,不会再给予
能说到一起的人只得离开
他不与你分享,这驱驰南北的精灵
好似人生已经够长——
你要丧去,把更多空洞留给他人
人的异化如既定事实;大的侄儿
正从远路奔来,带一些故园风貌
立在春的蓓蕾之上
阴郁而无望的退场
把花萼的形状揉进人发光的脸面
我看到惊起的麻雀
它在两个小区交界处的空中来回飞
身披白金日光
惜旧日
我记得有限的一些时日
过去的天空飘着飞鸟尸首,年轻岁月
属于不恰当的、你的少年,我的乡村
何时你曾用实在的手将人抚养
朝着什么样的方向逃亡?为何我
有涣散双眼,以帮助更多快乐来临
我记取,银镯代替铁环,代替铜板
滚进池塘码头
小少年,脚踝在水里嬉游
搅起白水花,啊,他的脸荡向何方
人世微不足道,渐渐忘记一处春风
看到,成为雷同幽灵
明瓦、户牖、水杨柳、磨刀人,越转越快
碎屑返回恢复树的轮廓
我爬上一棵高树,在巨枝圆而实的交接处
翻起一本难得的课外书,那时
世界仓促似风而来
乡村在耳语、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