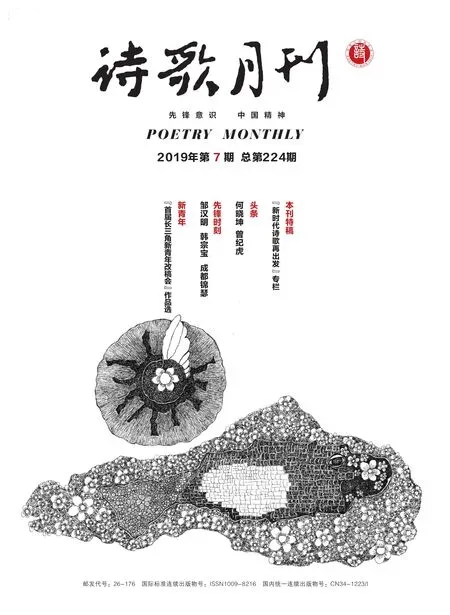肉身化的灵魂书写
——何晓坤诗歌读札
王士强
坦白地说,我此前对何晓坤作品的阅读近乎空白,但近期在读到他的诗之后着实受到了吸引、震动,故而较为细致、系统地阅读了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所谓“专业读者”,阅读诗歌作品差不多已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实事求是地说,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的确是不多的,而能够让人受到冲击、震动、震撼的作品,则无疑是少之又少。何晓坤的诗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
写于2017 年夏天的《写诗何为》大概可以代表近来何晓坤关于诗歌(及人生)的态度和理解。诗歌如此展开对于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的关切:“照顾一个患者需要多少的耐心/这个话题稍显沉重。在时光门外/我们并没有学会,将日子分类储存/没有学会,在那朵浮云的深处/稍停片刻,让肉身静静听灵魂歌唱/谁在幻想,高处的掌声和花朵/谁在忽视,低处的骨头发出的声响/生死被隔开了。需要一抹暮色/把渐行渐远的影子,从天边拽回/还给大地和尘土。”其中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比如在“浮云的深处”“让肉身静静听灵魂歌唱”便是极为动人的一个意象,精短但却包含了巨量的内容,浮云、肉身、灵魂构成了富有张力的三角关系,由此,人生的“大戏”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地展开。再如其中“需要一抹暮色”以把“渐行渐远的影子”还给“大地和尘土”,以及关于“高处”和“低处”的书写,均别致而有意味,有着对于人生真谛的洞察。诗的最后写道:“写诗何为?谁在把最后的凋零/装进了语言的寺庙。看雪白的床头/临死的孤独,远比诗歌具体/空空的疼痛,远比文字揪心”,最后的凋零、语言的寺庙、临死的孤独、空空的疼痛……均有着极为丰富的阐释和想象空间,包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非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千山万水不可得,无论是对于诗歌的理解、对于人生的理解,都达到了一种极深、极高的境地。叫作何晓坤的这个诗人,无论其世俗之名气、地位大小,不可等闲视之。
——而这首诗里面的“让肉身静静听灵魂歌唱”在我看来在何晓坤整体的诗歌中也颇具代表性和阐释力。“肉身”与“灵魂”是他诗歌中一对重要的、具有原型意义的关键词,很大程度上,他的诗歌是一种灵魂叙事、灵魂书写,但他的书写不是完全精神性、形而上、凌空蹈虚的,而是肉身化、在场、及物的,他的写作是一种肉身化的灵魂书写。
1
人生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它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需要面临和处理的问题,却同时也是古往今来一代代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勠力求索而终无答案的终极性问题。这样的终极性问题,中国古代有被称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的屈原的“天问”,西方哲学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它们或许都难以被穷尽,难以被“解决”,但是,对它的靠近、思索,却是必要而有益的。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许正在对于这样的终极性命题的靠近、思索和个性化解答之中。何晓坤的诗,在我看来便有着对于上述终极性问题的思索,或者说,这些终极性命题是他诗歌写作的背景和基础,他从未停止对这些命题的思索,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或远或近地对这些命题做出呼应和解答。
《在月光下漫步》中写了人的诸种形态:“此时在月光下漫步有人沉醉于过往/有人憧憬着明天也有人会想起别的什么/比如头顶的神灵比如脚下的蚂蚁/更多的人什么也不想任凭孤零零的影子/晃过毫无意义的时间”,这里面便涉及人生的意义问题,沉醉过往与憧憬明天、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蚂蚁,其中或许并无对错、高下之分,都是人生的一个维度和侧面,唯如此,人生才有了丰富的可能和无尽的魅力。“时间”之意义的有无,更多端赖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和选择。有意义只是短时间的,长远来看则可能“望远皆悲”,终无意义,对意义有限性的认知是一种智慧,对“无意义”的认知本身也是一种反抗,人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与“无意义”的两极之间辗转、寻索、行进的。人生是复杂的,自我也是复杂的,如其在诗句中所写:“春天的灵魂”,“一半是止水一半是烈火”,“霞光中的一朵油菜花”,“一半是盛开一半是凋落”,而“浮尘中飘过的那张脸”则是“一半清晰一半模糊”(《中国哲学之隐喻》),这样的发现无疑是较为全面、深刻的,而对于自己,他同样有如此的发现:“在我灵魂的两隅/分别潜伏着魔鬼的狰狞/和天使的笑脸”(《在钻天坡顶看油菜花》)。对于一只飞翔的“大鸟”来说,天堂与地狱也不是截然二分的,它们甚至就是一体的:“一只翅膀指向天堂/另一只翅膀指向地狱”,“指向天堂的翅膀苦撑着肉体/指向地狱的翅膀膨生着欲望”,如此,大鸟自身不能不面临抉择的艰难,“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均等/都只一翅之遥大鸟横陷其中/两只翅膀指着两个方向/不知如何扇动”,最终也只能是“一只翅膀飞向天堂/一只翅膀落入地狱”(《大鸟》),这里面不是简单化的认知与选择,而是指向一种暧昧与复杂,唯其如此,人生才更为包容、丰富、立体,同时也更接近真实。
诗歌《与自己书》中写道:“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吧/把过往像垃圾一样运走这样的年龄/不该有疼痛和疯狂也不再纠结和幻想/回到内心去煮一壶清茶安静下来/看看夕晖里的大地多么柔软安宁”,这里面包含的洗尽铅华、宠辱偕忘、平和自然,可谓诗人何晓坤精神追求的夫子自道。诗中继续写道:“包容裂痕依旧的光阴原谅自己/也原谅整整一生不离不弃的影子/告诉它委屈了跟随了大半辈子/也没有长大以后还会越来越矮小/现在我要去打扫落叶了如果你还愿意/就和我一起弯下腰去”,关于时间,关于万物,关于自己,“世事诚可原谅”,这里面包含了慈悲、豁达,是直面自我、直面自身命运之后的感悟,既关乎当前与自我,又关乎每一个人,关乎永恒的时间和“万古愁”。在《瘦身》中,他写身体里多余了赘物而带来的疼痛,从而引出了应该瘦身、如何瘦身的问题,“背着金子在江水中逃命的人”同样“没有学会瘦身”,作者并未简单地做出价值判断,但这样的意象和表述却触目惊心、引人思索。
2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人生有如登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勇于登攀、壮志凌云、登高一呼自然是好的,但这也不是全部,其中还有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过程与结果的问题,是否“高处”一定是好的,而“低处”一定是需要克服的,如此之“高度”的标准是否过于单一了?等等。在《山顶》中,何晓坤对此有他自己的理解:
山顶直插云霄仿佛已经成为/天空的一部分我们的一生/都在仰望山顶这个天空下的贵族/也一直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万物/我们一直以为离天空最近的/就是山顶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登临这个地方耗尽自己/当我们穷其所有爬到山顶/却怎么也看不出高处和低处/与天空的距离究竟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正是如此,人们终其一生所爬的“山”,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或许不过是一个土丘、一粒泥丸,爬上它与不爬上它根本就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此是否就不必劳作、不必攀登,这样的行为就毫无意义了呢?恐怕又未必如此。正像西西弗斯不断推巨石上山未必只是荒诞和无意义一样,这种劳作的过程或许本身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包含了生命的壮丽与庄严。在《爬上窗台的蚂蚁》中有与此类似的情境,“有人在处心积虑地囤积阳光/有人在阳光灿烂的黑暗中四处逃窜/这是我所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奇妙景象”,他也曾做出诸种努力,到最后“而从天空到大地从有形到无形/所有的门窗都已关上/我只能悄无声息地转过身去”,而当他抬头,“那些穷其一生爬上窗台的蚂蚁/正把小脸贴在厚厚的玻璃上/诚惶诚恐地朝里面张望”,这里面的人并不高于蚂蚁,蚂蚁也并不低于人,更重要的,蚂蚁和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境遇,在这背后,或许是所有的生命、生存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由对人生的如此深入、深刻的认知出发,何晓坤的诗达致了一种平静、达观、睿智的境地,宠辱不惊、平淡自然。譬如河流:“静止中的河流不生一丝波澜/荡尽了沧桑和惆怅浮华和喧嚣已无踪影”(《不要试图打破一条河流的宁静》),譬如流星雨:“归途已清扫干净一生的悲喜即将结束/万物寂静大地心疼地张开双臂/像母亲紧紧搂住在高处挣扎了一生的游魂”(《猝然坠落的流星雨》),譬如湖泊:“而湖水有着深不见底的平静”(《面对一个湖泊》)。在《风动之后》之中,他写道:“……风动之后/万物皆弯下了腰,风中的小草/头颅也深深地埋进了浮尘。”万物即我,我即万物。在《多年以后》中,他写道:“多年以后我会最后一次走进内心/收拾最初的柔软与疼痛清扫最后的灰尘”,直面生死、命运,其中有大宁静,亦有大悲悯。由这样的书写可以看出,何晓坤的确是一个关心灵魂、关心终极的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的精神世界高阔、辽远,内心则是宁静、自足、从容的。
3
何晓坤诗歌同样有着切近的对于人世、历史的观照,他不是凌空蹈虚地进行玄思冥想,而是在现实、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生命观照的,及物、深切、有力。
比如在《听父亲说家史》中所叙说的并不遥远的家族历史:“你的祖父,是个好人,死于枪杀/你的祖母,一生念佛,死于天灯/祖父之弟,一个山河爱好者,死于狱中/祖父之妹,生而有度,死于惊恐”,这些历史成为沉重的石头,父亲“十五岁”即开始背负,现在转交给了“我”:
交给我吧,父亲!我也背不动/我会替你把它交给时间,它是个雕刻师/它会把这块让你喘息一生的石头/雕成废墟里的菩萨,雕成天空的祥云/雕成春光和满山遍野的花朵
这里面有对过往历史的不动声色的控诉,同时也从中跳脱出来而没有被这“沉重的石头”压得喘息不得,看到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往好的方向发展转化的可能。这种亮色、希望的存在是重要的,也是人之为人、诗之为诗的核心要素之所在。在《软肋》中写到了过去特定历史场景中的一幕,外公是“地主”但却免于被批斗,甚至“每天都能抽纸烟,喝小酒”,其“原因很简单,他是十里八乡/唯一会写春联,会为活人喊魂/为死人超度的读书人”,因为批斗者也有“软肋”:“批斗者有软肋,都不敢保证/春联不贴,死人不超度,活人不喊魂。”诗行简短,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让人啼笑皆非而又深长思之。
何晓坤的目光始终不脱离其所身处的现实世界,他关注现实的变化,书写着时代之变革。《回村记》中所写便颇具普遍性和概括力,故乡已成“异乡”,许多的东西都“不见了”:“羊肠小道不见了/茅草屋和红瓦房也不见了/老槐树下的唠嗑不见了,暮归的牛羊/也不见了。火塘不见了/炊烟不见了,堂屋内壁的供桌/也不见了。供桌上的天地不见了/祖宗的灵牌不见了,香油点燃的灯火/也不见了。”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物“非”人亦“非”,“村头的那座小树林,也不见了/它成了乡村客运站。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一条狗趴在他脚边/不知道他是在等离城的客车/还是等回城的亲人”,所呈现的是当今中国大规模发生、触动人心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现实图景。何晓坤关注现实,同时关注现实中的人,或者说,他更为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内心和处境。
何晓坤的诗关乎精神、关乎灵魂,有着超拔、高远的一面,但是,精神和灵魂并不是没有温度、冷冰冰的,不是对于现实生活、现世生活的拒绝。他在诗歌《欲望》中写:“法师说,你们的灵魂装满欲望/魔就统治了心灵。看看你们的身后/每一片云朵都在喘息,每一个影子/都在逃亡和追逐。花开花落,转瞬即空/清空你们的欲望吧,跳出心的牢笼/在这心惊肉跳的人世,唯有成佛/能解救你们的灵魂。”“成佛”自然是一种途径,但是,却也并不是唯一的,不是目的,正如另一种声音所说:“突然一个声音响起/请问法师,在这心惊肉跳的人世/还有什么样的欲望/大过成佛”,这种审视和反思自然是重要的,对于保持平常心,保持理性和健康的生活是一种必要前提。一定意义上,“佛”并不在现实生活之外,并不排斥肉身、欲望与俗世,而是就在红尘之中,就在人间烟火之中。故而,何晓坤的灵魂书写又是肉身化的,是身体在场的,是感性的、在世的、“有声有色”的。他尊灵魂而不孤绝,重肉身而不沉溺,通过这样的灵魂与肉身相结合的书写,何晓坤的诗歌在“诗”与“思”、美学与历史、意义与修辞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