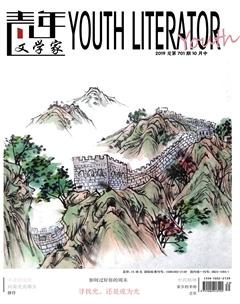“词典写作”中的反叛意识
摘 要:《马桥词典》作为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韩少功极具价值的作品,曾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词典写作”的文体样式可以看作是韩少功在文化“寻根”深入到语言层面和小说形式实验之间找到的极佳联结,在当代长篇小说艺术探索上具有突出的价值,而其写作中所蕴含的反叛意识和反叛姿态下对民族文化血脉的守护,于当代文坛来说更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马桥词典》;韩少功;词典写作;反叛意识
作者简介:唐钰尧(1992-),女,汉族,四川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04
随着时间的流逝,著名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为一部带有突出原创意味的小说经典,这一结论已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尽管上世纪末,围绕这部小说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经典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对于经典理解的终结。相反,一个文本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对于它解读的无限可能。所谓经典,始终是一个敞开的文本,等待着后来人从各个视角及不同层面去理解和阐释。《马桥词典》看似一本方言词典,实质是以“词典体”即“词典编撰”的形式写就的小说,每个词汇的“释义”都牵引着“马桥”这个地方的一个故事一段逸闻,故事与故事衔接,人物与人物關联,钩沉着“马桥”历史的纵深;由此,众多的故事组成了“马桥生活”,众多的人物构筑了“马桥世界”,而众多由“马桥世界”吐纳的词语又汇集成这部独特的“词典”。
韩少功曾以被视为“寻根宣言”的《文学的“根”》一文和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及一些被广泛讨论的短篇小说,被确认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多年来的笔耕不辍,从早期的“伤痕”、“反思”潮流到中期的“寻根小说”,直至九十年代以来的“跨文体”写作,韩少功皆用不凡的作品带给当代文坛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他的创作生涯也被许多学者视为与“新时期文学”的生长发展具有某种同构性。作为韩少功的首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出版之初就引发了多方关注和讨论,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同时期,许多评论家及作家都撰文表达了他们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其中有对于小说形式创新的激赏,也有对作品精神价值的赞誉。大多数评论家一致认为“词典写作”的巨大弹性使韩少功的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皆获得了恰当的安放,《马桥词典》打破了文体界限,为小说提供了一条新的审美道路;还有学者从文化多元时代认识相对化的大背景上,以人类学、社会学或者民俗学等视角阐释《马桥词典》,肯定其作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文本所具有的认知价值。但在收获多方赞誉的同时,也夹杂有对于“词典小说”文体合法性的质疑:“我们可以对于词典形式能否成功地表达小说的美学特征、‘词典小说这一艺术体裁能否成立进一步提出讨论和质疑”[1]。韩少功对中国的文学传统有过深入的钻研和精心的选择,同时也对西方文学有着比同代作家更多的了解,他因而拥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高度的文体自觉。韩少功的作品获得重视的原因除了对“寻根”的深入关注,也表现在不断加强的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使中国当代经验的书写在内容上接通传统气脉和形式上打破陈旧体式,进而让当代小说创作有了民族文化的底蕴和现代主义的先锋气质。小说《马桥词典》内容中含有的高浓度文化价值和文体形式上对于传统小说的“反叛”,即使是在今日读来,依然充盈着新鲜活泼的感受,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马桥词典》的“词典写作”和其中所蕴含的“反叛”意识,对于日益僵化和失血的小说创作现状来说,不啻具有一种启发作用。
一、小说文体的“反叛”
“语言”、“词语”作为《马桥词典》的主要书写对象,从宏观上来看,受到二十世纪世界性的“语言学转向”人文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在学界已然达成共识,特别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对当时的文艺界影响深远,《马桥词典》中对于语言(方言)的特别关注在韩少功的笔下也显出了某种哲学内蕴。
韩少功在90年代写就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随笔中表达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仅对文化现状有深刻的见解,同时也可以视作他为创作小说《马桥词典》而做的思想准备。蒋子丹在《韩少功印象》一文中说过韩少功是一个“怀疑论者”,读过韩少功散文便可以发现,“怀疑”可以说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怀疑”使他凡事多了一份审慎和质疑,特别是大家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怀疑”让韩少功成为了一个寻根究底的探索者,面对一切定规化的事物,现实也好,文学也罢,这种怀疑和探索,皆携带了“反叛者”的姿态,可以说是对语言的反思和对小说文体的“怀疑”共同促使了《马桥词典》的诞生。“词典写作”不仅重新建构了小说的表现逻辑,而且将韩少功此前许多主题集中汇聚,尤其是“寻根”意识的一以贯之,使小说语言的、文化的、哲学的思考别具一格。
众所周知,词典是记录语言使用的工具书,如同一个词语仓库,以某种顺序把人类公共话语系统里的各类词汇储存在一起,方便提取和使用,处在人类公共话语结构中,由某些具有“权威性”的语言学专家编撰,接受来自某些“权威机构”的审定,每个词条的释义要求客观准确,因而使之具有语言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作为工具书的词典,每一个词条所取的释义必定是社会语词意义的“最大公约数”,简化一个个词语的来龙去脉,把感性归指到理性,使具象化约为抽象,将情感演绎成概念。相反,小说作为最适合“讲故事”的文类,“虚构性”是其招牌标签,小说文本通常离不开“人物”、“环境”、“情节”这几个要件,时间律和因果律更是推动故事起承转合的动力,因此制造出一个个闭合的系统,给读者一种近似于“现实”的完美幻觉。那么把“词典”写作“小说”,即是将小说与非小说文体进行杂交,将“客观”概念的释义与“虚构”人物的故事进行缝合,是一种大胆的文体实验,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这种“缝合”的完整与否无疑是对写作者的巨大挑战。“词典体”的碎片状天然具有后现代文本的某种“解构”倾向,“词条释义”的形态用一个个词条及其背后断章般的叙事拆解了长篇小说惯用的“整一性”故事构造,对打破传统小说封闭单一的结构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读过《马桥词典》的人可能都会赞同,“词语编撰”和“词语释义”作为其最主要的叙述手段,是构建整部小说的基石。“词典写作”在文本中发挥着形式功能的同时也充当了某种叙事内容。在传统小说的书写中,“词语”只不过是作家笔下等待被差遣的兵卒,是为叙事内容服务的工具,是“形式”的组成部分,一种物质外壳般的存在。韩少功则第一次以小说的名义,把“词语”本身作为直接的书写对象,耐心考据词语的前世今生,生动叙述词语的来龙去脉。一个个词语及其负载的人和事在作者笔下拥有的平等性,使整部小说读来并不存在焦点或重心,而是拥有清明上河图一般“散点透视”的效果,处处丰富精彩,许多词语包藏的故事里常常掺入作者的发散性思考,感性和理性兼用使文本形成叙事与议论糅合的特殊形态。“散点透视”的笔法同时也带来了叙述视角的滑动,以此形成不同角度和距离的关照,使描写的对象“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打破了单一的价值形态。在小说里,读者可以发现叙述者的不同身份:有一个知青韩少功,他是马桥生活的参与者,在他的眼中马桥的人事多作为一种“在场”的现象而存在;有一个“词典编撰者”韩少功,他似乎是以一个学者身份在“马桥弓”做田野调查,通过方言撰写“马桥”的民族志;还有一个“小说家”韩少功,他是“马桥故事”的虚构者,第三人称的叙事拥有“全知全能”的视角,以想象和思索填补了马桥现象以外的空白。三个叙事身份共同构筑着“马桥世界”似真似幻般的立体丰富。
作为一个因文体自觉而备受称赞的作家,“词典写作”的文体动机明确蕴含着一种反叛精神,这种精神在词条“枫鬼”的释义中有直白地表露:“我写了十多年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2]在“讲故事”里表达叙事动机,这种叙事的自我指涉使得文本呈现出某种“元小说”[3]的因素。韩少功认为真实生活是由词语与词语交汇合成构建的,同时也镶嵌在经纬交织的因果网络中,因此那种主线凸显的传统叙事模式至多只能充当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不符合实际生活里万端纷纭的因果线索。就实际状况而言,人类社会由不同的生命脉络和生活实践缠绕交织而成,很多时候更多是一个复杂暧昧的整体,而非层次分明单线运行的平行空间。基于这一认识,“词典写作”的明确动机就是要反叛小说叙事传统里已然固化的“主线霸权”。韩少功有意削弱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而强调“词典编撰者”的位置。“他选择了词典这种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对世界的恭谦态度”[4]他要把自己还原到“马桥世界”的一个观察者,反叛小说家们对自己笔下世界“一手遮天”地全权操控。
二、“反叛”的价值
作为“先锋”或是“异端”的反叛者们兴致勃勃地要与反叛对象决斗,他们不屈的姿态里常常充满傲人的生命力,但是发力错误的反叛和为了反叛的反叛通常都只能降格成一种空洞的文化姿态而已,如同堂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重要的是追问反叛的价值何在?那么不得不涉及的问题便是:作为一种与“传统”决裂的叙事方式,“词典写作”的价值何在?
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本该是血肉一体不可剥离的,如果说文体是作者依据某种审美目的精心编织而成,那么其本质也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词典写作”的面貌本身便可以看作是《马桥词典》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韩少功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和反思,在《马桥词典》的文体策略里更多地指向了包含在小说文本中不易被读者察觉的意识形态的痕迹:“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能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5]、“这也许正是意识形态危险驯化的一部分。一个个意识隐疾就是在这种文体统治里形成的。”[6]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本,内在地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小说修辞学》的作者布斯把叙述主体的感情、议论等均看作是控制读者的一种叙述策略。如果说语言和叙述技巧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那么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之中的意义观,使一些人和事进入了小说而筛弃了另一些人和事,而这种“意义观”也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7]某些未被记下却真实存在过的人和事便是如此被遗忘在生活的犄角旮旯里,不留印迹地自灭自生。然而,又正是“词典体”在结构上的自然、平等,才使得“词典写作”具有挑战主线霸权意识形态的可能。“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8]《马桥词典》想要做到的便是打捞一些在传统小说主线叙事的“宏大性”或“整一性”价值下被筛弃和忽略的人物甚至事物,它们可以是“长在罗伯家后院”那两棵被命名为“枫鬼”的树,一头名叫“三毛”的牛。作者也可以“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9],以确立它们独特的价值。这无疑是对主流叙事的反叛,更体现了韩少功眼中“万物平等”的博大情怀。“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10]“词典写作”对读者惯有期待视野所滋生的阅读惰性也是一种挑战,每一个词语都可以被当作是进入“马桥世界”的一扇门,读者不必依照传统小说的阅读模式从头至尾才能读懂《马桥词典》,而是可以通过平常使用词典的方式从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词语进入小说内部,进入众多不同的命運所交织出的一场场悲喜剧,这样的“马桥世界”因敞开而拥有了无数个侧面,以帮助读者构建新的感觉模式。作为小说家的韩少功,“马桥”也只是他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审美对象,作家在词条背后的知识发挥并不一定来自严谨的科学考证,更多的则是来自个体的生命经验和情感触动。“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本书的作者,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11]这才是一个作家区别于一个语言学家的视角,是韩少功“编撰”这本“词典”的意义。普通词典为大众提供关于词语科学的实用的知识,而小说《马桥词典》反叛科学的常规的解释,提供给读者更多的是具体生命的情感和想象,这是关于词语文学的审美的知识。
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提出过应该把文学的“根”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12]。相对于同时期“寻根”作家阿城、张炜等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的关注,贯穿于韩少功创作实践中的则是对于处在边缘位置的楚文化的持續思考,《马桥词典》可以看作是通过地域方言的收集而保存楚文化遗风的一种努力,是对“现代性”社会中文化“一体化”和“同质化”趋向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下却潜藏着守护的实质,为了守护民族文化“根脉”里曾经重要的地域文化,以还原汉民族文化原生形态的多样性。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自古以来就被儒家的正统文化和“现代中国”以及“革命话语”等价值观念所筛弃,同时也生长在“科学”势力控制相对薄弱的乡野地带,少了来自庙堂的规训和“现代性”的侵蚀,一直在主流文化的外围野生野长,虽然充斥过多非理性的因素,但其内里自有一股野性不羁、昂扬充沛的生命力。从《爸爸爸》开始,韩少功始终坚持对于民族文化性格的深层剖析,对于传统文化秩序及价值观念的透视与批判,“他依然在寻根,但根的呈现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概括和描述了。”[13]《马桥词典》可以说是“对整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秩序,完成了高度寓言式的整合”[14]比起《爸爸爸》浓厚的寓言色彩,《马桥词典》更多的人物形象,更复杂的性格特色,更错综的因果线索等再掺入知青经验和“韩式议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爸爸爸》的扩充版,只不过在描写笔法上更接近生活真实,少了变形夸张。
《马桥词典》第一次以“词典”这种“权威”的形式,给“未被现代社会命名”的野生文化命名,同时释放出被封存在方言词语内部的人和事,通过呈现一段故事或一段曾经鲜活的人生,给一个个冰冷的符号重新注入生气,使词语还原成有体温的血肉之躯。从“死”文字到“活”故事,“词典写作”要做的是:把语言还给了语言。现代社会里的千言一律人云亦云,词语在被密集使用和复制的过程里,其出身之处的原始经验和感受早已损耗溢散,如果说保存方言是保留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在全球化浪潮持续冲击着的时代,为了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势力范围和扩大流通领地,普通话的发展不得不面临“工具性”增强而“文化性”减弱的现实,字词不断地剔除自身原始的感性内涵,一个个符号和词语成了越来越抽象乏味的存在。“《马桥词典》的写作是逆语言发展的历史而动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抗拒汹涌澎湃的语言普通化进程带来的歼灭性暴力。”[15]同时,通过“马桥方言”韩少功为读者展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图景,马桥人以他们特有的价值观置换了普通话里许多词语的含义,比如“科学”成为了“懒”的同义词,“醒”是“蠢”的意思,“漂亮”带有“不和气”般的不怀好意,“模范”在晴天和雨天却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叙述中,有韩少功对马桥人落后愚昧的批判,也暗含了作者对某些传统美德的留恋,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在现代社会中已然失落。
三、结语
“八五”新潮以后,翻译盛、文化热、“主义”热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渐趋形成文坛的主流。不得不承认,作为思想资源的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对国内作家们创作“技术”上的升级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随时间推移,“从语言的空转到思想的空转”,“形式主义”的诸多弊病也逐渐凸显。韩少功对“新时期文学”以来国内文坛存在的“唯形式至上”一直持有警惕和清醒的认知,他认为技术无罪,但唯技术至上,形式玩过了头,小说的表达脱离了现实“引力”就只剩下语言的“空转腾挪”,仅仅只有“叙事游戏”的文本是无法带来情感冲撞和心智开启的。韩少功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兼容并包地配合自己感性流动同时智性发散的文体形式,“词典写作”的散发状正好配合了他的感知和思维的方式,小说在他的笔下更近似于一种综合的艺术体;同时,作为一个坚守的“文化寻根者”,“寻根”始终是贯穿其写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母题。“寻根”小说向民族文化厚实岩层中的深入勘探,可以看作是使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更具辨识度,进而使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努力。韩少功作为文化书写者中的文体“先锋”,一次又一次突破了文体的边界,为民族文化寻找更合适的安置之地,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改写着当代文学对于“小说”内涵的认知;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在《马桥词典》里,韩少功的杰出之处体现在形式突破与文化书写的高度焊接之上,是更扎实更深入的文化反思奠基了文体的突破。
《马桥词典》反叛的表征背后是作家艺术观念的更新,是中国文学步履不停的“现代性”探索,也是融入“世界文学”的努力。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对本土文化资源清理、继承、批判、再造,拥有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精良民族血脉的“现代性书写”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学”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如同威廉·福克纳笔下的弹丸之地“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小镇“马孔多”,“马桥弓”也同样是韩少功丈量人类世界的尺规。《马桥词典》的“词典写作”在“寻根”的持续深入和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之间取得了效果极佳的联结,给予了当代文坛持久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2]韩少功:《马桥词典·枫鬼》,作家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一般认为“元小说”是一种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传统小说的叙述内容一般关心人物、事件,而元小说则更关心作者本人创作这部小说的相关过程.
[4]张新颖:《<马桥词典>随笔》,《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5]韩少功:《马桥词典·枫鬼》作家出版社,1996年9月.
[6]韩少功:《暗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
[7]韩少功:《马桥词典·枫鬼》作家出版社,1996年9月.
[8]同上书.
[9]同上书.
[10]韩少功、王尧:《文学: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韩少功:《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作家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2]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76页.
[13]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增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14]季红真:《末世的孤愤》,《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孔见:《语词的命运——重读<马桥词典>》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