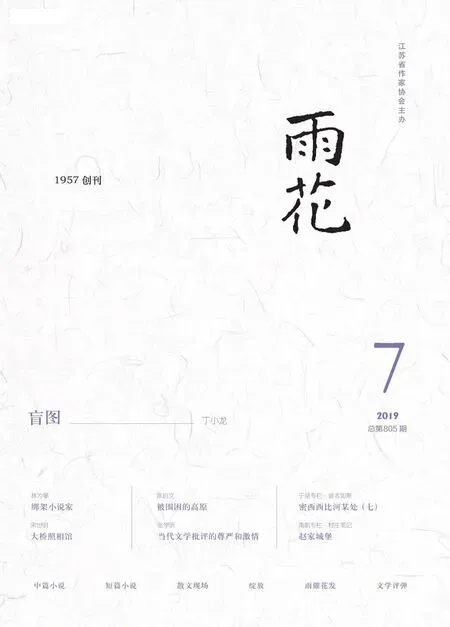赵家城堡
南 帆
我多次觉得,似乎拿赵家堡没有什么办法。去过赵家堡两趟,一直想写些什么,但至今还没有写出来。
“赵家堡”这种称呼肯定隐含了传奇的意味,家族,城堡,一个封闭的空间,世代的恩怨情仇……可是,赵家堡的“恩怨情仇”远远不止家族的兴衰,而是积攒了整整一个王朝的怨恨。南宋德祐二年,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被俘,宋恭帝宗的哥哥赵昰与弟弟赵昺侥幸出逃并且进入闽地,赵昰福州即位。由于元军疾速迫近,宋室不得不离开陆地漂泊于海面。赵昰不久去世,众臣拥戴赵昺为帝,乘船逃往广东崖山。小朝廷喘息未定,元军已经循迹而至。一场力量悬殊的决战之后,苦苦挣扎的宋朝终于吐出了最后一口气。陆秀夫背负九岁的赵昺投海自沉,随后,十万之众的军民追随殉国,密密麻麻的浮尸起伏于海涛之间。
乱军之中,十六艘战舰突出重围逃离崖山海面,闽冲郡王赵若和与他的几个侍臣正在船上。这些船只北上返回闽地,至厦门附近遭遇飓风,仅幸存四艘。赵若和等人只得舍舟登岸,藏匿于闽南一带,为了躲避元军的追杀而不得已改姓黄。“黄”者,“皇”也,皇族的身份仅仅剩下一个可怜的谐音。明代洪武年间,赵若和的一个后代遇到了官司,被诉与当地的黄姓通婚,有伤风化。赵若和的后代不服,出示谱牒证明他们的赵氏身份。这件事飞报朝廷,朱元璋格外开恩,下令恢复他们的赵姓。多少年过去之后,赵若和的九世孙赵范考中进士,为官一任之后厌倦仕途,卜居山间修建赵家堡。赵范之子赵义赴开封、杭州游历,返回之后再度扩建赵家堡,仿造各种两宋故都的建筑景观,以至于人们可以将赵家堡想象为宋朝皇城的大型沙盘。
改朝换代,泣血椎心,春花秋月,故国不堪回首——如此曲折的历史情节,为什么我迟迟写不出什么?
踏上一条石板路穿过赵家堡厚厚的黄泥城墙,心跳如鼓,双目圆睁。门口附近那一棵大树栽种于何时?枝杈横斜,墨绿色的树叶浓密得如同一头乱发。斜阳照在一排石块砌起的房子上,所有房子的屋檐都高高地翘起。小广场上放置几个花岗岩石墩作为旗杆的底座,竖起的大旗杆悬挂两面杏黄旗,上面分别大书“赵”“宋”二字。一个妇人走出石房子晾晒衣服,随后又掩门而入。几只鸡在小广场上悠闲地踱步,一条狗迈着小碎步轻轻地跑过。发生了什么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回头看了看,确认已经跨入赵家堡,两层楼的城门黑黝黝地戳在阳光下。城墙是城堡的躯壳,躯壳的坚固程度意味的是安全指数。我知道赵家堡的外墙是三合土筑成的:长石条作为墙基,黄泥之中调入糯米和红糖,同时掺上若干碎贝壳,墙体厚两米左右。传说之中,这种墙体的坚固程度不亚于水泥。一代又一代的赵姓子孙攥紧双拳、神情肃穆地坚守在城墙之内。他们谋划出了什么?
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以佯醉的姿态伸出胳膊轻松地揽过一个王朝。赵氏掌管天下三百一十九年,交出去的时候却哀鸿遍野,血流成河。金兵掳走了宋徽宗与宋钦宗,囚于冰天雪地;元军将另外半个宋朝推到了海里,沉没于无尽的波涛。偌大一个宋朝仅剩赵若和这一支血脉隐姓埋名地潜伏在闽南深山密林。他们屏气敛息,心惊肉跳,避开元军的搜索而存活下来成为赵若和后半辈子的大业。当然,他们需要“潜伏”名义。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可以东山再起,光复大业,否则,如此屈辱地活下来又有多少意义?由一文不名的贱民晋升为天下霸主,所有的回忆都是自豪的励志;由天下霸主重返一文不名的贱民,所有的回忆都是痛悔的咬噬。失去了皇宫和各种皇族的头衔,这一份骄人的家族记忆是仅存的唯一财产,无论如何不能遗失。历史行色匆匆地穿过元朝驶到了明朝,汉人终于返回金銮殿。但是,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如同废纸片似地飘落于中途。坐在龙椅上的已经是朱家的人,赵家的成败早就退出舞台而成为模糊的前朝旧事,刻骨铭心的只能是赵家的后人。赵范每一次重读家谱,温习家族记忆,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赵范父子一定时刻担忧,谱牒的口口相传或许会意外中断,烙印在子孙后代意识之中的痛苦痕迹或许会突然烟消云散。必须赋予某种坚固的物质。花岗岩,三合土,日复一日地出入的建筑物,这一切无疑是贮存家族记忆的最高形式。我相信这是修建赵家堡的初衷,回避另一些家族的骚扰或者防范海盗仅仅是次要目的。
赵家堡设置外城、内城与“完璧楼”三重空间,这显然仿造汴京的外城、内城与大内。外城筑四个城门楼,东门的牌匾为“东方钜障”,西门的牌匾为“丹鼎钟祥”,北门的牌匾为“硕高居胜”,南门决绝地关闭,赵家再也不愿意向南出逃。曾经一路向南,从汴京、临安到崖山的最后一刻。南面是宋朝的伤心之地,赵家堡的大多数房子面向北方。
前朝的皇族后裔聚族而居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一个新兴的政权必将竭尽全力弹压遗老遗少的复辟图谋。赵家堡的香火竟然摇摇晃晃地在元兵铁蹄的缝隙延续下来,这种例子大约绝无仅有。明朝的气氛缓和了许多,但是,赵范念念不忘祖先的屈辱,他觉得赵家的子孙没有理由松懈。我对于赵范产生了一些好奇,这个人物的性情之中流露出坚毅、敦厚和严谨的成分,肩上似乎扛得住一些重量。赵范曾经担任无为州知府、磁州知州、户部郎中,两度赴西北督边。明神宗肯定了赵范的政绩,不仅写了一块匾额“福曜贺兰”,同时还赏赐了金银。赵范退休之后返乡,这些金银即是他修建赵家堡的资金。赵范给赵氏家谱写序的时候,痛心疾首之态溢于言表:“奉使出雁门关,吊胡马嘶风之遗,发怒指誓,厉兵秣马,长驰胡漠,勒石燕然而雪耻,以酬先世,壮志未酬,驰驱已倦,归休于林泉之下,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山川环郁,家范五十三条,无日不讨族姓而申儆之,告以王业之艰,绳武不易,而战兢临履之不可以已也。”坊间的舆论存在一种观点:宋朝皇族的老赵家这一脉血液之中,缺少的就是坚毅、敦厚和严谨这些品质。
许多人构思的宋朝形象是,一袭华丽的长袍披在一副文弱的躯体之上。人们可以轻易地描述一个文采斐然的灿烂宋朝:造纸,纺织,农业,瓷器,贸易,造船,那么多行业仿佛一起苏醒过来,四面八方地架构起一个熠熠生辉的宋朝。宋词,古文,书法,绘画这些门类的大人物不必多说,人们立即想到了苏东坡,辛弃疾,欧阳修以及苏门六君子那些人;程朱理学仿佛有些刻板,但是,宋学将儒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将视野延伸到科技,人们还会言及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朝缺少什么?这个问题远为简单:宋朝缺少杰出的军事家。人们熟悉的杨家将大部分是演义出来的,真正驱驰于战场的是使一杆沥泉枪的岳飞以及他率领的岳家军。然而,他被朝廷的十二道金牌火速召回,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多一首宋词或者少一幅书法作品无关紧要,缺少军事家是一个国家的致命破绽。宋朝是不是发生了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例如那个宋徽宗赵佶。赵佶相貌俊美,轻佻浪荡,时常出入青楼。据说他的父亲宋神宗看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再三感叹李煜的优雅风流,不久之后赵佶出生。宋徽宗自幼喜好笔墨丹青,书法和绘画天赋非凡。宋神宗传位宋哲宗,宋哲宗无子嗣,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弟赵佶继位。当时的宰相曾经直言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是,他仍然在太后的支持之下轻松地胜出。赵佶执政二十五年,治国无方。金兵大举南侵之际,他惊慌地将手中的皇位抛给了儿子宋钦宗,转身离京南逃。第二年金兵破汴京,废徽、钦二帝,并且将后妃、宗室、百官、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数千人以及仪仗、冠服、礼器、珍宝玩物等完整地打包押送北方。靖康之年,北宋灭亡。
金帝显然十分蔑视他的宋朝对手,徽、钦二帝分别被封为昏德公与重昏侯。赵佶的表现仿佛更像艺术家或者诗人而不是一国之君。山河破碎似乎没有带来多少痛苦,皇家藏书的丢失才让他仰天长叹。爱妃被抢,被迫穿丧服,种种精神折磨之下,赵佶以泪洗面,颤抖着手写下几首哀婉的诗,有名的当然是这一首:“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如此的辞句立即让人记起了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和“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作为书法家,赵佶的名字是与“瘦金体”联系在一起的。“瘦金体”瘦劲爽利,笔法外露,锋如兰竹,原先当为“瘦筋”,因为是御笔而尊为“瘦金”。赵佶的大草千字文也极为流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是,龙飞凤舞之间的确浮动着柔媚飘逸之意而少一些沉郁顿挫。
古今的许多诗人慷慨悲歌,壮怀激烈,但是,如果手无缚鸡之力,种种豪言不过纸面上的书生之叹。那些崇尚铁血精神的人嘲讽地说,诗人那一份字斟句酌的工夫为什么不用于研习剑术?再多的诗文和书法也挡不住来自北方的铁蹄。一代天骄,只须弯弓射大雕。精致是脆弱的别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决定这个世界的是军事实力而不是各种华而不实的艺术才情。要粗犷而不要浅吟低唱,要简单而不要瞻前顾后,大块肉大碗酒,醉后血脉贲张,仰天大笑出门去,挥舞大刀砍人或者被人砍倒。生活如此明瞭,哪有必要如同诗人那样说一句话拐三个弯。诗人抛出的那些小感觉、小情调可能腐蚀心性,一腔愁绪、满腹牢骚的战士还怎么上战场?古希腊的柏拉图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要把那些诗人赶出理想国。诗人、书生、知识分子的痼疾即是,相信美、概念、哲理可以塑造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以残酷当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玉树临风的潇洒仅仅取悦眼睛,雄辩的滔滔宏论仅仅取悦耳朵,旷野之中走来一个莽汉一拳打翻在地,所有的故事立即结束。谓予不信,请看赵佶。不论这些言论是否公允,反正宋朝作为一个窝囊的形象耻辱地镶在历史的画框之中,再多的苏东坡或者朱熹也无济于事。
历史学家可以站在岸边的高地上说三道四,作为皇族的一个后人,赵范或许还意识到另一个隐秘的问题:为什么曾经生活在皇宫里的那些赵姓先辈似乎都有一些弱不禁风的意味?——无论体质还是精神。许多赵家的皇室成员体弱多病,夭折或者早逝,还有一个太子是精神病患者,放火烧了宫殿;尽管后宫的三千佳丽团团围住,好几个皇帝仍然没有子嗣,皇族的生殖力似乎低于平均数;他们当然位高权重,可是,不理政事者有之,优柔寡断者有之,孱弱无能者有之,耽于酒色者有之,一些皇帝迟迟无法摆脱太后的阴影,宋光宗赵惇居然被形容为历史上最为惧内的皇帝。赵范肯定想从这种形象之中突围,他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家长。当然,他没有三千里江山可供挥洒才华,他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赵家堡不到一平方公里。
站在小广场一眼就可以看见赵家堡西门附近的那一座瘦瘦的石塔。石塔共七级,据说是汴京铁塔的缩小版,高度为后者的十分之一。石塔东移几步即是两个莲花池,代表汴京的杨湖和潘湖。杨湖纪念的是忠臣杨家将的杨继业,湖水清澈;潘湖羞辱的是奸臣潘仁美,湖水混浊。当然,赵家堡两个莲花池的水质相近,时常有一队鸭子游弋水面,仿佛无忧无虑,不计宠辱。莲花池上的一座桥分为两段:一段是拱桥,另一段是平桥。拱桥弧度之大,以至于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竟然摇摇摆摆地走不下来。赵家堡唯恐人们想不起汴京“清明上河图”之中的虹桥,石桥上刻上了“汴派桥”三个字。赵家堡中央的五座府第按南宋临安凤凰山下的皇宫修建,每座五个院落,最后一个院落为二层,是内眷的居住之处,俗称梳妆楼,五座府第计有一百五十间房屋。赵家堡的主楼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土楼,名为“完璧楼”。“完璧归赵”的寓义显然比“黄”与“皇”的谐音深刻。“完璧楼”长二十米,共三层,上下的楼梯十分陡峭。“完璧楼”前放置了一个花岗岩匾,上刻明朝书法家张瑞图的行书“松竹村”三字,背面为隶书“硕山”。莲花池旁还有一块石碑,碑上镌刻“墨池”二字,号称米芾的手迹。当年米芾也曾经担任无为州的行政职务,夜间在衙门吟诗挥毫。衙门池塘里的青蛙不认识这一位书法大师,聒噪不止。一怒之下,米芾墨汁淋漓地写了个“止”字,裹在一方砚台上投进池塘,青蛙从此敛息噤声,池塘的水却逐渐黑如墨汁。于是,米芾又挥笔写下“墨池”二字刻在石碑之上。赵范在无为州任知府的时候见到这块石碑,他将“墨池”二字拓印带回。赵家堡这块“墨池”的石碑是赵义根据拓片重新镌刻的。不知两度转拓是否失落了什么,我觉得赵家堡石碑上的“墨池”二字似乎少了一些韵味。灿烂的宋朝已经海市蜃楼般地消失,赵范父子的一辈子心血只能复制若干汴京与临安的投影。
这些奇怪的建筑物之外,赵家堡没有别的故事。哪一个年代,是否有些秘密使者出入城门,密谋于“完璧楼”的某一间小屋子,然后,一只信鸽携带一个惊天计划向远方飞去?另一个年代,是否有些身轻如燕的武林高手越过城墙,潜入赵家堡,窃取某些机密文书或者在小广场大打出手?闲常的日子里,赵家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是否在空地上拉开架势,习武练功;或者卧薪尝胆,等待一个遽然而起的日子?没有任何可供想象的资料。“完璧楼”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孤伶伶地供奉着一柄锈迹斑斑的大刀,号称重80 斤。不知哪一个人挥舞过这一柄大刀,斩杀过哪些仇敌,总之,一无所有。
第二次到访赵家堡,我很迟才离开。暮霭沉沉,几个农民荷锄从田地里归来,尾随身后的黄牛哞地叫了一声。这些农民用古老的闽南方言大声寒暄,内容无非今年的雨水和秧苗的长势,他们还惦记着祖先的功绩吗?入夜之后,天上一轮清朗的孤月,赵家堡一排排屋檐翘起的房子犹如一片片剪影。几星灯火,三五声犬吠,四处寂静无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种寂静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不要想象还会遇到哪些特殊的人物,还有哪些奇异的情节等待发掘。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句撼动历史的大哉问。君临天下,“天子”是一个神奇的称呼,皇帝是天之骄子。然而,老天爷赐予的仅仅是机遇,而不是血脉。无德无能,血脉又能帮多少忙?皇宫里的赵宋一脉相承,直至陆秀夫背负赵昺跳海的那一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悲声四起,嗟叹无数,尽管如此,赵与宋之间缘分已尽,所有的故事不再续签。多少年之后,明朝的赵范可以在夜深人静之时反复重读家谱,一百遍地后悔,一千遍地扼腕长叹,但是,一件事情无可置疑:机遇不再。时过境迁,不会再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凑巧,不会再有当年的风云际会。
修建赵家堡当然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赵范父子迟早明白:光复无期——这些建筑物仅仅是若干泥土和石块垒成的缅怀符号。历史收容这些缅怀符号,但是,现实永不回返。维持族人的存活就是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目的。结局之后不会再有更多的结局。事实上,赵家堡可以卸下这一份负担了。可以笑谈古今,哪怕争论一下是非成败,但是,没有人再把自己的日子拧成一根紧绷的弦,夜不能寐,时刻背诵再造一个宋朝的神圣使命。春种秋收,捕鱼捉蟹,如此安居乐业的日子并没有亏欠什么。这时,我可以放心地安慰自己:面对一个宋朝的沙盘,找不到灵感就不必勉强了。
不久之前,一个熟人抽空到赵家堡走了一趟。回来之后,周围的朋友询问观感。他说不出什么特别的见闻,一圈城墙,几幢土楼而已。他想了想补充说,那儿的土鸡蛋不错,他买了好几斤。赵家堡与土鸡蛋?我诧异了片刻,转念一想,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