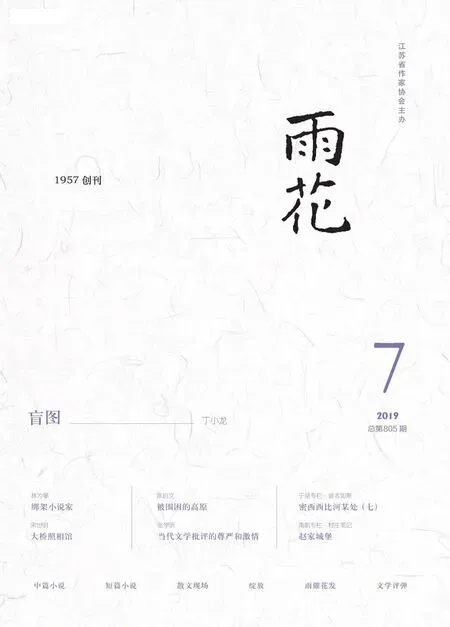谁的钟表坏了?
——读范小青短篇小说《现在几点了》
子 川
现在几点了?寻常语境一句寻常问话,被提溜起来做了小说题目,竟生发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张力。2019年第1 期《雨花》杂志尚未寄至家中,我就在主编朱辉的微信上读了小说《现在几点了》的电子版。线上匆匆读过,通过微信转给了几个文友,事情似乎还没做完,就又把小说下载到电脑,用WORD 文档打开,再细读一遍。小说的故事看似简单,读了却有点化不开。真所谓篇制不长,张力不小。
小说用“现在几点了”这句话做引子:
“老人坐了下来,手臂搁在桌子上,她以为他要开始诉说自己的病情,等了一会儿,老人说了一句,现在几点了?”
“她回答的时候,看了老人一眼,她是有经验的,所以已经有了一点预感。果然,老人又说,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明明是一个关于时间刻度的问题。梅新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却“基本判断出来了,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提问,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阿尔茨海默症。”梅新医生以确诊口吻表述老人的症兆。确实,阿尔茨海默症会导致病人出现时间定向障碍。“老人指着自己的胸口,明天我这里有点闷。”“前天会不会下雨。”很显然,“时间概念已经完全混淆或者丢失了,”根据医生梅新的判断:“这至少是到了中期的病症了。”
小说开始于对时间刻度的询问,然后又通过提问者的“阿尔茨海默症”消解了询问的意义项。然而,时间作为小说揭示的主题,却始终在小说情节线中显现,带着一些不太明晰的意义项。
“老人皱着眉,十分焦虑地说,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了。”一个八十岁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有此症兆,不奇怪。在语义项层面,“没有时间了”符合一个八十岁老人的逻辑。
接下来,护士小金也为时间纠结:“她们正说着话,小金的手机响了,小金一看来电,还没接电话就叫嚷起来,哎哎呀,我差点忘了——哎呀呀,现在几点了?”
这还不算,小说中轮番出场的人物,几乎都在时间节点上打绊儿:
“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个面带怒气的中年男人,他正在嚷嚷,医生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跑到外面瞎聊天,浪费我们时——”
“她赶紧说,让我先看吧,我马上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哇啦哇啦哇啦——我时间来不及了——”
“那妇女说,你不是心疼时间吗,你要是死了,时间就全没了——她忽然叫喊了起来,啊呀,现在几点了?啊呀呀,我不量血压了,我来不及了!”
“周医生很懊恼,一直说,怪我,怪我,那天我约了要去看房,时间太急了,我没有仔细看,我那天时间来不及了,我要是时间来得及,不会这样粗心的。”
“老太太在旁边嘀咕说,你这样的,不用来麻烦医生,自己到药店拿医保卡就可以了,来医院还耽误别人的时间。”
小说读到这里,才知道原来作者想说的并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或者,“阿尔茨海默症”只是一个影子。影子周遭,渗透的全是时间,时间。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环境下,时间,时间。仿佛冬日危机,四处呈现。
汉斯·梅耶霍夫曾经说过:“问人是什么,永远等于问时间是什么。”(《文学中之时间》)的确,生命在时间中展开,生命其实是一些不同的时间刻度,而且是一些可以消耗殆尽的刻度。小说中的“现在几点了”,不再是一句简单问话,它似乎还多出几个意义项:时间不多,已进入临界状态;时间所剩无几,再不什么什么就要来不及;一种与时间相关的焦虑普遍存在着。
如果用四季划分生命的时间刻度,冬日应是生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现在几点了?在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里,语义层面无意义,但在生命周期上,这一提问的潜在意识却是对所剩无几的时间的焦虑。
因此,一个小说未提及的字词出现了:时间焦虑。小说中这样一些对话,让人时时感受到这种焦虑:
“老师说,喔哟,张阿爹你急得来,急着去上班啊?”
“张阿爹虽然咳得厉害,嘴巴仍然蛮凶,说,难道不上班的人,就不要时间了吗?”
“老师说,好了好了,不和你说时间了,人都这么老了,还时间时间的——”
“脾气不好的男人又不高兴了,说,你时间来不及?就你忙?现在谁不忙?再忙也有个先来后到,不要不讲规矩。”
再看看这组对话:
“梅新说,那个,她急着量血压,要去赶车?”
“赶个魂车,赶火葬场的车吧——她要买彩票。”
“咳嗽的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还忍不住插嘴说,买彩票急什么急呀,到晚上也可以买的。”
结论是:“她们都觉得自己的时间很紧。”
梅新医生之所以从大医院降职到社区医院,也与时间有关。她要去接外地过来的妹妹,而她先生的时间概念有瑕疵,据她估算“妹妹大约八点二十左右到达地铁出口。可时间已经八点十分,丈夫居然还没有出门,”于是,她只好自己请假去接人,而偏偏这个时间里,出了医疗事故。小说写到“丈夫的手机里却传过来电视机里的声音,丈夫‘咦’了一声,随口说,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在这个短篇小说中被不同的人重复使用。
小说中,时间焦虑并非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单一症候,当小说中的人和事,都与时间挂上钩,时间焦虑似乎已经是一个全民性症候。于是,小说并未提及的似乎是全民性的时间焦虑症,显现在读者眼前,在读者心中引起震撼。
这病始发何时?病根是什么?小说家没有说。小说家不是医生,虽然她写到了医生与病人。这里留有大片空白。这里的空白由读者自己去填写。
笔者在读小说时,突然闪回幼年的生活。那时,大人们经常“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轻轻松松谋生活。如果要说当时的人不如今天的人进取,似乎也不让人信服。别人且不说,仅我父亲早年也就是做个三分利的小生意,竟可为八个子女盖下八处房产,用时下流行语去形容,还真是够拼的。可他依旧能痴迷于琴棋书画,悠哉游哉过日脚。后来,时代所迫,琴棋书画玩不起来,他干脆给我二哥四个小孩起名:张琴张棋张书张画。回忆起来,当年并非他一个人如此,印象中,街坊邻居,大都这样从容、写意地生活着。
为何到后来就一个个活得疲于奔命了?不好深究。应当还不是所谓“现代化并发症”,与现代不现代似乎毫无关系。去国外旅行,看瑞士、丹麦、芬兰这些国家,周末商场无一例外关门打烊。街面上,许多地方看不到人,唯有咖啡馆、休闲场所满座。时间上,这些国外人群与我们同处一个刻度,空间上,我们前人与我们同处一个纬度,为何他们都能很悠闲地生活,我们就不能?
难道真是我们记载时间刻度的钟表出了问题?
小说安排了两个似梦非梦的梦境,来讨论钟表。应当说这是小说最值得注意的细节。
“老人重新坐到了梅新的桌子前面,跟梅新说,医生,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坏了,时间找不到了……”这似乎是写实。只是后来,“老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塞到梅新手里,说,时间在这里。”让人觉得有点梦幻。再后来,“梅新正想把那个奇怪的纸单掏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就听到有人咳嗽了一声,把她惊醒了。”
“原来是个梦。”却好像又非梦。
一个周末,在家里整理衣物的梅新,无意中在很久未穿的旧衣服口袋里发现“一张修理钟表的取货单,上面有钟表店的店名和地址:梅林钟表行——梅长镇梅里街十一号。”
“她想起了那天中午的那个梦,这明明是梦里的一张纸单,怎么会真的出现在口袋里?”
接下来是梅新回家乡梅长镇,去看望父亲,去找梅林钟表行。“正如她所猜测,梅里街已经不是原先的梅里街了,虽然门牌号还都在,但是十一号不再是钟表店,而是梅里街居委会。”
遇到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钟表行所在。有一个大叔似乎认识她,但一说话她又觉得不对,“那大叔说,好久没见你回来了,好像你父亲去世以后,你就没有回来过?”
“梅新忽然意识到,这大概又是一个梦,梦是荒诞的,她应该从梦中醒来。”
其实,似梦非梦只是想用一种模糊方式来表达:表坏了。表坏了,没有修好或修好了没能取回。
什么表坏了?这让人们在时间面前变得不那么对付。而事实上人的生命始终与时间相关,时间刻度不对,人的生存质量与生活品味就都出了问题。
或许与社会价值取向有关。记得当年有一个豪迈口号:“超英赶美”。这对中国人影响极大,对我个人也如此,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这代人都有“跃进”情结。到了新时期,许多东西都回拨了不少,唯独这“跃进”劲头丝毫不减,只不过“跃进”方向与指向的内容有不同。这时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间与金钱,效率与生命,划上等号,等号后的答案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这些历史背景或许与今天的时间焦虑有点关系,应当还不是病根。病根应该出在文化上。如同自然植被被破坏会造成沙尘暴与雾霾,文化植被遭到破坏,社会环境自然就出现若干的文化症候。时间焦虑是其中一种。
有一个叫俞敏洪的大V 说:焦虑的根本原因,是你守不住自己的节奏,太急于收到回报,看到改变。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在于,他把全部看成了个别。如果是一个人的焦虑或一部分人的焦虑,他可以这么说,一旦所有人都焦虑,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显然,文化问题这口子不能开,说透了需要著一本大书。不过,从前人的价值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端倪。
那么,文化上的问题又出在哪里?《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管子的“四民”划分,与后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样,都是在价值取向上向务虚层面倾斜。为何把最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商”排在末位?为什么要去强调“百无一用”的读书人?这里其实有一个精神高于物质的价值本旨。而这本旨始于“以人为本”的理念。的确,人如果没有精神了,人还是人吗?
以人为本,还是以别的什么为本,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还是《管子》,“霸言”篇中,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有这么一段言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格和个性的发展。古人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于是我们在能读到的几乎所有历史典籍中,读不到“商”人什么事,包括那些挣快钱的人,工于应用的那些人。不能说社会发展与进步与他们没有关系,但最终,钱与物质都是生命的附加值,人的尊严、人格和个性才是价值本身。今天社会价值取向怎样(不展开评说)只看所谓“上流社会”有多少老板即知。这里可以把大V 的话用在这里:“太急于收到回报,看到改变。”当价值取向倾斜于物质至上,人们怎么能不急功近利?因此,别太强调致用,男女老少,都务点虚行不行?
事实上,人的尊严和价值,人格和个性发展,都不是金钱所能换取。当“一切向钱看”了,当“时间就是金钱”了,确实有一个钟表坏掉了。“现在几点了?”是小说中的提问,小说外也有一个令人心颤的疑问:“谁的表坏了?”
还是回到小说。根据医生梅新的判断:“这至少是到了中期的病症了。”
还是那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老人重新坐到了梅新的桌子前面,跟梅新说,医生,现在几点了?……你能不能帮我修修表。”
医生,能不能帮我们修修表!
——一个解释欧姆表刻度不均匀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