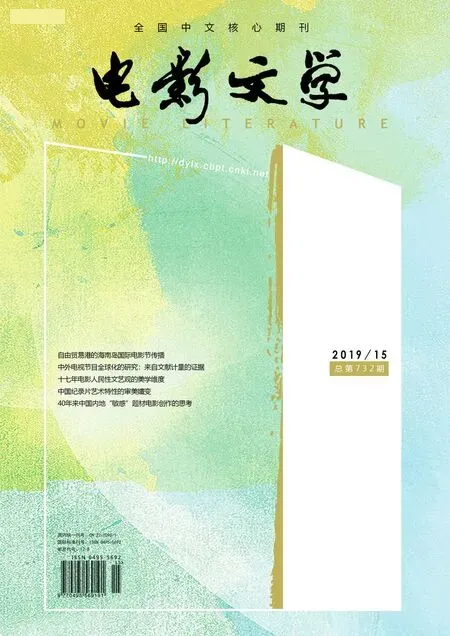迪士尼动画电影的伦理诉求
——以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的迪士尼影片为例
盛开莉(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迪士尼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凭借着他自己“美国式”的勇气与才智,开始将欧洲童话占为己有。“迪士尼的签名模糊了查尔斯·贝洛、格林兄弟、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夏尔·佩罗这些名字。”[1]迪士尼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启,文字在童话文类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动画电影而发生转变。迪士尼总是能抓住童话的文化缰绳,改变着人们看待童话的方式,通过图像,动画制作者们占有了文学的与口传的童话。迪士尼电影在占有文学童话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面是迪士尼将文学经典拿来作为“美国制造”的原料和工具;一面则是文学经典对迪士尼动画电影进行的基因植入。在电影这个不再依赖文字的叙事场域,那些童话文本中由文字铸就的精魂——不朽的道德力量与永恒的伦理价值,并不会丧失,反而被迪士尼电影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从伦理精神的层面出发,对安徒生童话改编的两部迪士尼电影《小美人鱼》《冰雪奇缘》进行考察,可见其伦理诉求也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影片的伦理诉求也受到了安徒生童话的伦理意识的深刻影响。
一、代际冲突与家庭伦理
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运用来自古老神话的变形母题,将从兽到人的形态变化与人类的成长紧密联系起来。小人鱼从兽到人,从海洋到陆地,从形体到生活空间的变化,体现出从自然到文明的进阶:隐喻着人的成长是一种“上升”的过程,亦即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阶梯式发展。在欧洲古老的神话中,美人鱼同塞壬一样,常以动听的歌声和美妙的竖琴声对海员施加魔法,把落水的海员引诱到海底。“教堂把她作为恫吓人的象征。因为美人鱼代表了诱惑和死亡。”[2]安徒生的小人鱼身上没有了传统水中精灵代表诱惑和死亡的妖魅气息。当王子乘坐的船向海的深处下沉的时候,她奋不顾身地游过去救了王子。这种利他的、道德化的选择,已经显示出小人鱼不同于其他兽类的伦理意识。随后,小人鱼以失去美妙的声音为代价,获得了人类的双腿,这看上去是一次生物性的选择——从兽的形体变为人的形体。实际上却是一次伦理选择。美妙的声音代表着人鱼极具诱惑性的一面,隐喻和象征了代表本能欲望的兽性因子。安徒生赋予成长以伦理意义,“成长意味着形成伦理意识并以伦理意识约束自然本能,使行为符合社会伦理规范”。[3]36小人鱼基于对灵魂(善)的渴望,为使其行为符合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用伦理意识克服原欲:放弃了人鱼美妙的声音。小人鱼在自觉的伦理选择中,逐渐地具备了获得人类灵魂的资格。
安徒生通过小人鱼的故事,意在引导儿童读者的伦理行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从而完成从天真本能向文明过渡的成长过程。迪士尼从家庭入手,将原作中的关涉儿童成长的伦理意义,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识的转换,将伦理焦点转向代际冲突与家庭伦理责任,使得影片具有了新的伦理意义。迪士尼动画《小美人鱼》在沿袭安徒生的变形故事的基础上,依照迪士尼的趣味和公式,强化了巫婆的邪恶力量,通过善战胜恶的线索,安排小人鱼和王子达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婚配,在善恶对垒之时,将原作中缺位的父亲置于核心位置。由此,安徒生笔下人鱼追求人类灵魂的故事,转变为家庭代际冲突的故事:叛逆少女与专断父亲之间的对峙与和解。
家庭是儿童成长中开启伦理意识、进行伦理认知的第一站。家庭作为一个伦理精神实体,其中的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成为一个人一生中的伦理出发点。影片把小人鱼三代同堂、祖母管家的主干家庭变为了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几乎是现代西方世界最主流的家庭结构,即父母和孩子,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导致家庭与个人主体地位的转变,在传统的主干家庭中,人皆以“家庭人”立足,而新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伦理则更加强调自我,追求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与自我的享受。主干家庭奉行传统的代际伦理,更重视前代,在代际的责任上更强调子代对父代的顺从与尊重。安徒生笔下的小人鱼,始终悉心遵从祖母的权威,即便对人间世界充满了渴望,可还是得等到祖母许可,才敢浮出海面。成年礼上,小人鱼即便厌恶祖母为她装扮的沉重饰品,也还是选择了遵从。小人鱼沉静、内省,以至于所有的愿望都暗中酝酿,与家庭中的长者并无对抗和冲突。
迪士尼的小美人鱼没有了安徒生赋予的沉静与内敛,更多追求精神自由、个体独立的一面,对于自己不被允许的梦想,她也毫无隐瞒地企图。父亲对人类世界毫无好感,满怀敌意。小人鱼却对人类世界充满了渴望,父女截然不同的好恶构成了尖锐的代际冲突。影片中的川顿国王因为小人鱼的忤逆不尊,大发雷霆,摧毁了小人鱼的人间世界收藏品。小人鱼对人间世界的向往,以代际冲突的形式被表达出来。
代际冲突是两代人之间由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引起的对立与矛盾。相对于原作中的遵从,影片中的主人公一直在挑战父亲的禁令。女儿代表着追求代际公平的年青一代,相比于“家庭人”的传统角色,她更加看重自我实现、自我享受。而海王为代表的父亲则是传统代际伦理思想的体认者,他以“家庭人”立足,重视代际责任。海王颁布的家庭禁令,在小人鱼那里,是家长专断的象征,它可能阻断小人鱼的个人梦想,可能使其牺牲个人享受。代际冲突的根源在于两代人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念:父代被传统代际伦理思想所束缚、习惯将人看作“家庭人”,更看重人对家庭所尽的义务;子代则在家庭关系中遵循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将个人的幸福看作最高理想。
影片中,小人鱼在追求代际公平的过程中,以叛逆的姿态进行冒险,因为轻信与无知,将自己置于险境。以代际责任为宗旨的海王,在女儿安危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他”行为:交出了自己的神杖,甚至被巫婆囚禁。获救后的海王又从尊重对方主体性出发,用神杖赐予小人鱼人类的双腿,许可了她和王子的婚姻。海王所体现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种崇高的人类情感,达到了完全无私的高度。海王无时无刻不在捍卫家庭——这个伦理精神实体。相形之下,小人鱼在整个追求过程中,由于看重自我实现,更多利己主义,对于家庭代际责任却少有考虑。影片将西方文化看重个体的独立与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家庭代际责任与义务之间产生的伦理冲突,以定点聚焦的方式凸显了出来,显示出迪士尼动画的现代伦理诉求。现代主干家庭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日益凸显,影片通过强化表面专断、实则慈悲的父亲形象,树立了承担代际责任、具有利他情怀的家庭伦理观念。黑格尔曾经说过:“伦理是现实的或活的善,它通过人的知识和行动得以体现出来,而成为现实的或活的。”[4]影片实现了家庭伦理的强大教诲功能:引导儿童接受利他的、善的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面临代际冲突时,以家庭伦理意识引导人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电影将主人公的邻里关系变成了姐妹关系。由此将故事的发生场域放置在了“家庭”当中。“家庭具有伦理象征意义。它们既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类具有伦理尊严的基本标志。”[5]事实上,父母亡故后,家已经成为她们获得安全感、尊严感的最后堡垒。姐妹俩从离家到归家,家由残损到复原,才是故事的核心表达。一个本来完满的核心家庭,先是遭遇了父母的突然离世,随后又是艾莎在加冕仪式之后的逃离,安娜为了追寻姐姐而离开,当家中成员纷纷离开之时,也是家庭分崩离析之际。一个眼看要倾覆和溃散的家庭,最终还是依靠姐妹亲情,由善维系着的亲情伦理,转危为安。从亲密和谐的姐妹关系,到渐生嫌隙,乃至剧烈的矛盾冲突,最终因为来自外界的对“家”的威胁而和解。这个没有父母存在的姐妹之家,经由磨难的考验,最终走向了加倍的稳固。儿童的成长,本就是由“自然状态”走向“社会化状态”的过程,家庭必然承担起一个伦理精神实体的责任,通过影片的伦理选择,逐步引导儿童认识和形成家庭伦理观念,学会承担伦理责任,对于现代家庭的亲子关系的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冒险旅行与道德完善
表面上,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与安徒生原作《白雪皇后》存在较大差异。主人公的性别、身份、相互间的关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在差异重重的皮相之下,影片的伦理诉求却深深植根于原作中关涉成长的伦理意义之中。
安徒生童话中有大量旅行故事,以主人公的出走和冒险为基本模式,《白雪皇后》正属此类。坎贝尔将神话中英雄的成长过程总结为出走、启蒙、归来。[6]事实上,这也是大量民间故事和童话中常见的情节模式。对未成年主人公而言,旅程成为成长仪式的象征。《白雪皇后》里的小格尔达为了寻找加伊,踏上了冒险旅程。安徒生冒着让情节无限拖沓的危险,为小格尔达布置了一个又一个与寻找加伊关系不大的关卡。从“会变魔术的女人的花园”到“王子和公主”,再到“小强盗女孩”,一路所遇对于天真的小格尔达来说,充满启悟。她遇到花儿给她解释“爱”,王子让她明白“利他的爱”,小强盗女孩和驯鹿让她明白友谊。“在旅行故事中,安徒生表现善的信念在对抗恶的过程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引导儿童以仁爱的原则和道德勇气在面对困境时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3]97格尔达是一个幼弱的孩子,却在极端残酷(冰天雪地)的外界环境中,孤身跋涉,找到加伊,并使其获救。她没有依凭外界的神奇力量,而是靠着强大的道德力量完成了救赎的任务:代表真挚情感的热泪融化了加伊被恶冰封的心。回到家的时刻,“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这场离家之旅,呈现了善恶共存的复杂伦理状况,通过旅行,他们开始辨识现实社会中的善恶,具备了关于善恶的伦理意识,从而成长为伦理意义上的人。
电影基本情节遵循了“出走—归来”的模式,即通过“冒险旅行”获得成长启悟的情节类型;来自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物内心的重重考验,成为主人公不可知的旅途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与小格尔达和加伊相对照,电影中的主人公安娜与艾莎也都经历了离家冒险的旅途。并且均属一个主人公被某种“恶”挟持,另一个想要去寻找对方。加伊的出走,是受到了白雪皇后的蛊惑,被恶所挟持。艾莎的出走则是因为自身拥有的难以控制的冰雪魔法。而安娜和格尔达的离家则是主动选择,都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对方。
由于影片对白雪皇后形象的隐匿和再造,安徒生笔下关涉成长的伦理意义在艾莎这个人物角色中得到有力彰显。影片中没有了《白雪皇后》里构建正邪关系的邪恶代表——白雪皇后,可这种邪恶力量却以冰雪魔法的形式隐藏在艾莎身体里。在《白雪皇后》中,白雪皇后和她的冰雪魔法浑然一体,和谐共存,因为对人类而言,白雪皇后本身就代表了邪恶的异己力量。而在艾莎身上,魔法与自身却有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深刻矛盾,这转化为艾莎对自身魔法的深深恐惧。幼年的艾莎,因魔法而伤害了妹妹,这是她无法控制魔法的后果。这种不可控带来的恐惧加深了她的矛盾,为她加冕之时和妹妹产生争吵,负气出走,任由魔法控制自己,埋下了伏笔。
“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7]5人性因子可以通过伦理选择得到强化,进而控制兽性因子。而兽性因子作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无法通过后天选择彻底去除的。艾莎天生拥有冰雪魔法,意味着魔法并非后天选择,这是她自己无力去除的。冰雪魔法正好象征了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7]6展现人性因子如何与兽性因子搏斗,进而成长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是艾莎形象的意义所在。冰雪魔法象征了艾莎身上自由意志即兽性因子,成为“好女孩”“好女王”则代表了与之搏斗的人性因子。因为要做“好女孩”,艾莎才对自身的魔法产生深深的恐惧。要做“好女王”,她才戴上了隐藏魔法的手套,战战兢兢地参加了加冕仪式。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艾莎角色的核心。
除了结尾和开头,剧中的艾莎始终表现为焦灼与紧张。这种紧张皆源于自身的斯芬克斯因子的搏斗与冲突。代表邪恶力量的魔法,在大量的童话文本中,都只属于女巫。正面女主人公,亦即“好女孩”,根本不会拥有。一边是好女孩,一边是巫婆才有的魔法,不断撕扯着自己,成为艾莎难以自处的关键。两种因子的此消彼长,导致了艾莎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从而形成伦理冲突,表现出道德教诲价值。“好女孩”(理性意志)占上风的艾莎,沉静内敛,理智又克制。魔法(自由意志)出笼时的艾莎,疯狂而暴力。在经历了磨难和考验后,“好女王”归来,冰封之城阿伦戴尔春回大地,象征了她理性意志的回归,控制了自由意志。此时,冰雪魔法并未消失,而是成为理性可以驾驭和控制的,对女王的魅力反而是锦上添花。
安徒生童话中的白雪皇后作为恶的象征,成为小格尔达和加伊成长路上的考验。白雪皇后用恶助推了孩子的成长,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伦理意味。只有经历了恶的考验,用爱和善战胜恶,才能成长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白雪皇后用恶之面孔,完成了善举。迪士尼改编让白雪皇后以冰雪魔法的形式寄生于艾莎之身,使得原先人与外界的正邪之争演化为人自身、内部世界的激烈战争。更好演示了斯芬克斯因子在人身上的此消彼长。艾莎是一个道德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一种劝诫和教诲的力量。这是对原作伦理价值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道德教诲价值:人要成长为真正的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不仅需要战胜来自外界的恶,更重要的是控制自己内心的恶。
安娜形象和格尔达的最大接续性在于二人共有的“天真”。保有天真固然可贵,但“天真”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辨识善恶的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辨识善恶、从自然向社会过渡的过程。比之艾莎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内心风暴,亦即人与自我的战争;安娜经历的则是人面对自身以外的对象世界时,怎样认识善恶,进而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成长为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影片沿袭原作中安徒生对冰雪酷寒的着力刻画,将自然的形象作为安娜冒险旅途上的重要风景。安徒生对冰雪力量和严寒的描绘,使得自然成为锤炼人的道德意志的场所,电影则通过对自然的展示显示了冒险旅程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交织着安娜所经历的伤害与被伤害、真挚友谊与“虚伪爱情”等需要通过亲身体验才可以得到鉴别和收获的宝贵经验和认识。
尽管安娜旅途上邂逅的克里斯托夫、驯鹿以及雪宝,都因为迪士尼元素而变得喜剧化,影片依然将真善美作为冒险旅程的目标,与安徒生童话保持了一样的伦理诉求。旅行是“促进人性因子一伦理意识——发展变化的契机”,[3]80通过一场旅行,在亲身体验中形成伦理意识,成长为伦理意义上的人。这是安娜和小格尔达形象所传递的相同伦理意义。
迪士尼虽然以全新的方式占有了安徒生童话,但作为文学经典,其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却在迪士尼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迪士尼让安徒生童话的伦理价值得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同时也通过巧妙的借鉴与改装,重新构建了自身的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