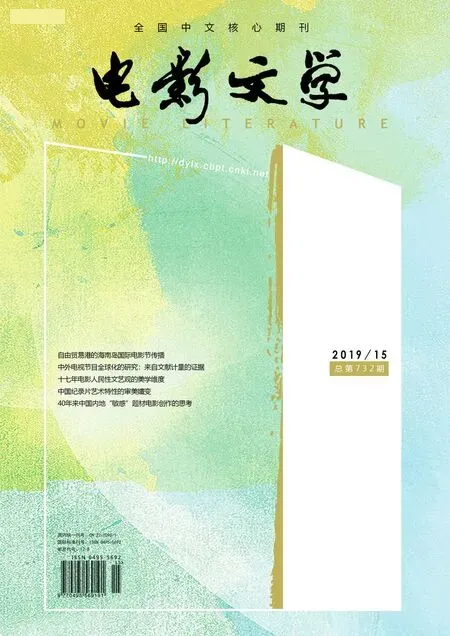电影民俗学视野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
沈 鲁 吴 迪(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民俗叙事,在文化“消费升级”的当下,越发凸显其不被现代化驯服的力量。细察电影创作中的民俗叙事,发现电影创作者透过民俗讲述中国故事、找寻中国文化过程中大抵呈现出三种视角:一是以启蒙的姿态,通过现代理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期盼人性的回归;二是重在关注民间市井生活,试图呈现中国民间社会景象与问题;三是引入人类学理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俗,重在关注各类民俗事象,肯定民俗文化的价值,希图在“固有血脉”和“历史惰性”之间寻回传统文化。这三种视角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其时的社会时代背景状况,如今,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下,回头审视电影民俗叙事的这三种视角,以民俗叙事反抗“视觉快感”,对“讲好中国故事”策略的提出有所帮助。
一、对民俗的“他者化”表现
(东方)“他者”出自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与(西方)“自我”相对的存在,强调的是客体、异己特质。当“他者”与“主体”逐步被区分,“主体”不断被确立,催生了“他者化”现象,即西方为确立自我中心价值,树立自我支配地位而贬低、丑化异质(东方)文化的行为;相反,中国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他者化”是将(东方)“自我”塑造成(西方)“他者”更易接受的形象的行为。
张艺谋是电影民俗叙事中以启蒙姿态创作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引领下,“新民俗电影”驱赶“文革”阴霾,重铸国人灵魂,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他以“以意臆志”的创作态度,对民俗做出艺术化创造处理,将糟粕的封建民俗影像化,试图唤醒沉睡已久的人性。《黄土地》被西方意外“发现”后,张艺谋开始琢磨如何“取悦”西方,《红高粱》尚且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崇拜赢得了国内外的美誉,《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却将残暴的“民族劣根性”表露无遗。尽管学者王一川曾经较为客观地指出:“在《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中描绘的原始情调,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唤起了原始中国的真实感。”这些影片代表着正宗的“中国”形象,但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认真审视张艺谋电影中对民俗“他者化”的叙事表达,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民俗奇观演绎的并不是中国人的常态,而是能够唤起西方认同的被“他者化”了的东方想象。影片对古老/原始/愚昧/野蛮/专制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塑造,对裹脚/长辫/深宅大院等丑陋的中国意象的表现,对宗族斗争/乱伦野合等野蛮行为的呈现,是最能吸引西方人的地方。但是一味揣测西方的结果就是“自我”被“他者”所遮蔽。2017年《长城》再一次呈现出对民俗的极端“他者化”,“长城”是中国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张艺谋似乎只是借用了长城的躯壳讲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拯救故事:为抵御饕餮建筑的长城不堪一击,若没有两个白人雇佣军的舍身相助,长城军团根本无法击溃饕餮,中国也无法得救。影片故事内核与中国毫无关系,片中巍峨的万里长城、中国神兽饕餮、高亢的秦腔“秦时明月汉时关”、孔明灯、火药和指南针还有中国传统兵法的排兵布阵在整个故事中都不过是为满足西方人胃口的“饕餮盛宴”,只有一再用言语强调的“信任”是中国集体主义的象征。
显然,张艺谋对民俗的“他者化”偏向极端,同样对民俗进行“他者化”的导演李安并没有和张艺谋一样放大民俗事象中的神秘因子去迎合西方“他者”对东方“自我”的想象,而是将民俗安置于西方语境中,从“他者化”的视角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电影语言诠释中国文化。他的“家庭三部曲”也被叫作“父亲三部曲”,三部影片中的“父亲”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大量的中华传统民俗事象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人伦道德的深刻命题。《推手》里的中国书法、太极拳、京剧文化;《喜宴》中的红包、旗袍、闹洞房;《饮食男女》中的大量饮食民俗都非常好地糅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国式家庭”这一耐人寻味的深刻命题,体现出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与人文关怀。“一方面抛弃了后殖民心理带来的民族虚无和模糊传统文化身份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又消解了民族性的凸显张扬,从此面貌中走向了与西方的平等对话。”
讲好中国故事是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中国故事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现实的,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但是一定要能够展现中国文化精神。我们不能否认张艺谋电影极高的美学价值,但是他电影中极端他者化的民俗叙事不符合现下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要求,我们不妨借鉴李安导演中对民俗的“他者化”表现,站在“他者”视角凝视本族文化,找到中国民俗文化中与国际价值观的“重合点”,将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呈现出来。
二、对民俗的“市井化”言说
继张艺谋们的“新民俗电影”之后,第六代导演同样表现出对民俗叙事的浓厚兴趣,也就是“城市民俗”。例如,冯小刚的“贺岁片”充满了京味儿,贾樟柯的山西电影描写了汾阳县城民俗,娄烨的电影也让人领略了上海的市井文化……总的来看,电影中的“市井化”民俗叙事大抵体现为以下三种状态:
一是电影中体现了较强的市民意识、世俗情怀。以往电影的民俗叙事多是寄托了某种文化因子,这些电影着眼于“市井”,表现着老百姓在时代大变革中的真实状态;二是市井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成为电影的表达对象。这些电影大多将城市底层人物作为主人公,围绕着他们的市井生活展开故事。《三峡好人》里的煤矿工和女护士,《站台》中汾阳县文工团的年轻人,《推拿》里的盲人按摩工,《甲方乙方》的自由职业者……三是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对白。贾樟柯电影里的汾阳方言、冯小刚电影中的老北京腔调等。
抛开艺术形式不说,电影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的艺术。国际评委在阐释贾樟柯电影获奖理由时,无不是认为他的电影通过对中国(人)市井生活的描述展现了一种普世的人的情感。他自己也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为了表现这样的电影母题,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处处都渗透着民俗情感的山西汾阳县城,通过对山西市井生活的展示来达到他的目的。电影里的人物最朴实的山西方言,汾阳县城的特色民居,山西特色的刀削面、猪头肉、饺子,等等。当然,贾樟柯电影在对民俗的“市井化”言说表达了对普通人关怀的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另外一种影像化书写。正如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列斯所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变化,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贾樟柯这么深刻地反映出这种变化。”
同样,冯小刚也认为一部影片哪怕是喜剧,它的魂还是要“扣在普通人的梦想、普通人的烦恼上”。所以,他将“老北京”作为镜像底色,表现着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市井生活。从《甲方乙方》到后来的《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碗》《手机》再到《老炮儿》,北京方言“京片子”的调侃/揶揄/插科打诨以及从相声/评书/戏曲/杂耍中汲取的“京味诙谐”,不仅是北京市井文化“油”与“贫”的表现,同时也将其时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包装成城市民俗故事,在喜剧的装点下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状态的思考及对人类情感的体悟与定位。例如,金钱对人的诱惑与异化,社会道德诚信的沦丧。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形成于时代文化思潮变迁与中国电影体制转型,将北京城市市井民俗作为影片的叙事轨道,为处于转型社会中迷茫而失落的国内观众找到一条“回家”的路,满足了他们对冷漠的社会人情的表达需要。
三、对民俗的“挽歌式”描写
不少民俗在现代化浪潮中濒临消失,影视人类学家们拿起摄影机将它们记录下来,也有不少导演将镜头聚焦于此,以艺术化的影像世界展现正在“失落”的民俗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艺术是用来阐释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价值观而精心制作的产物。电影如此,民俗艺术亦是如此。
吴天明导演在电影《变脸》中讲述了一个身怀变脸绝技的民间艺人只身漂泊于江湖,面临绝技失传、香火难再续双重危机,寻找下一代传人传承“变脸”的故事。中国民俗艺术大部分都受到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有着“传男不传女”的不成文规定,变脸王也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是,狗娃面对变脸王“女娃无用”的观点时,“观音菩萨也是女的,何以你要去信她,求她?”的反驳以及影片最后变脸王把绝活传给狗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同时,这样的故事结局也给民俗艺术的发展开拓出一条出路。导演在表现对四川变脸民俗艺术的热忱和对民俗艺术传承出路思考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民俗价值及其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
2017年,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上映,这部同样是以曾盛行于民间的唢呐艺术为红线的影片,反映了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唢呐民俗的日渐式微、悄然隐退。曾“跪倒一片孝子孝孙”的“百鸟朝凤”,所承担“红白喜事”及“娱乐解闷”等功能,构建了乡村人际关系,维系着村民共同的感情和价值体系。但面对新文化的进入,除了师父焦三和游天鸣,其他唢呐匠也选择逃离奔向现代化都市的怀抱。“影片表面上是在讲民间唢呐技艺遭遇到的现代冲击,但根本上,当然是用唢呐来连带整个传统的乡村伦理体系,从师徒关系、夫妻关系到婚丧礼仪、典章制度,唢呐的衰弱是整个传统文化衰弱的象征。”虽然说,影片叙事结构并未尽如人意,但是这样的民俗叙事策略依旧是达到了警醒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的目的。
在吴天明的电影中,正是因为他放弃了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以平视关照的视角,在对民俗进行挽歌式描写的同时体现了导演对民俗艺术的热忱、对民间艺人遭遇的同情,对日渐式微民俗艺术何去何从的担忧以及对社会时代状况的思考,才使得传统民俗的灵魂在虚构的电影故事中得以重生。在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的电影中,采取吴天明导演的这种通过对民俗的“挽歌式”描写策略,让国内观众了解到原来国家还有这些民俗,原来有些民俗正濒临灭绝,也让国外观众看到中国更多的优秀民俗文化和国人对这些民俗文化的挽留。
四、结 语
民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积淀。走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民俗成为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存在。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下,民俗叙事可以说是为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快速、准确、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