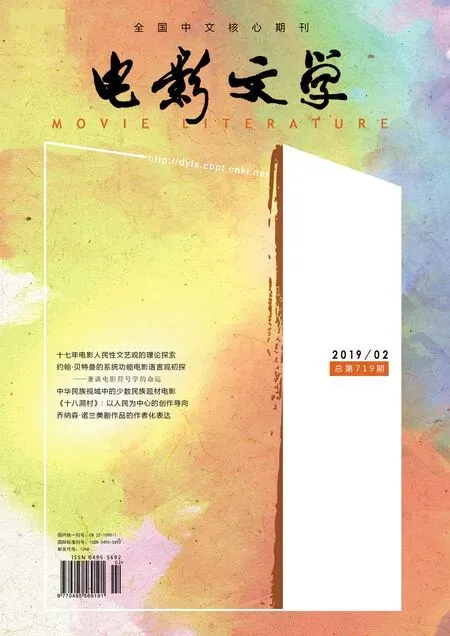当下国产犯罪片的类型建构与话语表达
高瑞利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50)
众所周知,犯罪类型影像善于以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为核心编织犯罪故事,反映现代文明病症,描画人性之复杂多元。尤其是在好莱坞电影中,犯罪类型构成了庞大的影像谱系。“它以现代都市文明为语境,并以犯罪片为基本类型,向上衍生自荒原和小镇背景下的西部片,向下则涵盖了黑帮片、警匪片、抢劫片、警察办案片(police procedure)等多种亚类型,也常与惊险悬疑或侦探及神秘片等各种类型相交叠。”[1]不过在中国,囿于社会发展程度与意识形态制约等因素,犯罪片一直处于较为匮乏的境地,长期盘踞场域中的是表现国家机器与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反特片/公安片/警匪片。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与类型化叙事的不断成熟,好莱坞、中国香港尤其是韩国犯罪片创制经验被不断吸收与借鉴,中国内地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类型意义的犯罪片。诸如《天注定》(2013)、《白日焰火》(2013)、《心迷宫》(2014)、《解救吾先生》(2015)、《黑处有什么》(2015)、《烈日灼心》(2015)、《追凶者也》(2016)、《冰河追凶》(2016)、《少年》(2016)、《火锅英雄》(2016)、《暴雪将至》(2017)、《引爆者》(2017)、《嫌疑人X的献身》(2017)、《记忆大师》(2017)、《暴裂无声》(2018)等影片接踵而至,一改国产犯罪片屈指可数的局面。从中虽然仍可看到创作者们在类型边界问题上的游移不定,例如对于警匪片与犯罪片边界问题的模糊,但其类型化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上述影片的类型叙事与话语表达展开发掘,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当前国产犯罪片的发展状况与审美内质。
一、类型杂糅与非线性叙事
类型电影虽具有稳定的创作惯例,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既静态又动态的体系。如同托马斯·沙茨所言:“一方面,这是一个关联到叙事和电影成分的熟悉的程式……另一方面,文化态度的变化、新的有影响力的类型电影、工业的经济情况等,持续地改进着任何一种电影类型。”[2]可以说,类型与反类型的辩证法是支撑类型电影创新与发展的本质问题。近年来的国产犯罪片在类型叙事上形成了两个较为醒目的风格标志:一是元素上的类型杂糅;二是结构上的各类非线性叙事。
所谓类型杂糅或类型复合,是指某一类型积极吸纳其他类型电影元素的创作现象。随着受众电影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与类型电影的不断突破边界,类型杂糅成为类型片创作中的潮流。当下国产犯罪片普遍不再拘泥于传统犯罪片的黑色暴力叙事方式,而是积极吸收悬疑、喜剧等其他类型元素,在跨界与融合中寻求新的生长点。例如杨庆执导的电影《火锅英雄》虽在视觉风格上维持了犯罪片一贯阴暗压抑的冷峻风格,但同时集中了犯罪、爱情、喜剧、黑色等诸多元素。导演本人也表示:“一部优秀的电影是没有类型的,甚至是可以超越某种类型。”[3]在这部充满重庆文化符号与地域景观的影片中,导演延续了前作《夜·店》(2009)的类型杂糅路向,将犯罪故事讲述得妙趣横生又充满黑色荒诞意味。例如在叙事手法上,影片就大量运用了巧合、反差等喜剧创作手法。无论是主人公刘波一行无意撞见银行抢劫现场,还是影片末尾两群反面人物在误会中兵戎相见,都让影片情节发展充满意料之外的戏剧张力,也让主人公的命运变得一波三折、富有吸引力。
除类型杂糅之外,“拼图叙事”等各类非线性叙事也成为当前国产犯罪片惯常使用的叙事手法。例如,忻钰坤执导的《心迷宫》就以精巧复杂的迷宫结构构成了一种叙事奇观。影片有意采用多线索、多视角叙事,从每一位人物的不同视角出发讲述碎片化故事。围绕偏僻乡村突然出现的尸体,诸多人物一一登场,描画出复杂的乡村政治图景与道德状况,也展现出人性的复杂。这种“拼图叙事”为影片营造了强烈的悬疑色彩,也不断挑战受众的期待视野,促使他们以积极解谜的姿态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中。
二、复杂人性的审视与开掘
犯罪片向来具有发掘人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先天优势,以犯罪者为主角发掘其犯罪根源与人性的纠葛挣扎是犯罪片屡试不爽的创作路径。如同有论者所言:“对人性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批判,是犯罪片主题表达的核心内容。”[4]近年来,《白日焰火》《烈日灼心》《记忆大师》等影片纷纷将笔触对准犯罪者的幽暗内心,发掘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展现出国产犯罪片愈加深厚的形象建构与人文关怀。
学院派导演曹保平向来善于在商业与艺术中间寻求平衡之道。从《光荣的愤怒》(2007)、《李米的猜想》(2008)再到《狗十三》(2013),他的电影既注重叙事的戏剧性表达,又善于发掘个体的情感状态与生存境遇,流露出较为强烈的风格化、作者化特征。其电影《烈日灼心》堪称近年来在人性探讨上最具代表性的国产犯罪片之一。影片讲述了辛小丰(邓超饰)、杨自道(郭涛饰)、陈比觉(高虎饰)三名犯罪青年为隐藏曾经无意间犯下的罪案而隐姓埋名,但却在警察伊谷春(段奕宏)的执着侦破中不断被卷入各类旋涡与人性挣扎的故事。三位主人公如何在与警察伊谷春的斗智斗勇中洗脱嫌疑成为推动影片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叙事结构上来看,不断设置的人性困境与身份危机令影片悬念迭起,充满戏剧张力。不过,更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借助悬念重重的“猫鼠游戏”所展开的对人性复杂性的发掘。
对于三位主人公而言,多年前的命案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与负罪感如幽灵般游荡在内心深处。三兄弟一起抚养孤女“尾巴”,正是他们试图摆脱负罪感的自我救赎。警察伊谷春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生活,也让他们陷入了绝境与危局之中,人性的轻与重、明与暗在这一刻被暴露在极端情境之下。表现陷入失常状态的人性是曹保平的惯常手法,他本人就曾指出:“对于影片我都是从人物入手,然后故事基本都架构在一个极致的、失常的状态下,所以每一个故事基本上都是人物被抛离出惯性轨道时间段内的状态。……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抛离正常轨道之后的人的状态,因为这更容易表现出人的复杂性,包括人性中亮的一面和暗的一面。”[5]以往的国产犯罪片/警匪片常常在正邪二元对立原则下,将犯罪者塑造为脸谱化、平面化的反面形象。但《烈日灼心》却深入犯罪者内心深处,描画他们的恐惧与喜悦、明亮与阴暗,尤其是辛小丰这一人物更集中表现了对于人性善恶的质询与追问。影片中,伊谷春与辛小丰的同事与对手关系令后者无时不处于身份焦虑与危机之中。为此,辛小丰不惜以假扮同性恋等种种手法试图摆脱嫌疑。在影片天台缉凶段落中,面对陷入危境的伊谷春,辛小丰陷入了救与不救的巨大道德困境。当他战胜内心重重挣扎而向前者伸出救援之手时,也代表着他救赎之路的最终完成。这一段落,极为浓缩地表达了整部影片的主旨,正如影片中伊谷春的台词所说的那样:“你知道什么是人吗?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他有你想不到的好和想不到的恶。”最终,影片触摸到了人性最幽深的角落,也展现了犯罪电影应有的痛感人性体验与深厚人文关怀。
三、社会症候的观照与反思
犯罪片善于展现现代文明语境下的个体与社会冲突,以一种社会病理学的方式观照社会肌体的诸多病症。近几年,《天注定》《暴雪将至》《引爆者》《暴裂无声》等影片鲜明地体现出犯罪片观照历史或书写现实的努力。国产犯罪片中越来越自觉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源自创作者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也源自韩国犯罪片等创作经验的渗透。以《杀人回忆》(2003)、《老男孩》(2003)等为代表的韩国犯罪片擅长在冷峻凛冽的影像风格中凝注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形成了较为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对国内电影影响颇深。从《暴雪将至》《引爆者》等作品中,就能看到鲜明的韩国犯罪片元素。
董越执导的电影《暴雪将至》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为故事背景。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座阴雨绵绵的南方小城里,小城中发生了针对多位女性的连环杀人案。有“神探”之称的保卫科干事余国伟一心渴望借此机会一举破案,跻身体制内。这部风格极其阴冷压抑的影片虽有犯罪片外衣,但内在质地可以说是一部反类型的文艺电影。影片没有紧张激烈的警匪对战场景与环环相扣的破案解谜过程。影片的叙事视点局限在主人公余国伟身上,受众只能随着他的行为与想法游走于迷雾般的凶杀悬案中,无法逐步推导出完整清晰的案件链条。与此同时,影片还运用了大量的省略叙事,没有对诸多主要角色的情感纠葛与社会关系加以详细交代。这种叙事方式使得情节充满了空白点,故事因果关系的模糊不定不断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
在作者化的同时,《暴雪将至》更引人注目的是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的审视。近两年来,从《钢的琴》(2010)、《少年巴比伦》(2015)到《八月》(2016),不同类型的国产电影纷纷将镜头对准国企改革历程,对那段历史投注了或怀旧或同情的目光。而在《暴雪将至》中,创作者有意将小城凶杀案与变革的大时代相勾连,透过犯罪故事窥探时代车轮的转轨与社会集体心理的流变。主人公余国伟(段奕宏饰)作为体制外的保卫人员,费尽心力想成为正式公安人员,甚至不惜以爱慕者燕子为诱饵来缉拿凶手。影片中有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幕:余国伟面对执法人员,反复解释自己的姓名,“余是余下的余”“余是多余的余”。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以不可逆转的姿态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体制内身份正面临崩塌。余国伟则是逆时代潮流的“多余人”,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黄昏寻求体制内的身份认同。影片末尾,国有冶炼厂在职工们的无声注视下轰然倒塌,从此化为历史的废墟。余国伟跻身体制内的无望与职工们丧失体制内身份的无奈在那一刻纠缠在一起,书写了一则“镌刻历史的铭文”[6],描画出了庞大的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也唱响了一个集体主义时代的挽歌。
电影《引爆者》则将镜头对准当下中国社会的底层工人群体。影片讲述了煤矿爆破工人赵旭东(段奕宏饰)无意中卷入煤矿老板的阴谋旋涡,而后在重重困境中奋起反抗的故事。赵旭东既是地下爆破工,又曾因私造炸药而入狱,凸显了他在社会中的双重边缘身份。而在资本阶层的步步紧逼之下,曾经委曲求全的他只能揭竿而起,在一处充满隐喻的工厂空间里点燃了反抗怒火。在《暴雪将至》中,曾长期拥有主体地位的工人群体在市场大潮前面临强烈的身份危机。而《引爆者》则展现了进入新世纪之后,经过十余年高速现代化进程后新工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说前者所表征的是集体主义时代曾具有政治主体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而后者所呈现的则是新的历史语境下浮现的‘新工人’群体所普遍具有的社会身份焦虑。”[7]上述两部电影的同时出现,展现出当下电影创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不断自觉的观照意识,也展现出了犯罪片在犯罪叙事与本土社会问题结合后所能触及的深度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