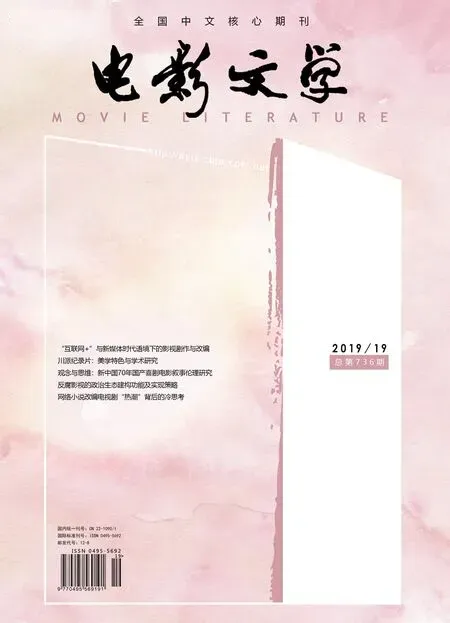试论明星社会责任的生成逻辑
王 艳 颜汇成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与电影明星相关的各种话语数量剧增,他们也正成为大众“欲望”和“快乐”的目标以及“道德”的参考标准。由此,明星研究的学术视域自然要超越对电影自身(包括电影产业、电影本体和电影文化)的关注,而将注意力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也就是说,将“电影明星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明星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引之下,本文尝试借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概念对电影明星的社会责任做一考察。
一、明星与卡里斯玛型权威
卡里斯玛(Christma)是韦伯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概念源自韦伯对基于权威的合法支配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形态的经典研究和分析。韦伯依据支配的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区分出了三种支配类型:传统型权威、卡里斯玛型权威与科层制(或法理型)权威。在韦伯的概念体系中,“卡里斯玛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为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他们拥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根据此种禀赋,以及根据——在神的观念已清楚形成之处——存在于此种禀赋之中的神之使命,他们行使其技艺与支配”[1]263。那么当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电影明星”是否可以算作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
派屈克·菲利普在《类型、明星和电影导演》一文中指出“明星”具有四个层次的内涵:(1)明星是一个真实的人;(2)明星是角色的公开表演者;(3)明星是一种人格面具;(4)明星是一种形象。[2]这一分析性的界定基本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明星的经验和认知。就明星的诞生过程来看,他们首先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然后通过在某部或某几部影片中的成功表演而为电影观众所认可或熟知;正是借由这种认可或熟知度,他们得以进入更为广泛的媒介文本之中,以某种观念、价值或“人格”的符号形式进一步与各种媒介的接受者深入接触,从而有机会获得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认可,并最终化身为某种鲜明的公共形象,成为来自媒介文本,却又超越任何具体文本之上的“明星”。因此,对于明星而言,观众的认可或认同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不论观众的这种认可或认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还是受到当下各种媒介的大肆宣传所致的被动认同。那么,观众为什么会认可或认同一个明星呢?或者说,观众认可或认同的是明星的什么呢?
从历史和经验上看,当我们提起费雯丽、英格丽·褒曼、马龙·白兰度、贾莱·古柏、约翰·韦恩、克拉克·盖博、格丽亚·嘉逊、李小龙、成龙、巩俐、姜文、周星驰等中外电影明星时,往往所感受到的都是他们所散发出的超凡魅力,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光晕环绕着他们,诱使人们对之产生由衷的崇拜心理。正如保罗·麦唐纳所言:所谓的明星不只是一个表演者,而是魅力的化身、形象的代表[3]。因此,对于观众而言,其所认可或认同的正是明星所展现出的超凡魅力。这种超凡魅力可以来自明星在电影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李小龙的银幕形象;也可以单单基于明星本人超凡脱俗的外表,如英格丽·褒曼、玛丽莲梦露;也可以通过游走于各种媒体文本之间而获得虚假的超凡魅力以保住作为明星的社会身份。无论如何,对于明星而言,拥有并表现出某种超凡魅力是其成为明星的关键——正是在此意义上,明星的确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卡里斯玛”属性。
然而,具有“卡里斯玛”特性的明星是否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权威”?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定义来看,“权威”来源于权威的追随者一定程度上的自愿服从。它不同于“权力”这一概念,因为对马克斯·韦伯来讲,“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4]。现实生活中,明星的追随者,特别是明星的粉丝显然是自愿追随自己所认可的明星的;明星在社会生活中的号召力,或者说使其追随者自愿服从的能力可以在铺天盖地的明星宣传或广告中得到见证。因此,拥有并表现出某种超凡魅力的明星的确是现实生活中的“卡里斯玛型权威”之一种,并自然具有这种权威类型的“个体性、非常性、使命性、反经济性、不稳定性和革命性”[5]等基本特征。
二、明星身份的赓续
在电影史上,明星的衰落与消匿如明星的诞生一样数不胜数。其实,明星作为一种“卡里斯玛型权威”本身就无法逃避注定衰落的命运,“对任何非凡的能力所燃起的卡里斯玛信仰,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再度失去其光芒和意义”[6]。丧失身份的危机早在明星身份生成的那一刻,就同样作为身份内涵的固有属性而存在了。但是电影工业不会任事态自由发展,电影工业的长久兴盛离不开电影明星的支撑——美国好莱坞的发展史即为例证。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群体或一种身份的明星——而非仅仅针对现实的某个明星个人——如何巩固和保存自身。
面对这一困境,马克斯·韦伯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八种方式:以个人特质是否符合权威地位为标准选择新的权威;以神谕、抽签等技巧借助神意来选择;由原来的卡里斯玛权威指定继承人;由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权威群体推举;通过血缘关系继承;通过某种仪式赋予;权威的追随者主动选择并承认;通过民主制的选举产生。对照韦伯给出的产生新的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八种途径,我们可以发现:当下新的电影明星的诞生方式已经基本涵盖了所有这八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常规的通过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而诞生的明星,比如黄渤通过《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疯狂外星人》等影片而成为新一代的中国喜剧明星;通过电视上的各种选秀节目诞生的明星则实践了第二、七、八种方式,比如腾讯视频独家推出的《创造101》;张艺谋导演通过其影片所推出的“谋女郎”以及近期真人秀节目通过“导师制”所制造的明星则基本符合第三、四、六种方式;“星二代”在中国影坛的出道方式则往往是对第五种方式的践行。
韦伯所给出的八种方式虽然为明星的持续生产提供了可资依赖和仿行的途径,但不同的方式所发挥的效力是不一致的,其产生的结果也各有不同。对制造明星而言,有些方式,如以选秀节目来具体实践的第二、七、八种,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内生产出大批量的明星,满足电影产业的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一方面,明星所具有的卡里斯玛资质逐渐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或专职化的选拔来获取,导致卡里斯玛的“祛魅”倾向。“卡里斯玛能力一旦转变成一种用任何手段——最初是纯巫术的手段——来转移的例行化资质,这就开始步入从天赋资质——可以被实验与确证的,却无法传递与追求的资质——转化为原则上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资质的道路。”[1]323“祛魅”倾向的产生使得明星身上的神秘光晕逐渐消失,并日益染上世俗化、功利化的色彩。另一方面,对造星途径的过度依赖会使得明星的卡里斯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个人独特性,而变得整齐划一,缺乏多样性——这必然会最终影响整个电影生态的良性发展。
三、不可推卸的明星责任
持续不断地制造新的电影明星虽然关系到电影工业的长盛不衰,却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它同时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议题,特别是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社会而言。
如上文所言,卡里斯玛型权威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这种超凡魅力并非封闭自足的——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超凡魅力与追随者对他的认可或认同密不可分。“被支配者对卡里斯玛之承认与否,是卡里斯玛是否妥当的决定性因素……此种承认乃是对某些启示、对英雄崇拜、对领袖绝对信任的完全献身……如果领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法创造奇迹和成功;如果神或魔性及英雄性的力量似乎抛弃了领袖;最重要的,如果领袖无法继续使跟随者受益,他的卡里斯玛支配很可能因此丧失”。[7]因此,对于明星而言,追随者的承认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他是否可以获得或保有其明星地位和身份,而追随者是否承认又取决于他能否为其“创造奇迹和成功”,“使跟随者受益”。对于明星的“追随者”而言,“奇迹”“成功”“受益”意味着什么呢?
很显然,就电影而言,明星所能提供的内容包括奇观化的感官体验,如明星光鲜的外表、出色的表演、引人注目的银幕形象等;源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如明星所代表的浪漫爱情、温馨亲情、忠诚友谊等;醍醐灌顶的价值导引,如合宜的生活方式、正义、公正、对自由的追求等。如果说明星所提供的感官体验因其诉之于人的感性而不易持久,不够深刻,稍纵即逝,那么内心的幸福体验与合宜的价值导引则更能够真正地长久占据人们的内心,也是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追随者在权威那里最想获得的内容。此外,正如希尔斯在分析和进一步发展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时所指出的: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需要秩序。“人们需要秩序以便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秩序可以提供一致性、连续性以及正义。”对秩序的需要导致卡里斯玛的出现[8]268-269。而现代社会秩序的特征则表现为“由于理性化与官僚化的发展,对超越价值的信念会逐步减弱,个人或制度所体现的超越价值的象征意义会越来越少”[8]268。由此来看,明星的出现与持续制造就不再纯粹是电影工业与观众的合谋,而成为人们当下生活的真实需要——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明星成为向社会大众提供秩序的一种途径。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为追随者提供内心的幸福体验和价值导引,为社会提供超越性的价值和秩序感就成为明星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成为明星角色的固有内涵,成为明星持续不断地被生产,并进而不断生产自身的深层动机。
四、结 语
当下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超越价值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沦丧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进程。从社会学的角度,以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概念为依托来审视明星,不仅为我们认识明星的本质提供了一个颇有助益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许可以借此超越略显消极的文本分析和解读的研究范围,将明星研究推向更为积极的实践路向——不仅探讨社会对明星形象的建构,还进一步讨论明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积极地建构社会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