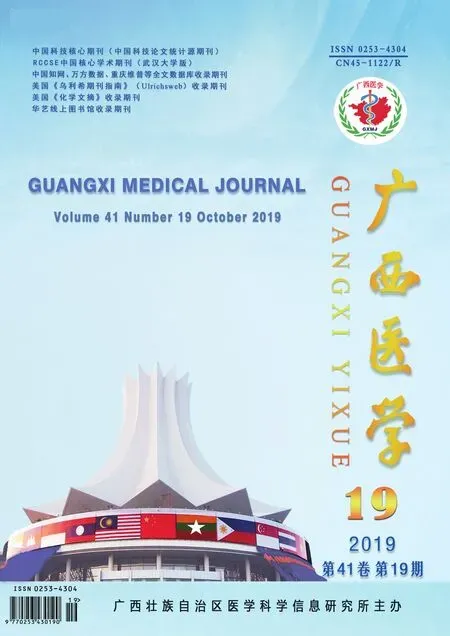“三医”联动政策背景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现状▲
于晓彦 蔡锦洪 何春辉 陈峰松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医院医务科,海门市 226100,电子邮箱:yuxiaoyan198927@126.com)
【提要】 我国医疗费用负担重,完善医疗、医保、医药三方联动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三医”联动政策背景下,我国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由理论走向实践。本文对在“三医”联动政策背景下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实践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完善评估程序和方法、探索更加灵活的谈判定价方式、适量扩大谈判药品数量、完善配套政策、增强社会共识等方面提出完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建议。
人民群众用药负担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1],要让老百姓用得上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药品。李克强总理就抗癌药降价问题多次做出重要批示,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工作要一抓到底,最大幅度降低药价,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2]。自“三医”联动进入大众视野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从医药入手、用医保管理、在医疗落脚”的举措,积极探索实施药品价格谈判机制。
1 药品价格谈判的意义及政策支持
1.1 药品价格谈判的意义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可以有效均衡医保、医药、医疗等各方的利益,其旨在以市场换取合理的价格,通过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对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破除以药养医格局、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内涵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1)药品价格谈判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好医保的控费功能,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轻医保负担,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因此,药品价格谈判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举措。(2)药品价格谈判有助于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对于医药企业,通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药品可以纳入医保目录,纳入谈判的药品直接进入公立医院采购目录,这相当于攻克了进入药品市场的两大难关[3]。药品价格谈判对接生产方和需求方,削弱了流通环节的主动权,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医药流通秩序,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3)药品价格谈判有助于减轻患者用药负担。药品价格谈判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降低专利药和独家生产药品的价格,是新时代下的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其可直接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增强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
1.2 我国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相关政策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4],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对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政策探索。随后,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见表1),逐步推动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实施落实。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我国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支持。
2009~2014年,国家层面涉及药品价格谈判的系列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探索建立医疗、医保、医药三方联动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但均为政策的原则性指导意见,未做出更为详尽的指导和要求。部分发达省份或直辖市率先开展省、市两级以降价为目的、以医保为筹码的价格谈判(如上海市),但尚未在国家层面开展与相关医药企业的谈判。2015年,国家层面开始进行药品价格谈判的实践探索。201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5]。这标志着针对部分专利药、独家生产药品的价格谈判工作从国家层面开始实施。

表1 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及药品价格谈判的部分政策文件
2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实践的发展
2.1 首次药品价格谈判 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建立了协调机制,组织并开展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谈判主要针对国内专利药和独家生产药品[6]。2016年5月20日,首批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公布[7]。2016年10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做好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新农合报销政策与国家谈判药品的衔接工作[8]。2017年2月,国家人社部印发新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谈判药品纳入新版目录中,至此,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主导的首次国家药品谈判尘埃落定[9]。首批谈判成功的3种药品包括替诺福韦酯(葛兰素史克公司)、埃克替尼(达贝药业)、吉非替尼(阿斯利康公司),降价幅度分别为67.33%、54.17%、53.33%[10]。以专利药和独家药为目标的药品价格谈判,释放了“贵族药”的降价信号。
2.2 第二次药品价格谈判 2017年7月,由国家人社部主导的第二次国家谈判结果正式公布,参与谈判的44个药品中,36种药品纳入医保目录,谈判成功率达到82%[11]。国家人社部发布《关于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54号)》,明确规定各地不得将这36种药品调出目录,并同步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11]。与首次谈判相比,第二次药品价格谈判成功纳入医保的药品品种扩大到36种。在这36种药品中,由罗氏公司生产的曲妥珠单抗由21 613元降至7 600元,降价幅度最高(达64.83%)。经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后,在36种药品中,除了天士力公司生产的重组人尿激酶原价格略有上升(涨幅为6.43%)之外,其他药品品种价格均明显下降,平均降幅为34.44%(8.98%~64.83%)。列入此次谈判范围的西达本胺、康柏西普、阿帕替尼等国家重大新药创新专项药品,全部谈判成功,降价幅度分别为30.03%、17.47%、36.52%[12],这也体现国家对创新药的支持。
2.3 第三次药品价格谈判 2018年6月,由国家医保局牵头,会同国家人社部、卫健委、财政部等启动了目录外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同年10月,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18年抗癌药专项谈判结果,经过与企业的谈判,参与谈判的18种药品中共有17种谈判成功,均为肿瘤药,谈判成功率达到94.4%[13]。这17种抗癌药品对非小细胞肺癌、慢性髓性白血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结直肠癌等恶性肿瘤具有显著疗效。17种谈判药品价格的平均降幅达56.70%,其中奥西替尼(阿斯利康公司)、克唑替尼(辉瑞公司)及阿昔替尼(辉瑞公司)降价幅度最大,分别为71.02%、70.85%、70.76%[14]。目前,按照国家要求,各地正积极落实17种抗癌药价格谈判相关工作,“4+7”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正在积极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15]。
2.4 3次药品价格谈判综合比较 目前,我国已进行了3次药品价格谈判,谈判机制遵循平等协商、利益均衡、以量换价,谈判成果显著,最终形成医保基金可承受、更多患者受益、药企愿意让利的“三赢”局面[16]。与首次试点谈判相比较,后两次的谈判药品品种数都明显增加。3次药品价格谈判降价幅度都很显著,这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费用负担。首批药品价格谈判的牵头部门是原国家卫计委,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与医保对接的问题;第二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主导部门是国家人社部,明确规定“各省(区、市)不得将有关药品调出医保目录,也不得调整限定制度范围”[11],因此能够保证谈判结果落地实施,药品价格谈判的利好效果在较短时间内能够看得到;第三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直接由国家医保局主导,助推了医保角色的转换,意味着医保走到了医药服务购买的前端。
3 我国药品价格谈判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药品价格谈判实践还处在起步探索阶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尚未形成完成规则、谈判定价方式单一、药品进院难、谈判品种少等。
3.1 药品谈判准入规则不完善 目前,3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主导部门经历了不断地调整,谈判流程也基本成熟,但是工作框架和流程还没有确定下来,尚未制定出指导未来工作的参考方案。企业受邀参加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没有自主申报的权限。在未来医保目录的调整、药品使用量的变化、专利药和仿制药情况的改变等方面,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还没有建立起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长效、动态的工作机制。在谈判结果落地后,对药品的实际使用情况没有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难以衡量药品价格谈判实际情况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
3.2 谈判定价方式以单一降价为主 受制于信息数据、法律法规等因素,我国的药品价格谈判形式较为简单。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定价方式以单一的降价为主,谈判过程中两组评估专家分别从药物经济性角度和医保基金负担能力这两个方面进行测算,最终形成医保支付价格。药品价格受到医药政策、流通、药品价值等多方面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定价方式对于根治高药价的问题至关重要,而这需要不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打造健康有序的流通秩序,提供科学合理的医药服务,鼓励创新。
3.3 药品进院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实际采购过程中,个别医院仍然存在二次议价行为,而且没有固定规则,这让已经大幅降价的企业无法接受。药品使用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在“以药补医”还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让谈判药品得到合理使用,需要医保、医疗、医药等各部门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也需要信息互通和细化考核、监督。
3.4 谈判药品品种数量少 3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成功的药品品种分别为3种、36种、17种,与实行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层面药品价格谈判的品种数量整体偏少。
4 “三医”联动视角下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政策的建议
4.1 形成详细的药品价格谈判规则,完善评估程序和方法 (1)根据实践经验,形成完整的谈判规则和流程,进一步完善谈判细则,包括企业根据规定提交材料,专家组对企业材料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形成价值共识,医保方与企业谈判形成支付价格和方案等。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规则和流程的有效落实,可为各省的药品价格谈判提供指导和参考。(2)重视证据,包括临床证据、经济性证据、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信息等,使得谈判过程更加科学、客观、公正。(3)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制定谈判流程的配套规定,例如欧盟透明性指南(Directive/89/105/EEC)等。(4)利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对谈判落实过程中药物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衡量和测定实际落实情况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便在以后的药品谈判中进行修订。(5)制定详细的谈判准入规则,改变“邀请谈判”模式,符合条件的医药企业可自主申报,明确药品通过谈判方式进入药品医保目录的路径。
4.2 进一步探索更加灵活的谈判定价方式 药价的形成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密切相关,降低创新药、高值药品价格,不能完全依赖于医保谈判机制。探索运用多种谈判策略,未来也可考虑国家层面“量价挂钩”开展价格谈判。借鉴国外的经验探索,运用更多合理的新定价方式。例如,参考德国医保定价模式,对新药进行分类评估,根据其价值进行定价。
4.3 适量扩大谈判药品数量 制定完善的医保目录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参与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药品种类和范围非常有限。在以往谈判经验的基础上,多维度实施谈判扩容,不仅要扩大谈判药品的品种,也将涉及更多国内药企。参照发达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品种数,结合药品的临床疗效、可负担性以及可及性等因素,遴选出适合谈判的药品。
4.4 完善配套政策以保障谈判成果的落实 随着更多以抗癌药为代表的高价专利药和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提出“医院不得以医疗费用总控、医保费用总控、药占比和药品品种数量限制等为由影响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与合理用药需求”[17]。另外,各地医保部门应重视费用控制,避免药品滥用,例如明确诊断标准、规范治疗方案等。各部门要继续强化沟通机制、督导机制和通报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发挥医改政策协同作用,实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薪酬制度改革等政策。
4.5 增强社会共识,加强“三医”联动 在“三医”联动改革中,一是要不断壮大医保部门的力量,充分发挥医保部门的统筹管理和行业引导作用;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在各省的落实中,减少由医保基金问题造成的阻碍。另一方面,作为实际用药单位的医疗机构直接参与谈判,不仅能够调动其积极性,而且能反映用药主体的真实需求;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对谈判全流程予以密切监督,对于不合理用药涉及的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医药代表、医务人员,予以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