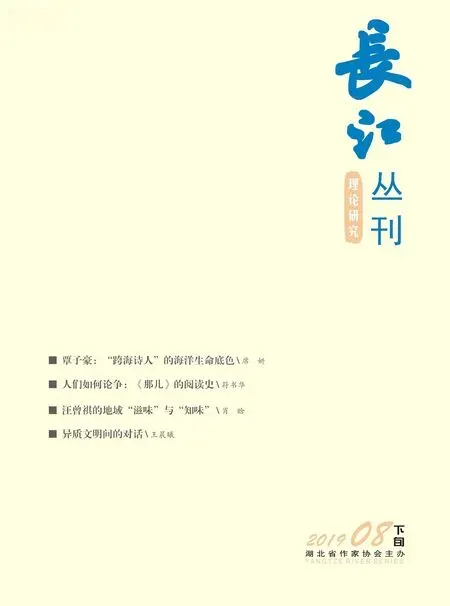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教育选择研究
——以富民小水井苗族村为例
■杨 俊/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一、对苗族乡村亚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思考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丹尼尔·贝尔对“文化”的定义作了如下诠释:“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这种对文化所具有的功能性解释,为我们传递出了文化在其使用效能上的功能性解释,即:文化总是和产生自身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基本生存状态的样式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底色,也就是“生命过程”,“生命过程”在这个定义中是一个前置性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文化不能够对自身赖以生存的民族群体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解与解释,这个“生命过程”的方向、路径及后果就会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处于盲目状态之中的民族群体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把握自身整体的发展趋势与状态,最终又会陷入到新的盲目状态,周而复始的重复这种盲目的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之中民族群体就会失去掌握自身命运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也就将自身置于一个盲从的状态,任由命运之神摆布而失去对自身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认知、把握及征服。在此“人类生命过程”和“解释系统”就成为相互依存的一对孪生子,二者融合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民族群体面对特定的“生存困境”时,能够以自身所认知、理解的方式去应对,去征服,最终形成民族群体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样式,在这种样式当中“生命过程”、“解释系统”与“生存困境”达成了一致。正式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我们完整看待文化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从历史上看,苗族先祖在和黄河中下游炎黄部落进行争锋失败后,苗人历代备受统治阶级及邻近族群的轻视,其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区,相较新地点其他民族来说总是属于晚到者,这就使得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更加恶劣,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环境中,个人所能支配的资源与能力总是有限的,单个的苗人个体很难独立生存,就只能结合为一个群体或集体,依靠集体或群体的力量来生存与发展。在这种艰难环境之下生发出的文化内容和形式总体上具有“冲突”与“和谐”的二重性,“生存困境”是“冲突”或“紧张”,代表了苗人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切实的生存压力,为了“对付”这样的生存压力,克服“生存困境”,就必须的“努力”,依据自身原有的“解释系统”来与新的在新的“生存困境”中形成的“解释系统”进行比照,进而调试、重建新的“解释系统”,赋予在特定“生存困境”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以新的意义来保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由于苗族迁徙范围广、跨度大,迁入地区的人文、自然环境也不尽相同,就造成不同苗族迁徙团体面临不同的“生存困境”,为“对付”不同“生存困境”所产生的“解释系统”及生存手段与方法也就大相径庭。可以说,苗族内部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苗族传统文化与新人文、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交流、融合、妥协的结果。
二、富民小水井苗村村史回溯
云南是一个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民族众多的高原山区,在如此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中各少数民族根据自身所持有及能够支配的资源多少,决定了自身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中的基本位置,一个民族拥有的基本生产方式、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及生产过程就构成了这个民族基本的生存内涵,这种生存内涵又直接决定着人口的多少、对外交往、影响范围等外延性因素。从富民县域内各苗族村寨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苗族村寨整体的发展同小水井苗村的发展历史基本一致。这个区域内的苗族几乎都是在清末及民国期间从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迁徙而来的,从苗族具体迁移群体的数量和文化积淀上来看,人口数量多的村寨400多人,少的只有10多人,这些村寨中总是以特定核心家庭所形成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相互连接,汇集成村的。
小水井苗村也是首先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而发展而来的。在对小水井苗村的整体调研过程当中,根据每户人家老人的回忆,可以大概构建出这样一种建村史。漂泊迁徙而来的苗族家庭在此地落到生根后,出于生产或亲情等原因,又将在原居住地的亲戚带到此地比邻而居,逐渐形成以一个核心家庭(最早落户)为核心的血缘亲族村寨,最终同一族群不同的血缘亲族家庭就构成了小水井苗村现今基本的状态。但应当注意,这些迁徙而来的苗族家庭从其自身实际来看,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在迁徙过程中,漂泊中的苗人家庭除了随身携带的简单生产、生活器具和具有血缘关系的有限家族成员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之物了。这里苗人的情况,总体呈现的是族群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结构简单、初级,文化整体构成总是围绕着初级“生存困境”展开,观念不复杂。二是由于总处于迁徙的状态,生产力不发达而“生存困境”又时常存在,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源供给不了太多的民族人口,这些就导致该族群人口相对其他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来说,人口数量有限。从进入云南的各苗族支系群体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两个因素较为准确概括了苗族迁徙群体的特征。积淀再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有一个继承的问题以及继承多少,发展多少和如何“扬弃”的问题,不是每一个民族中的个体都是且能够成为民族文化保持、传递、发扬者。
三、对小水井苗村亚文化形成与教育关系的思考
教育和文化都作用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所以二者从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捆绑在一起。文化要应对各种“生存困境”,积累经验和知识,而这些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总离不开一定的教育形式来进行传递与发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个具体文化事项的演变与累加,需要一代一代地传递与积淀,其中关键的就是要实现同辈之间的分享与代际之间的传承,否则,文化既形不成体系也不能起到对人塑形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化注定要把教育作为其生命的动力机制,从教育中获得活生生的生命博动,吐故纳新,成长发展。正因如此,如果说文化是“人生命过程的解释系统”的话,那么教育就是这个“解释系统”自身生命力的源泉或者是这个“解释系统”生存发展着的“生命机制”。
由于教育的发展总是与现实而具体处于变化中的文化事项休戚相关,因此关注教育就不能不关注文化中现实发生的具体事件。抽象的民族文化观念只存在于理论与总体的维度之上,在处于不断变化中民族文化现实中并不能完整的展现与提供真理性的认识,正如通常所说,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大概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单纯从抽象的民族文化概念上来看待、理解及解释具体的民族教育事项和文化事项,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对事实歪曲的理解与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面对复杂的民族文化变迁实况时,只能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事项、事件入手去分析、概括、总结,用以窥察文化变迁总的态势,进而提供理解与解释。在这当中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视角之一。
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当中,可以知道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教育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规律,规定与引导着人的发展。教育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间接力量,要通过教育的结果——人的实际行动来产生切实的效果作用于社会各领域,使其发生变化。可见,教育——人——文化之间隐含着一种实际的因果关系,透过这种因果关系可以看到教育不仅关系到整体的发展也关系到个体的发展,因为任何整体性的发展都离不开个体创造性的努力与行动,任何外部或内源的文化挑战与危机总是首先体现在个体的生存状态上。教育是一个实体性的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教育目的、教育方式、教育场所、教育目标、教育期望、教育成效等方面都离不开具体的学生、家长、教师、民众及环境的参与,呈现出的是一种“合力”的社会活动。当整体的危机与挑战出现时,就会使得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体与个体的生存应对之道。
苗族虽然长时间生活在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但这些发达的生产关系与文化总是以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其他民族相联系,在面对比自己发育程度更高的民族时,苗族就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当中。从小水井村史的开端来看,迁徙到此居住的苗族群体长期深受周边发展程度较高民族的歧视,使他们变得对外族的人和事都抱着疏远和怀疑的态度,不敢去面对繁杂多变的外部社会。再加上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处在生存极限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