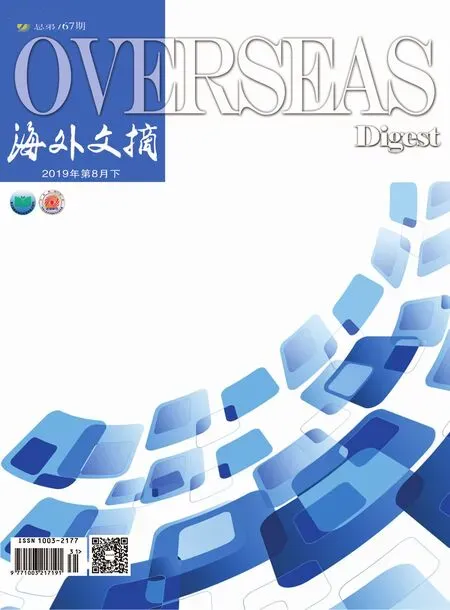新叙事理论视野下张炜《九月寓言》的文化意义
辛凤
(景德镇陶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403)
1 叙事伦理与个体叙事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叙事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将对叙事的研究引向了社会、文化层面。詹姆逊指出,观点对于叙事作品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比观点更为重要的是转调、半音过渡,电影的淡出或蒙太奇等发明。在叙事阐释中,詹姆逊坚持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视角。在欧美理论界,叙事学(narratology),通常指的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法国,后扩展到欧美的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但叙事理论本身,历史却要长得多,且仍在进一步发展。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己出现了关于叙事的研究。至20世纪,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外,又有以亨利·詹姆斯和卢伯克等为代表的现代叙事理论,及众多的后现代叙事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有了进一步拓展,它与已经取得大量研究进展的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沟通跳出了将其自身限定在叙事本文内在的封闭式研究的局限。叙事学在保持其自身的理论特征和学术范式的同时,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在文化研究背景下所出现的叙事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向。
与此同时,叙事理论的研究在国内纷纷开展,取得了很多成果。刘小枫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种,具体体现在其《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中的《叙事与伦理》一文中:
“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
透过作品对大叙事和个体叙事的观察,可以看清作家创作体现的价值。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提出文学是一种活动,由作品、宇宙、作家、读者四要素共同构成。作品来自于作家,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机会与感受,提供一种体验的力量。显然,在这里张炜的叙事已超出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了,在困境中弱者的生存超越了一切人民伦理,个体生存的意义成了作品最重要的表现。作品通过个体生存困境来否定乌托邦,又反向对乌托邦表现出关注,两者相互沟通显示出了作家对个体生存合理性和群体乌托邦梦想的双重关注,这正是张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持有的精神姿态,也形成了韩少功、莫言、李锐、余华等作家小说创作中的共同的倾向性。
在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阐释张炜创作中表达的个体意义和彰显的个体叙事的魅力:
首先,是个体叙事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与个人叙事的区分。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提及:“无根的苦难是因为宏大叙事的解体。”个体叙事中着力去表达个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把历史表现为个体无法超越的生存困境,这是对宏大叙事的一次解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先锋小说崛起,迎来新的文学高潮,评论界对先锋小说异常关注和热情称赞,然而到了90年代初,实用主义、经验理性、工具理性甚嚣尘上,主宰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时,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就是努力为价值理性争得一席之地。在作家队伍中,张炜便是道德理想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
其次,张炜是一个歌颂民间理想的代表人物和时代先锋。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一文中提出:“民间在当代是一种创作的元因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格取向。”在《九月寓言》里,张炜通过对大地的赞美和融入民间的忠诚,表达了一种纯美和无上的真诚。这种真诚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是孤独的,也是一道光芒无限的理想之光。作家在描绘了个体生存和群体梦想的悲歌,他们的这种关注是一场“无根的苦难”。
张炜是一位对时代极其敏感的作家。张炜说过,“在一望无际的海滩平原上,在一片片的稼禾和丛杆中间,我总是感到了令人至为激动的东西。它温厚无私、博爱,它宽宥了人们的所有行为。在这里,我常常呆上很久。我可以在这个时刻里回忆很多往事,总结我的生活。这时我开始变得宁静,很清澈,也很能容忍。”在产生于90年代初的《九月寓言》中,他坚定地举起“道德理想主义”大旗,将姿态埋进土地,“融入野地”,耗尽心力地去捕捉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对时代的某些隐忧和不安。莫言提及,“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诚然,张炜以他特有的魅力和特色屹立于当代文坛,不管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赞歌,还是深度挖掘生命和人性,他以在文坛坚实的地位和固有的姿态,始终坚持崇高意义上的写作,关怀巨大的历史与社会主题,怀抱殉道者的理想,关怀人的生存命脉和人的终极价值意义。
2 《九月寓言》叙事的文化意义
《九月寓言》作品的两个元素:理想之光和对土地情结的执着,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朴实和朴素之风,为文学作品的鉴赏带到更深的文化意义。
2.1 作品凸现的理想之光
1987年到1992年,张炜用五年的时间,隐居在山东龙口的农村,完成了这部《九月寓言》的创作。他说,“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上被挖掉了一块,而且很难补上了。”事实证明,这部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小说中叙事时间的独特魅力,文本中的追忆、憧憬、忧虑、困惑,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下的境况中更加耐人寻味。评论家陈思和曾用“还原民间”一词来概括九十年代某些风格的小说作品,《九月寓言》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陈思和指出文革后的小说家,更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改革的精神,他们亲身经历这段历史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希望能在作品中传达改革之意,这就使得他们即使在写民间时都具有先天的思想优势。
在《九月寓言》里作家以诗化的语言,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村,以寓言的讲述方式建构了一个乌托邦似的理想村庄。这是一个遍布着寓言色彩,有着自己独特的喜怒哀乐的村庄。所有的村民在祖辈留下的土地上辛苦而又快乐地度过充实的一生,依赖着土地繁衍生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力量,他们是简单的,除了生活就是生活;他们是纯朴的,他们自带最自然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天地境界的生存方式,他们与天毫无争执,与地和平相处,与工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不同,它不是在对对象化世界的征服、利用中把自已变成了榨取财富的工具,而是把尊重生命自身作为生存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九月寓言》这部长篇主要是讲了一个“奔跑”和“停留”的故事。但是,小村人无论“奔跑”还是“停留”,都是在土地之上。《九月寓言》更是一个关于人和土地的故事。地瓜是小村的主食,是生命的能量源地。在《九月寓言》中有多处关于地瓜的描写,有很强的年代感和指代性。张炜这样说“地瓜”:“在贫寒凄苦的岁月中,它给予村里人最后的安慰和保证。”“我没有想到它的象征,我只是爱它。”红的地瓜是最基本的食物,对庄稼人来说,填满肚子就是福气。在渴望吃饱的同时,则是小村人对饥饿的恐惧。比如肥的父亲是饥饿而死的,母亲因为饥饿而被两块煮地瓜噎死。提到地瓜的意象,张炜说:“小村里的人试着将地瓜做成各种各样的食物:水饺、饼、馒头,还有煎饼。这除了出于无可奈何而外,也还包含了一种亲情暖意。在贫寒清苦的锁钥中,它给予村里人最后一个安慰和保证。我被这种又普通又奇特的关系给感动了。”
地瓜给予小村人生命的激情,奔跑是这种激情的发泄。小说描写了一群年轻人赶鹦、肥、三兰子、香碗、争年、龙眼等的生活和斗争。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贫穷、落后压抑不住年轻人们的火热,他们奔跑、争斗,释放着自己体内的能量。《九月寓言》中也展露出小村人流浪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作品中各个生命乃至于希望得以存在的关键,好像只有去流浪和奔跑才会实现小村人的生命追求和生存价值。比如闪婆和露筋为了爱情而流浪、金祥千里寻鏊子、独眼义士三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负心嫚儿等等,都是在奔跑和流浪中展现出生命的价值和过程。作者多次描写到年轻人和田野、大地的融合,通过人与大地的融合,找到生命最原始的冲动和力量。在张炜看来,大地能够承载人类所有苦难,守住大地,是人类的精神救赎。
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厌倦、对乡村民间生活诗意的向往,一度贯穿了张炜近年的小说创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炜借由《九月寓言》的创作,提出了“融入野地”的理想,实现了其价值立场的转向。“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
张炜是一个歌颂民间理想的典范,在《九月寓言》里他通过对大地的赞美和融入民间的忠诚,诉说了一首纯美和无上的真诚之歌。有人说过,小说家是专门在人文、人性、情感这块园地上耕耘的人。人文关怀是真正的文学永远的追求。正如张炜所说:“一个知识分子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迎合世俗力量开始的。一个冒牌诗人从来不会在世风里守住什么。好的作家总是更多地考虑他读者的价值。”张炜正是默默坚持着这一信条,用自己的真诚来书写一首永恒的大地之歌。虽然,这种真诚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现实社会注定是孤独的,但同时也是一道光芒无限的理想之光。
2.2 对土地情结的执着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文学亦是如此。《九月寓言》的代后记《融入野地》中,张炜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张炜在这篇代后记中,不断地重申着这个真实,这个本源,那便是土地。在《融入野地》中,张炜多次提到土地、大堤、泥土,他说:“做梦都想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张炜作品构建的基础就是是那块生生不息、却又永久保持沉默的大地。
关注作品深层的蕴涵,是研究者不断开掘的动力。《九月寓言》是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在《九月寓言》中,张炜创作出了一个跃动着生命与激情的大地。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九月寓言》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在《九月寓言》中,张炜将“大地”这一意象,以哲学与诗的语言予以充分展现,主要体现在:
首先,张炜在叙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对土地的温柔与依恋之情,用拒绝城市和融入野地来寻找真实和原来。在《九月寓言》中,作者描述了一群不断奔跑的小村人,奔跑这一特征更能深切地体悟出大地对于生命的意义。村庄里的每个人的生命都与大地充分的融合,把个人命运都寄放在对大地的想象和期盼中。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漫长的苦难历史中,对命运、生命、生活都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在土地面前,生命变成一首热烈的歌,一个充满生命魅力的寓言。小村庄人的命运都交付给了土地,都交付给了最纯正的奔跑。作品中对于“奔跑”有很多处的描写,比如赶鹦的疯跑,肥在雨中的迷茫,三兰子的惨死,少年龙眼的耀眼的白发,用忆苦来排泄痛苦的老辈人,乃至于整个小村人不断奔跑的宿命。从这个角度看,作家依赖着对土地来书写生命,来获得人生的意义。因此,张炜通过最切实的人生忧患,却叙述出最超越的神意的欢欣。
其次,在叙述的语言上张炜显露出对于大地的某种不可抑制的好感乃至迷恋。在《九月寓言》中,张炜展示了一个跃动着生命与激情的“乌托邦”的大地,并详尽描写了小村人的生活。半夜里男人的摔打、女人孩子的尖叫、刘干挣、方起的悲壮的“起事”、金祥千里寻鏊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小村人为求得生存而做的拼搏。张炜对现代文明显然是排斥的,对小村代表的传统文明的轰毁充满了挽歌式的留恋。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张炜一直想寻找可以栖息他灵魂和希望的“野地”,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苦苦寻觅,张炜似乎依然没有找到这块“野地”,也可能永远找不到。张炜是孤独的,也是勇敢的。
3 结语
张炜说过:“水土可以养成一个人的血肉,也同样可以养大一个人的灵魂”。他用自己厚重的创作表达了自己的认识与取向,小说寄予了作家的思考和追问,创造出了超越故事本身的内涵,这对当下文坛和现实社会来说,其意义是深刻而远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