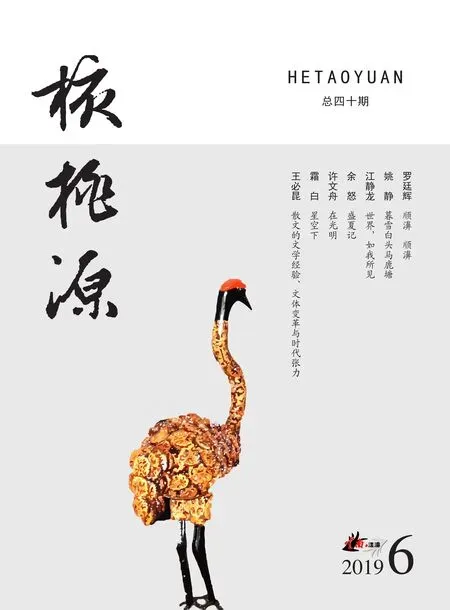边地(组诗)
一匹马的嘶鸣让大地更加辽阔
一只鹰的飞翔让天空更加高远
一阵风吹过
隐藏在草中的白云急切地咩咩
揭开你的锅盖
我就给你下锅的肉
离神最近的就是那条神秘的暗河
离灶膛最近的是我热烈的爱情
云杉和杏树
院子里有一棵云杉和一棵杏树
杏树寂寞了就开花,结果,招蜂引蝶
叶子也随时序更迭而变换着装束
云杉四季穿一身绿外套
抱紧膀子,使劲往高处窜
两棵树,像极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两棵树,忠诚着一座院落
后花园
我乐意结识这些细微的植物
它们或许叫、狼毒、牛耳朵叶子、狗尾巴花
或许不是
我乐意与它们为邻
我已经被挤在水泥丛林凌空的一角
犹如站在悬崖边上
老家这一处幽静的后花园
每一根枝条都在自由地伸展
每一片叶子都在尽情地呼吸
即使枯萎,也有干净的薄霜遮掩哀荣
西北风
把牛吹成皮,把皮吹成鼓
把鼓吹成一声叹息
西北风是一曲欢乐的挽歌
我问苍天:一场风到底还能走多远?
有一个村庄的名字叫喊叫水
一噪子喊出来,就有一个撕心裂胆的愿望
水淋淋地跳在地图上。不知道喊了几辈人
黄河水硬是从山后拐了个弯儿
不肯回来。就这样
眼巴巴地喊。地面上到处都是
裂开的嘴巴
我只是回来转转
别问我吃啥,喝啥
别担心我深夜受凉,孤枕难眠
哦,我只是回来转转
车就在门口
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母亲走后,树倒猢狲散
我的乡愁越来越单薄
隔三差五,在梦里沦陷
回家,亦是捡拾让梦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就别再问了吧
多少疼痛都不能说破
破了,就血流不止
在山丹牧场
一束干草,骑着风的骏马
在广袤的牧场狂奔,在秋天深处
一截截残破的城墙,度过了磨难
现归于平静,却又被游人践踏
雄鹰不语,马蹄叩问着沉默的石头
祁连山用一头白雪的银发回答岁月沧桑的奥义
此刻,我多想一个人在高处迎风而立
享受辽阔和生命对宁静的尊重
风在吹,风吹辽阔
我迎风而立,老泪纵横
中年生活
我在这个比镇子稍大一点的城市生活了二十一年
余生必将在此度过
我的老家距此50公里,人们叫它乡下或农村
是我前25年玩耍、念书、拾柴、割草、耕种、
挨饿以及
后来教课的地方
我美好的记忆和梦中的场景都与此有关
我凭着一手文章离开了乡村小学的讲台
在城里娶妻、生子、买房,并混入仕途
成为乡下人眼中的城里人
做过好事,也干过坏事,有些不是我自愿的
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貌似光鲜的生活后面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辛酸与悲苦
我的皮鞋总是粘着故乡的泥土
我也可以花天酒地的生活
但我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写简单的诗,喜欢一个
人独坐
过气的英雄也曾遇见迟暮的美人
彼此相信生活的真实
菊花瘦了,草药入壶,浑身的骨骼都在喊痛
最大的时尚是女儿放学后扑面而来的欢笑
我的同伴,那些生活的宠儿和城市达人
在饭桌上、在酒吧里,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前程、
股市、房价、情人
偶尔拿我的诗人身份做佐料
没有人跟我谈起祖国和诗歌
没有人谈起责任,谈起感恩
没有人怀揣月光,仰望星空。没有人
终于下雪了
一壶烧酒灌醉半生姻缘。甜蜜是站在门口
不敢张声的新娘,爱也开放疼也开放
这花的一生啊!
终于下雪了,纯洁、浪漫而又芬芳
我抿一口酒,再看看窗外
满心的花事成全邻家女儿闺怨的现实
枯 河
做梦都念着血液里畅游的鱼。两岸的芦花
和一群戏水的鸭子……
残存的老树浑身长满苦难的疤痕,忆起
早年在斧声中逃难的情景,那时它们还小
那时河水很大。一条河很果断地说去就去了
连一次让我承认错误的机会都不给
野 草
这里曾诞生过好多英雄,但英雄的头颅
高不过三寸野草。春天来了
满世界都是牛羊的焦躁的呼唤
总有一片绿哥为生命招展。英雄退避三舍
啊野草!今夜你衰败在我的睡眠里
明晨有人发现我女儿有两排茂密的睫毛
花开灿烂,也开寂寞
我只知道她叫地椒子,花开紫色,形体羸弱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风尘女子
我不知道她的学名。百里香
是人们强加给她的一个艺名,庸俗、腐朽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微笑
她的体香。从农历四月到九月
一路紫得发蓝,香得醉人
小小的叶片,细细的茎蔓
和土鳖虫一起,和蜜蜂蝴蝶一起
和狼毒花一起,和狗尾巴花一起
吵闹着西海固干旱板结的土地
我还知道她可以入茶,炮制一味良药
医治被岁月淤积在腹中的胀气
但现在她被历史失传,被风吟诵
潜伏在记忆中的暗香,时常呼唤我的味蕾
让我在某一个时辰忽然惊醒
想起遗忘在乡下多年的妹妹——
一棵草,一朵紫色,一缕幽香
兀自歌唱,兀自凋零
花开灿烂,也开寂寞
故 乡
小时候,从县城、从临沂回家
觉得到了村前南山就到家了
过了几年,从济南、从青岛回家
觉得到了更远些的
莒县平原上的沭河就到家了
前几年,从北京回家
刚过汶河,觉得到了再远些的
齐与莒的交界——穆棱关就到家了
而今,刚刚驶离河北
在黄河大桥的减速带上
我内心咯噔一下,到家啦!
世界越来越小了
我越来越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