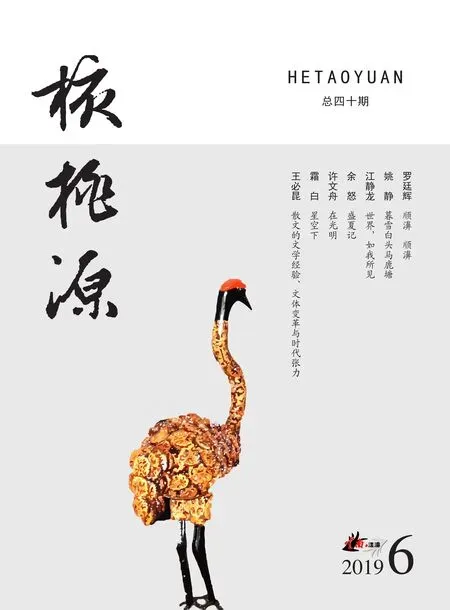人间事
母亲的葬礼
手术室门口的大厅里,我蜷缩在墙角,全身颤抖着,眼泪似决堤的河,在这个寒冷的冬至节里一分一秒煎熬着。外面寒风凛冽,吹响电线的声音,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呜”之声,丝毫没有辜负大理四景“下关风”的盛名。冬至的天分外冷,刻骨地侵蚀着我廋弱的身体,那片风中盘旋的白色,是多么身不由己,所有的祷告都显得苍白无力。母亲跟死神做着坚强的抗争,我甚至相信,母亲为了那个穿军装但未曾戴婚戒的儿子,低声下气地求黑白无常别把她带走。而无情的阎王,最后还是在生死簿上圈掉了母亲的名字。母亲流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两行热泪,两行对儿女和亲人留恋的泪,短暂的一生便定格在了那一条直线上。
母亲出车祸的消息不胫而走。救护车到村外已是凌晨一点多,村里的哥哥嫂嫂弟弟侄儿的都来接母亲,已是等候多时,寒风中烧火取暖。那一刻,我跟母亲说:“妈,这么多的亲人来接您,咱们回家,爸爸还等着您。”世间虽有飞来的横祸,猝不及防的变故,可人间有爱,来自亲情的温暖,就像冬夜里的那一抹火苗,温暖着那一阵阵寒冷。
一切都收拾妥当,鸡都叫过三遍了。年过七旬的大伯(母亲招家,所以我们管大舅、大姨、二姨喊大伯、大姑、二姑)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群里,他扶着母亲的灵柩,静默了好久,掏出兜里早已准备好的白毛巾说道:“妹呀,你素来爱干净,今天哥哥最后给你洗回脸,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好体体面面地出门。”说罢,一把又一把,从头抹到尾,将一口棺材抹了个遍。如何的兄妹情深,才让这个岁月末梢的哥哥在寒冷的冬夜送妹妹最后一程。之后,大伯转而对父亲说:“我妹命苦,苦日子熬到头,好日子刚开始她就忍心丢下我们不管,你得替她好好活着,照顾好这个家。”我无从知道,耄耋之年的大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仍不忘安慰平日里由妹妹一手照顾的体弱多病的妹夫。此时的二姑也已赶到,二姑早年落下病根,一双手抖得厉害,就连说话有时都口齿不清。二姑一上台阶,扶着门框就痛哭,任怎么劝都不停,边哭边说:“早上出去都还好好的,回来就变成这样了,你不是说好叫我等你吃饭,叫你哥等你吃饭,说好买我们爱吃的回来,一起过冬至节的。”天将拂晓之时,大伯牵着二姑走了,不让任何人送他姐弟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祭奠了最心爱的妹妹。
小哥一路风尘仆仆从部队归来,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三天夜里,也是出殡的前一天晚上。那时家里还不通车,下了车还得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披星戴月跌跌撞撞闯进家门,却早已哭成泪人。母亲送哥参军时仿佛昨天,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为国争光,等军旅荣归时也不负母亲的教诲,不成想,再次相见已物是人非,天人永隔。哥哥硬要看母亲最后一面,说什么都不听,说怕以后忘记了母亲的长相,我怕哥哥见了母亲更伤心,哭着哀求他,让母亲体体面面地走,你心里母亲的样子就是最美丽的容颜。
我始终不愿相信躺在棺材里的是母亲。甚至自欺欺人到处找寻母亲,还有母亲最后的影子,最后的温度。我在麦田里找母亲,不见;我在豆地里找母亲,无果;最后,是别人找到躺在菜地里的我,那块母亲出事前一天栽的生菜地里。我无法表达我的痛苦,我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束手无策,不吃不喝不睡,哭到失声,大哥抱着我说:“我求求你别哭了,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要是再有个三好两歹,我们仨怎么跟妈交代。”
按习俗,母亲出殡前,父亲得把一双筷子就着门槛断成两半,一半留在手里,一半落于门外,刀起刀落时,从此一别两宽,阴阳不同路。悲恸的父亲只举了刀,一双筷子也完好地落于门外,回看一眼那个陪了他一生的女人,哽咽着喊出:“起棺!”
出殡的队伍穿过村庄,又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几个唢呐手换着吹送山调,声音凄凉、幽怨。队伍行至半路,也是我送母亲的终点。按风俗,小女儿给母亲献完响午,不准送到坟地。相传,一个远嫁的姑娘得知母亲过世,而家里又一贫如洗,没什么可祭奠母亲,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尽管两手空空,孝顺的女儿也想送母亲最后一程,便日夜兼程地往娘家赶,饿了就喝山泉水,累了就靠树上睡着了,梦里,她见到了母亲,母亲打了只兔子,炖了兔肉给她吃。梦醒后发现,有只兔子死在了脚边,她没有多想,只要有东西祭奠母亲就是最大的安慰,便烤了兔子包在围裙里匆匆赶路。或许,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她在母亲出殡的三岔路口赶上了,于是将就点上三柱香火,将包在围裙里的兔肉倒在树叶上祭拜母亲,一曲路祭调里把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融进泥里,让清风捎去。眼下,我空有一腔的思念,也有丰厚的祭品,却没有什么调子相送。只有早早在那里等候母亲的三个大妈,她们是昔日里母亲的好姐妹,也是来送母亲最后一程。三个被岁月催老的妇人,断断续续的苦情调,用她们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姐妹情深。
毫无征兆地,母亲走完了她仓促的一生,连同她对世间的留恋,一并带进土堆,躺进了那草木的深处。
忆奶奶
因母亲招婿入赘,于是外婆变成了奶奶,那个小脚老太太。
听母亲讲,奶奶是地主家的姑娘,是四乡里出类拔萃的美人。印象中,对爷爷是寡淡的,甚至在路上遇到爷爷,我都不屑跟他讲话,以至于爷爷到弥留之际,我都没看清楚爷爷的长相。
奶奶并非嫁给了爱情,而是嫁给了世俗。在含苞待放的年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华里,却被嗜赌如命的哥哥抵债给了爷爷。奶奶不愿嫁给爷爷,或许她心里早就有了意中人,或许她从骨子里就看不上同样爱赌的爷爷,她抗拒过这桩婚姻,甚至以死相逼。奶奶一次次地出逃,却换来了毒打,有次还被拴在柱子上两天,不吃不喝。我无从知道,亦无法想象奶奶经历了怎样的遭遇,怎样的痛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是个孤儿,独自漂泊的父亲自然懂事得早,还腌得一手好的辣椒酱。当年我父亲上我奶奶家说亲时,给我奶奶带了罐腌辣椒,还信誓旦旦地说:“娘,我有一碗面糊,我都要香儿先吃饱,我从小没爹没娘的,您就是我的亲娘,等您老了,香儿和我给您养老送终”。奶奶深信父亲,她要让母亲嫁给爱情。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一贫如洗的家里只有简单的一套行李和一头小猪。父亲践行着他的诺言,他爱母亲,也深爱着我们,把奶奶当亲生母亲一样侍奉,对爷爷也是偷偷地照顾着。
奶奶的性格也如她的名字般。她一生爱干净,心地善良,就如同那朵开在雪中的梅花,素净淡雅,简单而不失高贵。记忆中,奶奶的头帕是黑细纱的,缠着轻巧,比缠黑粗布的美观大方。她总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长衫,打过补丁的裤子,在奶奶身上也看不到破旧不堪的感觉。每每早起,奶奶总在火塘边烤早茶喝,一个小泥罐,一小把茶叶,还有头天晚上攒下的一小块麦饼或是一小坨冷苞谷饭。奶奶娴熟地掂烤着,时不时凑到鼻前闻闻火候,在她认为最恰当的时机里,倒上早烧好的开水,“滋哩”一声茶水溢出罐口,茶香立马四散开去,弥漫在整间屋子里。奶奶总把第一杯茶敬了茶神,半杯茶水与额同齐,闭眼,静默,微动唇,把茶水按顺时针洒在火塘边。第二杯看茶桩,看看一天的财运、时运,呷一口凝神,品烤的技艺。第三杯,她才会就着早烤黄的麦饼或饭团,慢慢品着,慢慢品着她浮沉的人生。
奶奶总吓唬我:“不听话,背娃娃的人来了,把你背走。”我怕呀,可我也调皮,再说了,奶奶舍不得,她是拿命去护我周全的人。“背娃娃”的人也是季节性地来,不是随时都来的。每年秋收结束,小季下完,抬着大口袋,穿着怪异打着包头的外乡人就进村了,成群结伴挨家挨户地讨粮食,什么都要,谷子、玉米、面粉、南瓜、黄豆、辣椒,只要你给,他们都要。这个刚给了盆苞谷,那个又接着来讨,真就门庭若市。善良的奶奶总不让来人失望,可他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我们的失望之上。有次,奶奶把半柜苞谷分给了组团讨粮食的“背娃娃”人,母亲气愤之余对奶奶说,“您把家里几个月的口粮给了他们,您的孙子孙女就得喝西北风了。”奶奶总觉得那些年底还出来讨粮食的人可怜,能接济就尽量接济一下,家里多吃点瓜果蔬菜也就挺过去了。
奶奶的晚年还学会了抽烟。父亲总抽着烟锅,却给奶奶买了“两头出气”,从刚开始的金沙江到“青蛙皮”(春城烟),再到后来的带把烟(春城烟过滤嘴)。奶奶抽烟时,总靠在柱子上遥望着村口,复杂的眼神充满期待,除了等待亲人归来,是否还在等一个不归人,抑或是想走出村口去看看大山外的世界,这些我都不得而知。她每每吸口烟,都会剧烈地咳嗽,靠着柱子,看烟圈里的人生,一吸一吐间,释放着大半生的沉重。待抽到一半时,掐灭烟头,连同自制的锡箔纸烟嘴一起小心翼翼地收好。
奶奶溺爱我的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记得我上小学时,有次中午放学晚了,奶奶送饭到学校,告诉老师:“我家燕子体弱多病,怕饿坏了,请老师准假,先给我家妞把饭吃完,老师再给她上课。”然后,从围裙里拿出用毛巾包裹的小搪瓷杯递给老师,自己却坐在杨柳树下看我狼吞虎咽。有个高年级的学生总欺负我是黑人(没户口,超生),为此我都不想去学校,想逃课。奶奶揽我入怀,心疼地抚摸我稀疏的卷发,抑郁自己无能为力。奶奶教我:下次有人再逗你,你就告诉他,我俩拿面大镜子比比,谁比谁黑。奶奶这招果然灵验。
奶奶帮衬母亲,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年迈的奶奶尽其力量地操持着家务,除了变着花样地做两顿饭,还去侍弄菜地,田里薅草,割猪食牛草。母亲担心奶奶上了年纪,跌倒摔伤,不让她去田间地头,只让做两顿饭,她就说她老了不中用,说母亲开始嫌弃她。说真的,即使奶奶上了年纪,做的饭菜依旧清秀可口,荞麦饭、苞谷饭、麦疙瘩饭吃着不燥,还软口,馒头蒸得是松松软软的,锅里炕的麦饼也是香脆有加。每年冬月里,奶奶总把老点的青菜洗好,晾到半干,腌成咸菜装在土罐里封存,嫩点的洗好焯水,用棕叶拴好,挂在点点含苞的梅子树上,随风变成干板菜,来年没了绿菜也不愁。咸菜炒葱,咸菜炒豆米,咸菜拌鱼腥菜,下饭,下杂粮饭。
天有不测,老来摊祸。奶奶最后的岁月里中风卧床,那时的我已经上四年级,要到离家三公里的完小寄宿,周末才回家。奶奶瘦成了干柴棒,皮包骨,深陷的眼窝令我无助,母亲偷偷抹泪时,我大概知道了奶奶将不久人世。我把零花钱攒了给奶奶买麦芽糖,那是奶奶儿时一个老姐妹做的,奶奶嫌黑乎乎的不干净,叫我以后不许再买,岂知奶奶是心疼我的懂事,我还当了真。周末的任务是看护奶奶,我总把奶奶背到院子里晒太阳,给她洗打结的头发,再次编好扎起,洗澡换衣服,给她按摩毫无知觉的三寸金莲,讲学校里有趣的事情,看奶奶的两行清泪,听咿呀不清的酸楚。
奶奶在我五年级的那年去了远方,在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周三午后,独自一个人前行,不再归来,就如她来时一样孤单。熟悉的音容定格在了相框里,从床上,移到了墙上。
捉知了
今年的夏天尤其酷热,没有雨,去大蔳河捉知了的人就更多了。不知是何缘故,大蔳河有一段两三百米的河沟,有大知了,是知了家族里的高音歌唱家,被称作“双鼓手”。嘴馋的我怎可每年都看朋友圈的老铁们吃,与妯娌不谋而合后,水田里泡一天的我俩,跟着大部队踏上了捉知了的旅程。摩托车骑行了十七八公里,由柏油路换水泥路,再到坑坑洼洼的林区土路,终点是一个废弃矿场的小河沟。天刚擦黑,就有很多人静候着,人手一盏手电筒,兜里揣着塑料袋,都卯足了劲,等知了停在河沟里。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所有捉知了的人都屏住呼吸,很少交谈,怕知了听见人声而飞走。是我这个门外汉打破了寂静:“奇怪了,怎么知了在这才有,别处没有。”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之后,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说是因为有矿的缘故,矿里有一种特殊成分,吸引了成群的知了。有说是天气炎热,知了叫了一天,渴坏了来补充水分。也有人说月朗星稀夜没有知了,夜黑风高时才有,跟天气有关。也可能是知了交配的季节……似乎都有道理。我蹲在一块大石头上,看虫影掠过,揉揉眼,还是模糊一片,不知是天太黑,还是视力又下降了。凉风习习,鼻子里闻见河沟里特有的鱼腥味,耳朵里听见这夏夜里青蛙和蛐蛐的叫声。大蔳河的夜如此美妙,想把我们吞噬掉,而我们又想把知了吞食掉。正当我陷入无限遐想的时候,听到“大伙准备准备,开始了。”之后,齐刷刷的亮光都往河边走去。
首战告捷,巴掌大的一点小沙滩上,五只“双鼓手”被我成功擒获,“呁……”一长声中,知了在我手中作无用地抗争,我兴奋地尖叫着,同伴们却不动声色地向下游移动。我仔细地搜寻着战利品,一次次尖叫着装进塑料瓶里,兴奋之余,不小心踩翻了石头,一个趔趄掉进河里,洗了个“冷水澡”。塑料瓶没盖,“双鼓手”们趁乱逃逸,还是被河水带走了,我惊慌失措地从河里爬出来,它们已不见了踪影。半小时后,所有人都看见了那个在夏夜里瑟瑟发抖的捉知了的狼狈不堪的我,兜里还揣着十三只“双鼓手”回家。
记得小时候,我也曾跟着小哥去捉知了。与其说是捉,实质是粘。砍一根细长的木棍,捡一小截父亲编背篓剩下的细竹签,弯曲后绑在木棍顶端,缠上果树上的蜘蛛网,一个捕知了神器便诞生了。说到蜘蛛网,不是什么蜘蛛网都能粘到知了,只能选韧性最好的那种。小哥总能在核桃树、果树上寻到最优质的蜘蛛网,缠好,放到人畜碰不到的地方,中午放学后,带我粘上一两只知了后,小心揣在兜里,拿回家让母亲用缝衣线绑好,供我玩耍半天。没上学的我,知了便成了我的玩偶。小手牵着知了遛弯,知了抓着床单、被子、衣服不放手,气急败坏的我硬是给它拽下来丢在地上,拖着走,知了就使出绝招对付我:装死。结果是,我以为它真的死了,遛到后面,我只牵着空线头,伺机夺食的老母鸡发了财。我哭得一脸鼻涕,踹着让老母鸡还我知了。
童年的时光总是美好的,哥哥们极疼爱我这个妹妹,比我现在疼爱俩个“小情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末,大宝从学校归来,饭后带弟弟玩耍,无意中发现白天加水洗车未干的沙石地上有知了,但不是“双鼓手”,是极小的知了,两宝立即兴奋起来,打着手电,猫着腰,来来回回地捉起了知了,每收获一只知了,都喊着“妈妈、妈妈”,直到没再见到知了,整块场地翻了无数遍,还意犹未尽。
次日早上,我们仨将知了认真地剪去翅膀,清洗、焯水、晾干,油锅翻腾时,那特有的香味足以飘回到故乡,飘回到我的童年,不让母鸡抢了鲜香,我想来一口油滋滋的脆香,我吃知了肚子,身子和头留给哥哥,天真的笑声从我的虫牙溜过,滑过我稀疏发黄的发间,停留在母亲的怀里,定格在那幸福的一瞬间。而小宝遗传了老公的体质,几小只油炸知了路过喉咙,胃里稍作停留时便肚子疼,之后,全身长起了痘子,慌乱中带孩子跑到医院,诊断结果,高蛋白过敏。此后,心留余悸。
朋友圈的知了熟了,一如既往的,隔着屏都闻到了脆香。这次,我只是看看,没再有想法,就看看。
赶毛驴的女人
晨露还未隐去,东方发着鱼肚白,群起的鸟儿弹奏着交响乐,盖过了昔日此起彼伏的鸡鸣声。
宁静的山村经过一夜的休整,又鲜活了起来,昨夜睡下时的疲惫,已全然不在。该干嘛还是干嘛,不是收就是种,简单而重复。女人赶着毛驴,驮了两筐粪,不紧不慢地跟着,她不急着吆喝牲口,停停走走地,任由毛驴随性地走着。这条路女人走了很多年,很多年,久得连她都快忘了多少年。路边的树木依旧,土丘依旧,田地依旧,如果硬是要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来去时带走的尘土,和毛驴发现了干燥的初夏里昨夜新吐的草芽。它驮着粪时看了一眼,还小。
一路下坡,山路蜿蜒崎岖。女人穿着自己缝的千层底,这是作为一个彝家女人必有的生存技能。鞋帮上绣着蝴蝶采花,两只蝴蝶绣得栩栩如生,只可惜这两只蝴蝶,此时此刻它们已然是两只泥蝴蝶了,花香全变了泥土味,掺和着驴粪牛尿的味道。
女人踮了踮肩上的背篓,感觉又沉了点,走了几步,看见路边光滑的土堆,眼睛不自觉地扫了一眼,把背篓放在土堆上,绳子挪离肩,后背抵着背篓,脚呈七十度弯曲着站立,右手习惯性地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腮帮鼓起,长嘘了一口气。
“蹄踏、蹄踏。”到了麦地里,女人娴熟地低头、弯腰,右肩往前一送,把粪从背篓倒进地里。女人斜身低头,抖去脖子上的粪渣,放下背篓,拔了一把绿燕麦给毛驴吃。转身从驮子上把粪筐卸下来。而每卸一筐,她都斜站着,怕粪沾了一身。事实是,再怎么小心,鞋上的蝴蝶还是“吃”了粪,吃了带有好几种气味的粪。
趁空闲的档,女人要给空背篓添点东西,她麻利地拔着绿燕麦,这是给小毛驴备下夜点,“马无夜草不肥”,小毛驴虽不是马,却是女人强有力的帮手。还有那结了果的车前草,也没逃过女人的手,一并带回家,喂了圈里的过年猪。
缠在羊巴巴树上的那蓬黑泡果,昨夜又熟了好多,黑得诱人,稍微一碰,黑色的汁液便流了下来,沾着哪儿都留下紫黑色的一片。还好,小鸟没发现。女人抖抖手上的土,眼里流露着惊喜的神色,喉结微微动了动。一摘一送间,黑泡果迅速地通过喉咙,直达胃里,成为最真实的早点。留在舌头上的紫黑色,证明那些黑果子刚刚路过了此地。
女人拍拍毛驴的头,轻抚到鼻孔,“大毛,这回你可不许半路撂挑子了啊,这麦穗可要给小毛换生活费的。”女人熟练地拴好一驮麦子,俩个筐重叠着架在鞍心,已是满头大汗。她将右手当梳子,随便“梳”了几下,把凌乱的头发盘好,拿衣襟擦去满脸的汗,原本细密的皱纹似乎又深了一点,岁月,终是辜负了这朵村花。
男人说:“我出去打工养活你们,你乖乖帮我带好孩子,看好家。”女人送过山垭口,还朝男人离去的方向喊“早点回来。”男人带走了吃喝嫖赌,带走了女人对丈夫的期盼,也带走了儿子对父亲的依恋。男人走时,儿子九岁,男人三十二岁。如今,儿子上初三,男人没有归期。
小毛驴驮着沉甸甸的麦驮,没有回头偷着吃,一路上坡前行。山顶露出了第一缕暖阳,瘦瘦的,照在核桃树上,把核桃果也拉成瘦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