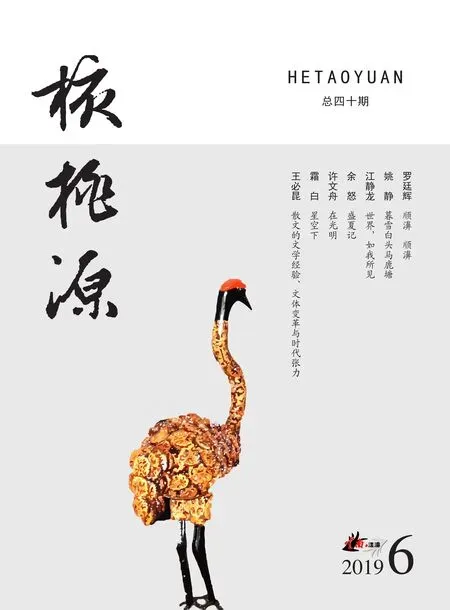旋转36度
一
张敞站在窗前看那个女人很久了,女人黄色运动衣,一条蓝色牛仔裤,很简单的装束。齐肩的长发柔顺地垂下来,她正坐在墙根阴影下低头看书,看得很认真。正值四月,漫天柳絮沸沸扬扬,落了女孩一头一肩。但她依旧无动于衷,仿佛被书里什么故事吸引了,就是这样很平淡的场景,让张敞无来由的有些感动,张敞已经不年轻了,见惯了很多事,真的假的,丑的美的,爱的恨的,甚至他看淡了生死,他觉得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他感动的了。
看着女人,不知怎的他就想起萧翎来,算来他和萧翎认识也有四十多年了,他和萧翎是前后院,他家在前院,萧翎在后院。萧翎搬来那年正是秋天,火红的枫叶像火一样铺了一路,张敞就在一个上学的清晨碰见了同样上学的萧翎,那时他还年轻,喜欢美好的事物,萧翎就是美的,美得像幅画,简单而自然。对,他一下找到自己为什么专注女孩的原因了,简单,自然,还有书卷气。
张敞年轻时喜欢读书,萧翎也喜欢读书,他们鸿雁传书是各种文学书籍,中国的外国的。那时萧翎梳着短发,穿着男孩子似得运动衣,甩着两条麻杆似的胳膊走在他的右侧,青春而张扬。张敞比萧翎大五岁,张敞大学快毕业了,萧翎才高三。她叫他张敞,敞字拉得很长,语调向上扬,有些调侃的味道。张敞不介意,很多时候他觉得萧翎就是另一个他自己。他两都喜欢文学,他们彼此传递着书,读完在互相交流感想。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张敞精神世界一直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现实中从来都是理性的。他知道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人要活在现实中。对于这点他的妻子晓华是不懂得的,晓华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女人,作为一名普通护士,她除了工作就是锅碗瓢盆,老公、儿子那才是她的中心轴,她身上更多是随遇而安,但这并不排斥她欣赏有才华的男人,张敞是这样男人,张敞的阳光和才气由内而外自然散发。而晓华身上更多是温柔和内敛的传统女人气质,这让张敞心神安稳,踏实。张敞不喜欢女孩子咋咋唬唬,女子无才便是德,张敞注重后者,现在有才华的女人太多了,但是能驾驭得了的太少了。结婚一定是要本分的,晓华够本分,是个贤内助。
但萧翎不是,这点张敞心里清楚。萧翎不但傲气还有点小资,她说有才气女人都小资并清高,比如张爱玲,比如三毛,比如林徽因……张敞说她有她们的傲气,没有她们的才气。他甚至可以想到萧翎未来的样子,穿一条丹比奴卡其色长裙,一双迪狐银白色高跟鞋,系一条浅色爱马仕丝巾,手提新款的lv包仰着头跟他说话,眼里满是不屑。他承认萧翎在讨论文学时脸上散发的光采令他心动,但爱情是一回事,婚姻是另外一回事。
张敞起身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这个便利店买来的廉价暖壶并不怎么保温。张敞叹了口气,炎炎走了五天了,估计快回来了。他不想再费心思了。毕竟他不是当初的张敞了,萧翎也不是当初的萧翎了。但是过去的事总是存在过呀,有时候张敞又想,如果当初他和萧翎走在一起,那么也就没有炎炎了,或者炎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笑了笑,笑自己年过半百还有这种可笑的念头。日子总是回不去的。
炎炎说:“爸,我已经联系好了北京301医院专家,我们明天就去看病。”
小霞看一眼炎炎,一只手抚着高高隆起的肚子,一边把玩一个透明水晶球。
“可是我快生了。”她面无表情地说。
“不会耽误很久的,老婆,我很快就回来,你放心。”炎炎说一句笑一下。
张敞觉得儿子哪都好,就是对老婆实在是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这点不像他。小霞斜眼看看炎炎,又看看面沉似水的张敞,她把手里的水晶球掷出去,水晶球掉在地上,蹦蹦蹦连跳几个高,叽里咕噜钻到电视柜下面去了。炎炎看眼小霞,又看看张敞,转头进了里屋。张敞啥也没说,他坐在那里一动没动,脸色变了几变,压了下来,他知道,虽然他心里憋着一股火,但是这个面子他还是要替炎炎撑下去。
如今的他只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人,不,是一个病老人。不管怎样说有炎炎这么孝顺的儿子还是满足的,前阵子三单元的老魏还说:“张敞啊,你看你多好,有炎炎这样孝顺儿子知冷知热。大家都这么说。”
张敞只能笑着点头,自己的儿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这些他懂。更何况炎炎有自己的为难之处。
老魏说对面楼里那个老马前阵子死了,死的那个凄凉啊,老魏说的时候咂着嘴,一连串的啧啧啧,张敞顶讨厌老魏这个口气,还有他动不动就伸出的兰花指,跟娘们似得,以前他总会半玩笑半认真地看着老魏说:俺是纯爷们,然后就没了下文。
老魏乜他一眼:“我知道。我也是纯爷们。”说完哈哈大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纯爷们成了调侃的词语。但是现在他不敢说了,自从得了这个病,他就沉默了许多。仿佛一下子他就从盛年跌进了老年。
张敞有些牵强地接起话头:“老马怎么死了?”
“听说他早上锻炼时候嘚瑟,非要去单杠上甩,他以为自己还是小伙子呢,结果从单杠上摔下来,你想想,本来就六七十岁的人了,这一下摔坏了胯骨,他又没有炎炎那样的儿子,自己去医院开点药,以为养一阵就好了,结果没想到越来越厉害,到最后不能动,吃喝拉撒没人伺候……”
“他不是有个姑娘么?”张敞记得老马那个姑娘的,头发染得跟火烧云似得,脸搽得跟唱戏似得,打扮妖妖道道。
“他那个姑娘还能指望上?”老魏撇着嘴又一串语气词。“她去老马那里哪次空手过?把老马的家底都倒腾回自己家了。”老魏又一顿啧啧啧。
“刚开始还三天两头去看看他,后来借口忙请了一个保姆一丢,也就不管了。从得病到去年也不过半年多时间,生生把个老马就这样葬送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更别说……”
老魏正要说什么,看到儿子魏刚从对面像座黑铁塔似得走过来,他拍拍张敞肩膀:“我们啊,身体健康最要紧。”然后笑脸迎着儿子回家了。
二
张敞总在想自己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他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比如那天他锁门时候明明手里攥着钥匙,自己却满世界找;还比如他从商场出来时候会在某一刻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比如他常常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却会忘了刚刚发生的事;还比如他看什么东西越来越模糊,听力也在衰退。前几年吧他晨跑时还是蛮有活力的,两圈下来面不红,气不喘。但是现在每天楼上楼下转个圈浑身就散架似得。
一个声音在心底嘲笑他:张敞,你老了。
我老了么?真的老了?但是他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啊,他平时很少照镜子,他觉得照镜子那是女人的事,他以前总是笑话晓华一天照八百遍镜子,那时他想:女人,呵呵,就是怕老。但是那天他无意中一抬头看到镜子里一个满目苍桑,面容憔悴的老人站在镜子里,他就呆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一直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啊。居民楼的人都羡慕张敞越来越年轻呢。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炎炎结婚后,还是晓华突然离世后?镜子里的那张脸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头发和鬓角一下就白了,像霜染的似得。他的身材也一下就佝偻了。晓华离世没多久他就经常晕厥,他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开始他以为是自己伤心过度,没有理会,但是某一天清晨醒来他看到家里的屋子突然倾斜,他紧张起来,连忙跌跌撞撞喊了炎炎,炎炎带他去医院,经过一系列繁杂检查后,医生说是颅内垂体肿瘤对视交叉的压迫形成的视神经萎缩,对于这些名称张敞记不住,儿子告诉他只是斜视,慢慢调养就好了。炎炎说的轻松,但是他心里并不轻松,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那以后他的视角经常会出现三十六度倾斜,三十六度的世界颠覆了他所有自信。他感觉自己一下就被岁月抛弃到世界另一边了。也许他就要变成第二个老马了。
他看着炎炎矫健的步伐,每走一步,个头就窜一窜,像一颗蓬勃生长的向日葵。还有那浓浓的眉眼,秀气的五官,那分明是另一个自己。这么看着看着他就恍惚了,在心里他一遍遍问自己:从那蹦出来这么大的儿子?而他分明记得他和萧翎在树林里读书还是昨天的事啊。
薄薄的雾气在树林的空隙间慢慢穿行,初升的太阳把树叶照得金黄金黄。连同他们那张洋溢着青春而含蓄的脸孔都生动如初。那时候他就是炎炎这个活力满满的样子。萧翎和他并肩坐在树林里那块青石上一起读《红与黑》《巴黎圣母院》《茶花女》,还有……萧翎修长的手指在一行行字迹里划过:“我看到这了,你看哪了?”她回头看他一眼,看他无动于衷,调皮地把他蓝色鸭舌帽檐又拉下来,张敞向上提提帽檐,伸出手想教训一下这个捣蛋鬼,萧翎望着他却低了头,她把胸前的玉佛含在嘴里红了脸转过去,他们眼神从书里溜出来又溜出去。
一团毛茸茸柳絮没头没脑突然就向着张敞撞过来,张敞有些懊恼地挥挥手打散这些讨厌的东西,侧脸避开那些柳絮,伸手把窗纱关上。楼下那个女孩还在看书,只是他们现在隔了一层窗纱,有了朦朦胧胧的距离。放佛两个世界。她在看什么书?这么入神?是文学么?
现在大早上就看书的女人可不多,尤其还是在这样一个大杂院,周边全是外地打工的,人们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大多是去赶着上班,或者忙业务,而她与世隔绝的悠闲似乎和这个氛围不太协调。他们来北京好几天了,医生说张敞需要住院手术,但是医院目前没有空病床,只能等一阵子,这一阵子不知道是多久,所以炎炎托人在北京六环找了这么一个小公寓让张敞先住下来,他再想别的办法。张敞从患病到现在倒是无所谓了,他慢慢接受了自己的病,就像习惯了一个并不欢迎的客人,客人不走他怎么办?除了有时候旋转三十六度外,别的没啥毛病。他自己宽慰着。炎炎留下一些钱,叮嘱张敞不要随便出去,吃饭啥的可以叫外卖。他说媳妇马上要生了他不放心要回家看看,好在离北京也不太远,几个小时就能赶回来。炎炎脸上红扑扑的,像抹了一层油彩,额头还冒着细密的汗珠。看着两头忙的炎炎,张敞有些愧疚,如果晓华在,自己就不会这样了。
他又一次想起晓华,只有晓华让他感觉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温馨和舒适。每天从跨进家门的第一步,他就开始享受帝王级的待遇,茶水永远是在进家门一刻递到手上,饭吃完了不用他动手,晓华自会主动满上,他的衣服永远是整洁如新,无论他什么时候什么心情回去这个叫家的地方,都会让他的心瞬间安定下来。包括儿子炎炎的出世,也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压力和烦恼。一切都有晓华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家的味道,也是晓华的味道。母亲说这是他的福气,他得意自己选对了人。但是为什么在静下心来的时候,他的脑子总会有意无意的有另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现在晓华不在了,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给儿子添了累赘,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没用。他挥着手让炎炎赶紧回去,说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炎炎又叮嘱了张敞一些,才狠狠心走了。
三
炎炎走了,就剩下他自己,诺大的北京城他不敢乱走,他怕自己犯了病给儿子添乱。所以他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这女人以前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也许是他以前心情不好忽略了,也许是女人之前并没有看书,没有引起他足够的兴趣?总之在这样一个早晨,被张敞发现了,四楼的距离有些远,她低着眉眼看不甚清楚,从她窈窕的身材看,年龄大约在三十,也许还要年轻些。年轻真好。张敞心里又一次感慨着。但是他又注意到了不远处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推着一个小车蹒跚学步,那是她的孩子吗?她是做什么的,保姆还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这些在张敞心里只是打了一个问号,他现在没有激情了,如果是当年,他一定会下楼和她侃几句,他是能说的,也是会说的。他和萧翎争论起书里的人物,往往萧翎都会败下阵来,那时萧翎总是调侃张敞适合做一个讲师而不是普通公务员。张敞说安娜是咎由自取,谁让她不自尊自爱了,如果安娜和简一样,那么就不会是那样下场。萧翎说他不懂爱情,爱情是什么?张敞头一扬,额前刘海一下甩上去,露出光洁的额头,清俊的脸孔,他双眉一挑说:“爱情几斤几两,爱情能当饭吃么?”
他对萧翎说:“我觉得女人应该像郝思嘉那样光彩夺目,永不放弃。”
萧翎看着他沉默半晌,眼底的两团火焰渐渐熄了下去,她忿忿地扔了书头也不回地往回走:“好吧,达西先生。但愿你能找到那样的精神伴侣。”张敞看着萧翎像两根倔树枝一样一甩一甩的胳膊,在那条水粉色纱巾里忽隐忽现,连同她纤细的身材消失在视野里,他追出几步冲着萧翎的背影嚷:你个神经病!他负气地把帽子扔在青石上呼呼喘气。再后来萧翎就很少找什么借口请教张敞了,张敞一直搞不清萧翎的态度。其实张敞自己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女人,比如晓华常说他不够浪漫,不够体贴。抱怨她过生日连礼物也没有,萧翎在这点上和晓华保持高度统一。
她说的时候好像是漫不经心的口气:“张敞……”
对,萧翎一直是这样称呼他,她不叫他张大哥,或者他的小名敞子,而是连名带姓一起称呼。好像他们不是邻居,倒像是多年的同窗同学。
她说:“张敞,你对嫂子要用心啊。”她说完看一眼晓华。
晓华娇嗔张敞一眼,拍着萧翎的手背说:“翎子,你不知道你哥他就是个书呆子,对他讲那些,就是对牛弹琴。”
萧翎看一眼张敞:“不是啊,张敞要做白瑞德呢”她绿色的水滴耳环一颤一颤的。
“白瑞德是谁?”晓华看着萧翎眯起眼睛笑,“你俩啊,都是文化人,我看倒是很般配呢。”
萧翎把脸转到窗外,太阳下薄薄的耳廓像煮熟的虾子似得。她看着洒水车轰隆隆开过来,水花溅在马路上,马路牙上一些尘土被水淋湿,有些呛人的味道。
“嫂子,我怎么配得上张敞?他要的是贤妻良母,我啊,只会吃不会做,而且野得很,他怕我辖制他呢,对不对张敞?”她仍侧着脸抬了下胳膊,白嫩的手腕上莹绿色的翡翠手串滑下来,似流动的水珠划了晓华的眼。
晓华目光从这头唆到那头,好像一根听诊器,仔细探视着他们心脏之间的微妙变化。
张敞看也没看萧翎,他的目光落在大街中央那座女神像上,那雕像好像是前些年搬来的,这座仿制雕像立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四线城市,不伦不类颇有些滑稽。
晓华和萧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讲得很是亲热,张敞只能不停地夹菜。除了吃,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晓华叹气归叹气,她知道日子还是要过的,张敞这种男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不会有什么波澜的。张敞说过日子当然是平平淡淡,难不成还把家搞成俱乐部?
就是那一天以后,张敞再也没见过萧翎,晓华坐在床上织着一件浅灰色毛衣袖子,银色的毛衣针在她的手指下像只探头探脑的老鼠一闪一闪的,她的眼神瞟过去淡淡地对张敞说:“萧翎去美国深造去了。”阳光照进眼里热辣辣的。张敞放下手里那本加缪的《局外人》慢慢走到窗前,桃花又开了,粉嘟嘟的缀满枝头,那么艳丽,那么喜庆,但是张敞的心却空了好大一块。
四
张敞很想知道那女人看得是什么书,但是他知道那只是很想,并不能代表他可以付诸行动。女孩的身体渐渐倾斜起来,连带她的坐姿,包括周围的房舍,如同一副美丽的油画插入了一些不规则形条,整个画框都是倾斜的,有些扭曲或者诡异。
张敞揉了揉眼睛,有些轻微晕眩。他讨厌这种感觉,就像讨厌萧翎指着他说:“张敞,你有一天会明白的。也会后悔的。”张敞想,不,他才不要后悔。他在屋子里伸伸腰,踢踢腿,他想他还年轻,等手术做完,他要去大理和海南转一圈,晓华生前一直想去大理和海南,她说她喜欢大理典雅古朴的风情,也想去海南看看大海,听说那里有块天涯海角石,她想想就有一种到天尽头欢喜雀跃的感觉。看着晓华孩子似的笑容,张敞不能拒绝。
但是她们的计划每次都被各种各样事情羁绊了,直到她弥留之际,她握着他的手,在他手心写了一个石字,张敞就明白了,他流着泪拼命点头,晓华看着他温柔地笑,眼里是说不出的眷恋。想起这些,张敞心里仿佛就有一把刀一点一点把他割开,让他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点发现晓华身体上的不适,那么晓华就不会过早离开;如果他多一点时间帮助晓华做家务,晓华也不会自己每天忙来忙去;如果他对晓华再稍微用心些,晓华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他亏欠晓华太多太多了。在晓华走后的每一个寂冷夜里都有一种噬心刻骨的疼痛窜入四肢百骸。现在他唯一能弥补的就是完成她生前的梦想。然后,然后他要重新制定一下读书计划,这次他不准备读文学了,他想先从叔本华和米兰昆德拉看起。
楼下女人合上书站起来,去牵小男孩的手,张敞看到她手中黄色的封面很熟悉,应该是鲁迅的《野草集》。张敞笑了,他想等萧翎从美国回来,倒是可以把女人引荐给她做学生。他又开始头晕了,他坐在床上用手支着脑袋,等那种排山倒海气势下去,才缓了一口气。最近他的晕眩越来越频繁了,他知道这不是女人的原因。也不是萧翎的原因。他数数钱包里的钱,又有些气馁地叹了口气。从二手冰箱里翻出一个前几天剩下的面包,还有一袋榨菜,倒了杯水,他把面包撕碎一点一点塞进嘴里。
他突然想起家里那些他曾经视若珍宝如今落满尘埃的书籍,他想起萧翎去美国后寄给他的翡翠手串和那个玉佛,还有晓华好像说在茶几下的抽屉里留给他一封信,还有写了他名字的存折和房产证,还有……他想趁现在还没手术,应该做些什么,他离开椅子,找了炎炎留下的信纸和一根笔,趴在那张简易桌子上,思索一会儿在纸的上方写了两个字,然后他看着窗外蓝蓝的天,想起有人说过一句话:一个图形绕着某一点旋转三十六度,经过五次这样的旋转后,恰好与自身重合,则这个图形一定是中心对称图形。
张敞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