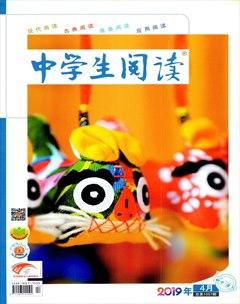父亲的手
林少华

父亲病倒了。突然之间。脑溢血。
出了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闭着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动,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声“爸爸……”。他的手明显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声,他又回握了一下。
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毕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
那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宽、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没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肤下显得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软软的。
我看着、攥着、抚摸着。我忽然察觉,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父亲的手——自懂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我居然从未接触过父亲的手!我感到惊愕。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是父子,见面或分别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没有接触的机会吗?没有,没有,是没有。我疏远了父亲的手。想到这里,我心疼地把父亲的一只手捧在怀里,注视着、摩挲着,眼睛随之模糊起来……
尽管生活、工作在乡下,但父亲的这双手几乎没做过农活儿,更没做过家务,也不会,甚至连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都不太会。但我必须承认父亲是个很聪明也很努力的人。父亲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乡供销社到县供销总社,后来转到人民公社即现今的镇政府。
同样是这双手,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别说十里八村,即便在整个县当时都是有些名气的。
可惜他脾气不好。同样一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让领导听起来不大舒坦。所谓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辈子都没升上去。
我继续搜寻记忆。搜寻父亲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间留下的痕迹。记得大学三年级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住在长春偏离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里。“文革”尚未结束,物资奇缺,连白糖都凭票供应,平时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对肝炎患者来说,糖是最基本的营养品。
一天中午,我在医院病床上怅怅地躺着。几个病友都睡了,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误的课,想入党申请能否通过。正想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竟是父亲。依旧那身半旧的蓝布衣裤,依旧那个塑料提包,依旧那副清瘦的面容。
我爬起身,父亲在床沿坐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然后一只手拉开提包,另一只手从中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白糖。又一个一个小心地摸出二十个煮鸡蛋,最后从怀里摸出二十元钱放在我眼前的褥单上。
父亲一个月工资四十七元五角,母亲没工作。八口之家,两地分居。作为长子,我当然知道这二十元钱意味着什么。我说钱我不要。父亲没作声,一只手把钱按在褥单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树上看了片刻,说:“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说着,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门的单薄的身影。鼻子有些发酸。
我的家在长春东边,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长春北边,相距一百里——父亲是从百里外的家赶来。又赶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党委宣传委员。
我更紧地握着自己从不曾握过的父亲的手。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双手再不会为我做什么了。
是的,父亲是个不善于用话语表达自己正面感情尤其是对子女感情的人,这双手也就给了我更多的回忆。
时间迅速向后推移,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岛生活了两年。两人的身体都还好,我就在市区较为热闹的地段租了房子给他们单住,每星期去看望一两次。
客厅有个不很长的长沙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一头看电视、看报。我去的时候也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坐在另一头,有时坐在稍离开他的中间位置。一次无意之间。我发现原本父亲靠着的靠垫正一点儿一点儿往我这头移动。细看,原来他用一只手悄悄推着靠垫。我佯装未见,任凭靠垫移到我的身旁。显然,父亲是让我靠这靠垫。但他没有说,也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慢慢移动,生怕我察觉……
如今,父亲的手永远地去了,去了三四个月了。化为青烟,化为灰烬,留在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的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经飘雪了,风越来越冷。
世界上还会有一双男性的手为我从塑料提包里一个一个摸出煮鸡蛋、一点儿一点儿往我身旁推靠垫吗?
(選自《朗读者II·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有改动)
【导读】
本文文字质朴。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传达出深沉的父子之情,读来催人泪下。请你概括文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