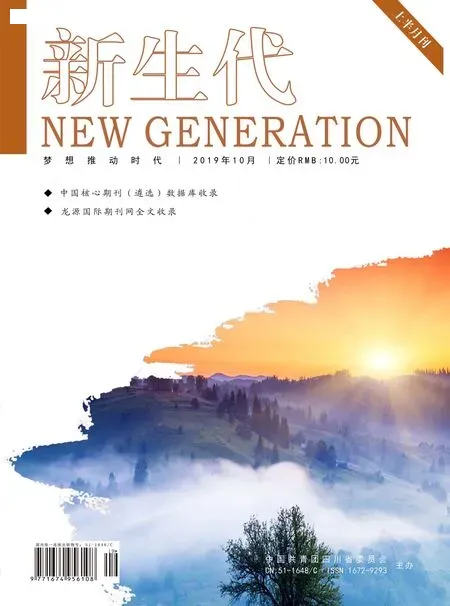牟宗三眼中的中西文化
程一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一.中国文化生命的特征——“仁显而智不彰”
牟宗三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最古老的文化模型中已有体现,《尚书·大禹谟》中讲“正德、利用、厚生”,实为道德的理想主义最初之发显。“正德”是内圣,“利用”“厚生”则是外王。从这时起,中国文化即已显出“仁的系统”的端倪,其对自然的探索和对制度的设计,无不以实用为出发点;其对“智的系统”的追求,无不笼罩在“仁的系统”之下。所谓“仁的系统”,具体地看就是伦理制度和学术教化。所谓“智的系统”,就是“本天叙以定伦常”中的“本天叙”。古代史官要了解自然规律,天文历法,这就为“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最古的文化是“仁智合一”的,但了解天文历法的目的,仍是“定伦常”,所以说“仁”是笼罩,是出发点和归宿。顺着这样的路数发展,道德和政治的系统就越来越彰显。及至周公制礼作乐,此系统已经趋于成熟(此既可能是历史实际的发展成熟,也可能是儒家理想中的发展成熟,而托之于周公)。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周文”,精神上即是“道德的理想主义”,实践上就是周代的礼乐制度。牟宗三先生云:
孔子之振此统于不坠,以及其垂统于来世,皆不指往时之陈迹言,乃指此陈迹所显示之‘意义’。陈迹不可为统,意义乃可为统。此“意义”乃孔子就典宪之发展予以批评的反省以得之。
制度可随时代之进步而改变调整,而精神则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并与现实的形式相结合,衍生出具体的制度文明。
至孔子时,周文疲弊,礼坏乐崩,乃有《论语》、《春秋》以垂教后世。《论语》着眼人伦日用,以“亲亲之杀”言仁;《春秋》着眼社会政治,以“尊尊之等”言义。仁义并举,其背后亦不出于道德的理想主义。其后孟子由“仁义”的内在性确立了“性善”的思想,将此精神整个地树立起来。由这样的内在道德性转出的生活是一种精神的生活,必将物质的欲念从精神中剥离掉,获得真正的“主体的自由”。自孟子始,宋明理学家等皆延续了这种理路并加以发展之,程朱的“居敬穷理”,王学的“致良知”,均是此道。所以孟子一路是深度地开拓“道德的理想主义”,直指仁心,直指天理,“当下便是,反身自见”,其代表性的命题就是“人禽之辨”。而另一路则是荀子,广度地发挥儒家学说,强调“知统类”,要继承儒家形具的文明,要“化性起伪”,用外在的、客观的实践教化人。这种客观精神本来很有利于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可惜荀子没有了解仁义的内在性,以“性恶”来与孟子对质,偏离了儒家的根本精神,故为后儒所不取;而荀子一派本身也因为没有内在道德性的自律(即“慎独”),而必然地堕落物化为韩非、李斯等法家的纯外在的精神。因其强调文物制度的“统类”,故其代表命题是“夷夏之辨”。孟子言尽心尽性,荀子言尽伦尽制,进路不同而理实为一:心性必寻求实现自己于伦常礼制之中,而伦常礼制则必赖心性方有其价值意义。虽然两路有分歧,并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但在孔子处其实是合一的,内在精神自不必说,其对外在精神的重视也可以在他对管仲的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中看到。如果这两种精神的形态在后世中复归一途,而不是分道扬镳,那么中国就能成就“仁智双全”的系统,也就能够自己开出近代的科学和民主制度。
经过孔子孟子等往圣先贤的发展,“智的系统”乃被完全融摄在“仁”之下,虽不再以实用为出发点,却越过了“智”的独立发展阶段,直接抵达了“超知性形态”,也就是“智的直觉形态”,牟宗三先生形容这种形态为“圆而神”。这部分牟宗三先生借鉴康德的理论,将“智”分为了三种形态:其最低级的是感性、经验,是囿于生活实用的“智”;其中间形态是“知性形态”,即概念的、抽象的、逻辑的“智”,能使我们认识现象界;最高级的是“直觉形态”,亦称“神智”,使我们能够认识本体界。康德认为神智唯上帝能有,是因为他以上帝为本体;而牟宗三先生认为,因道德才是本体,故中国哲学早已证成了神智可为人所有。对于道德和生命的重视使中国人的“智”一直笼罩在“仁”之下,所以从最低级形态直接转进了最高级形态;而“智的直觉”理解万物并不通过逻辑、数学,所以中国的科学没有能够独立发展起来,也就没有形成近代西方的规模。
二.中西文化生命之区别——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
至此我们说明了中国文化乃是仁的系统,昂扬其间的始终是道德的理想主义,“智”被函摄其中而不曾得到充分发展。牟宗三先生将中国这种充分强调心性的文化形态概括为“综和的尽理之精神”,其“综和”是表示“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尽理”则是统称孟子的“尽心知性”和荀子的“尽伦尽制”。而西方的文化形态,牟宗三先生则冠之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概念。
“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其实有两意。一是就西方的科学而言,西方文明之始的希腊文明首先重视“自然”而非“生命”,而“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需要观解地认识。因此西方人的“理论理性”或说“认识心”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智的知性形态得以与道德毫无关联地独立发展。故西方的逻辑、数学发达,近代科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乃有今日的强大。二是就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而言,超越的“绝对实在”是外在性的,天国与人间是截然对立的,上帝是世人所不能企及的,所以人们只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而不能依此判断世间的善恶,牟宗三先生由此称此教为“离”的,只有超越的客观妥实性而无内在的客观妥实性;儒家的主张则是天国即是人间,依“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一普遍真理可以实现现实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故既有超越的客观妥实性复有内在的客观妥实性,是谓“盈教”。这个“离”与“盈”的差别就体现在耶稣身上,耶稣将人间与天国截然地隔离开,以上帝的真理显示给民众。因为基督教不是心性之学,真理不是内在而是外在的,故决不能人人成为上帝,否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一如太平天国的杨秀清以“天兄附体”来要挟洪秀全。耶稣只能有一个,他是神而不是人,是三位一体的圣子,是“道”化为肉身。由此宗教精神,西方文化中遂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无“亲亲之杀,尊尊之等”之观念,这样一来社会上就会形成阶级、团体的对列格局,或者叫做“理性的架构表现”,遂容易转出民主观念与制度
由此可见“分解”的含义,就是与感性世界的分解。无论是科学中建立抽象的、概念的、偏至的“观念世界”,还是宗教中俗世遥不可及的天国、彼岸,都是与经验的、感性的世界相隔离的。而儒家的仁义道德则和感性世界相贯通,是实现于人伦日用之中的,故名“综和”。而西方之“尽理”则是研究的意思,与“尽心知性”也完全不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虽然要民主有民主,要科学有科学,但其根本问题在于背后无道德的理想主义,必然会一步步趋于自毁。简单说来,没有道德精神的指导,科学被用来发明更大杀伤性的武器、高科技的作案工具或者成为垄断者牟取暴利的手段;民主政治则沦为政客们通过煽动欺骗民众来中饱私囊的工具。这些可悲的情形不胜枚举,这里举例言之,并不是表示这是个别性的问题,其实在是结构性的、整体性的问题,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长此以往西方文明必走向自毁,应验“周期断灭”的魔咒。
牟宗三先生以“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区别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一大创举。他在对这两种精神进行的分疏中,逐步阐明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与民主,也逐步证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融摄西方文化,摄智归仁,用道德精神指导科学的发展与民主的进行,以道德的理想主义填补西方文化缺少内在的客观妥实性的不足,最终形成“圆而神”的文明,拯救西方文化免于自毁。这对于我们在西方文化价值仍然是世界主流的当代,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树立文化自信,正视道德的主体性,并以此统摄、融合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期在未来发展出根于中华、中西融汇的普世价值,都有极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