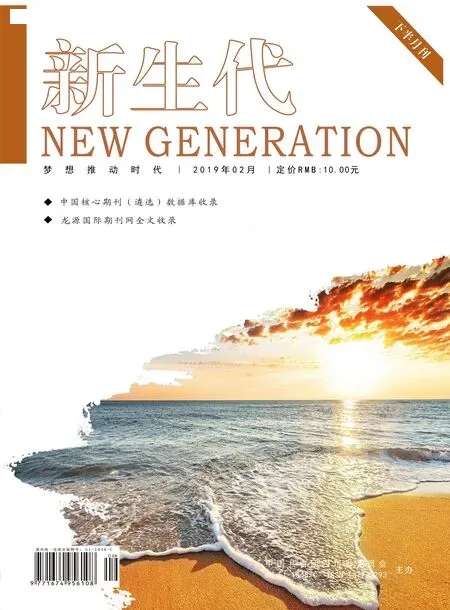选民理性与民主政治的效率
刘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一、民主的失灵
民主是现代政治研究的核心话题。民主自产生以来,它的原始含义是人民主权。其最早在政治领域里的实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但是,这种公民直接投票参与的民主决策方式并没有为雅典带来良性发展,以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多数统治实质上就是或经常会导致多数暴政的民主乱象。多数原则之于民主性和政治性决策是必要的,但其自身的功能也是有限的,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弱点。公民投票这种决策方式往往要采多数原则,而往往也是多数原则的局限性容易引发不良决策,从而造成民主的失灵。
二、理想选民的神话
多数原则之于民主性和政治性决策是必要的,但其自身的功能也是有限的,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弱点。一般而言,公民投票这种决策方式往往要采取多数原则,而往往也是多数原则的局限性容易引发不良决策。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卡普兰通过一个简单的需求模型揭示了人对信仰的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如何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卡普兰在对选民行为模式上的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和对人性的剖析,对“理性的无知”和“聚合的奇迹”进行批驳,得出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未必产生完美政策的结论,并提出“理性的胡闹”正是民主失灵的内在逻辑。虽然他绝不否认个体是具有普遍理性的,但他认为,在政治性决策领域,当每个人由“公民”变为一个“选民”,这种理性只会带来“胡闹”。
有一种“大数定律”理论认为,选民即便在无药可救的无知的情况下,民主依然能够运行良好,因此对选民无知穷追不舍进行反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卡普兰对此理论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奇迹”只能在选民不犯系统性错误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可是选民是会犯这种系统性错误的。所谓“系统性错误”,是指选民在某些观念上具有一致的偏见,导致在决策时出现集体性犯错。这种错误具体表现为四种偏见: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悲观主义偏见。这些偏见甚至成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投票决策与行为,引致系统性错误,从而否定了“聚合的奇迹”关于无知选民犯错的随机性的观点。
如果说对成本的计算是选民做出“理性无知”这一行为根据的话,那么成本的计算+选民自身的偏好则是卡普兰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完整的解释了选民决策失误的根源。通常情况下,如果坚持一种偏好或信仰需要付出巨大的物质成本甚至生命代价时,多数人会放弃这一偏好。但如果坚持这一信仰或偏见无需付出任何成本,或错误观念引致的非理性行为后果并不严重、成本足够小,人们就有理由坚持这种信仰或偏见,而不管其对错。作者把这种同时强调与理性无知的同源性与差异性的方法称作“理性的胡闹”。两者都将认知不充分看作是一种选择,是对激励的反应。差别在于,理性无知假定人们懒得去探究真相,而理性胡闹是在说人们主动去回避真相。选择在受到价格与偏好的双重影响。民主让选民自己做出选择但只给每个人微乎其微的影响力,从个体选民的立场来说结果如何与自己的选择并没有关系,这时选择成本价格为零,个人观念偏好达到最大值,理性胡闹达成,民主失灵。从追求真理的立场看是非理性的观念,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立场看恰好是理性的。
三、民主质量的提升
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提出:选民由于一些人性上的弱点在对公共政策的决策上是无法做到理智投票的,作为民主的一种替代机制,作者认为应当把大部分的决策事务移交市场处理,并且提出了“教育”对提高选民素养的积极作用。
卡普兰认为,选民的理性素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教育,而且经济学家的理性素养要高于普通大众。理性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作为社会人,选民的理性要受到教育、文化、制度、时代、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便经济学家也概莫能外提高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素养是卡普兰提出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之一。只有掌握充分信息、不易受利益集团影响的中间选民比例提高,民主决策的效果才会更优。卡普兰比较同质选民、异质选民、自利选民和无私选民的非理性后果,得到结论:当中间选民持有强烈的系统性偏见时,错误的政策将会盛行;如果中间选民能够清醒地看待问题,民主政治将选择社会的最优政策。提高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
在卡普兰看来对良好的民主的实现是应该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作者认为如果人们可以通过一项经济学知识测试后才能投票或者需要一个大学文凭才能投票的话,民主也许会得到更好地实行,这两项举措都将增加中间选民对经济学的理解从而导致更明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卡普兰反对政府过多干预,支持市场机制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他也认为经济学的国民教育将有助于培育更为成熟理性的选民,既然公共决策机制如此不完善,何不让更多的决策回归市场。因此,他对民主政治的评判,主要是相对市场制度的优越性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