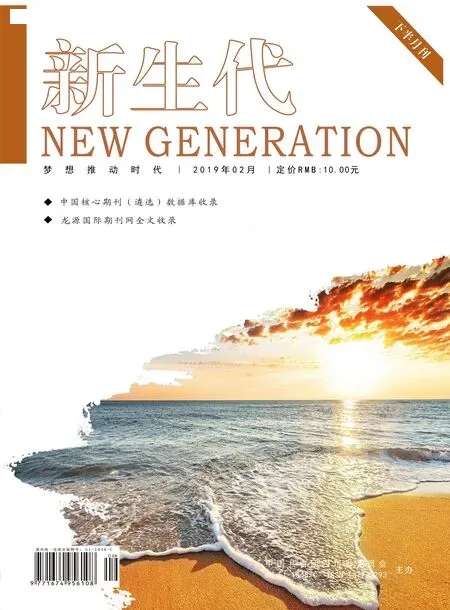儿时杂忆
张凯潞 河南大学 河南开封 475000
我梦到了,我又回到了我的乡村,睡在那布满土味的炕上,嗅到了生的味道。
从小就常听奶奶念叨自己是生在这个家里的,可我总没有太过在意,想着“不生在自己家,还能生在别人家?”终于有一天,我才知道,自己的的确确是出生在家里的,就在自己睡了十几年的炕上的。九十年代末,医院的接生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妈生我的时候,没有去医院,是奶奶亲手接的生。
十岁之前,我生命的记忆全部是在乡村。我是一个在土地的陪伴下长大的孩子。
我的家乡苹果很出名的,村民大多以种苹果为生,我家里也有三亩多的苹果园。那时候的身影,总是穿梭在苹果树下,爷爷奶奶一下地干活,就把我“放生”了。从浓荫树下穿过日光的碎影,尚小的我奔跑在不大苹果园里。有时候我也不乱跑,就待在他们旁边,他们在树上,我在树下。待到日头落西头,我提着篮子,带着他们,回到已经暗了的院子。
到了收苹果的季节,村里到处都飘着苹果的浓香。在外上班、打工的年轻人都会回来,帮着家里一起收苹果。苹果园里全是人们忙碌的身影,从树上摘下的红的苹果,一筐一筐地运往渠漕,然后又一车一车地运往家里。每一家都会专门收拾出一件干净的屋子,来盛放这一年的辛劳。我虽然小,可是也能出力,给他们送水送饭,捡一捡掉在地上的苹果。等到摘完苹果,就要将苹果从地里拉回来,那时候多的是架子车,都是需要人拉的。爷爷和父亲总是双手抓住车把手,将麻绳套到肩上,便低头拉起来,一年的成果全部凝聚在此刻,凝聚在爷爷和父亲的肩上,凝聚在他们的脚步上,凝聚在他们滴下来的汗珠里。等到苹果全部运回家里,看着被苹果映红的屋子,闻着满屋的苹果香,那是所有人最幸福的时候了。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我就被送到了村里的学校。学校不大,几亩地的地方。进了大门,一二三低年级的在南边的院子,四五六高年级在北边的院子。院子很古朴,清一色的土砖瓦房。黄色的泥砖撑起青黑色的瓦片,房檐满是窜出来的干草,墙是刷了白灰的,可是总经不住风雨的摧残,稀稀拉拉挂在墙上。院子里全部用青砖铺成的,都长满了绿毛,平常还好,一到下雨天,可就得留神,一不注意就会滑到。门窗全部是木头的,一打开就吱吱呀呀地响,声音回荡在院子里。进了教室,满眼都是土黄色,土黄色的泥地上摆着一堆土黄色的桌凳,土黄色的桌凳上坐着土黄色的学生;土黄色的泥墙上挂着发黄了的黑板,黑板前面站着土黄色的老师。土黄色的读书声穿梭在土黄色校园里,传遍在土黄色的村庄里。在我们低年级的院子南边有一个侧门,门后有一片光秃秃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操场。操场原本是没有的,学校南边本来是一片苹果园,学校买下来之后,扒走了树,铲平了地,就成了我们的操场。
小时候对于时间是没有概念的,有的只是对于玩儿的片段性的拼凑。如果硬是要说起来,那只能单把夏天揪出来。村里孩子的夏天,是离不开水的。那时的记忆中,多半是和水有关。夏天一到,有水的地方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三五成群地去寻找水的足迹。我们村子旁边有一条大河,从南方的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时候河水充足得很,伴着日光,莹莹的水浪从上游飘荡下来,站在河边,能明显感觉到冰凉的水汽向你扑来,打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如果你会游泳,纵身一跃,不快不慢的水流冲激着肉体,夏日的热气顿时消散,在水里扑腾几下,简直爽上天。即使你不会游泳,慢慢地滑入水中,让冰冷的河水浸湿你的肌肤,清爽的水汽从嘴里、从鼻子里、从耳朵里贯入全身,也爽到了极点。
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到达这里,脱得赤条条的,像一个个活脱的鱼儿在水边跳跃。青涩的身体在日光和水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胆子大的不断往水深的地方试探,胆小的总是靠在岸边,惴惴地望着胆大的在水里自由来回,有时候也想往前去,但是胆怯总把他往后拉。这时候胆大的过来拉一把他,他也就跟着胆大了起来,在水里扑腾几下,就掌握了技巧,便也能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滚动。就这样,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天近黑了,一个个淋着水出来,白光光的站成一排,冲着河水撒尿,比谁尿的远。在晚风中风干了身体,穿上衣服,疲惫地向家走去。疯了一天乏得不得了,躺倒床上,看看屋外月明星稀,听听阵阵虫鸣,闭上了眼,一天就彻底结束了。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转到了市里的小学,这样的生活就少了。再后来,上了中学、大学,回村的机会更少。现在也只有偶尔在梦里,才能回到那些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