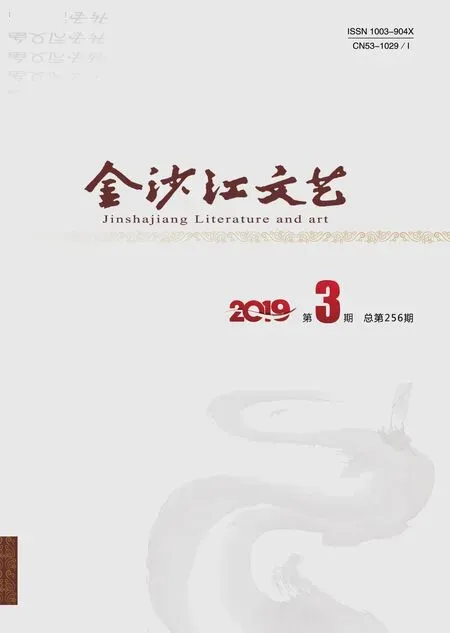仰视与俯瞰:乌东德水电站移民区感怀(七章)
米切若张(彝族)
一、诞生与消失
一座世界排名第七、中国排名第四的千万千瓦级水电站,即将在金沙江下游横空出世——乌东德水电站之举世瞩目,理所当然。
人们的赞叹理所当然:作为令人仰视的 “西电东送” 国家战略骨干电源,乌东德水电站装机容量1020 万千瓦 (相当于半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年均发电量约389.1 亿千瓦时、工程总投资逾1000 多亿元。电站功能以发电为主,兼及防洪、航运、拦沙,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担得起 “利国利民”“惠及千家万户” 这样高调的标语口号!
一座超级水电站的辉煌诞生,伴随的是金沙江南北两岸云南、四川两省94平方公里土地、32 个乡镇69 个行政村的淹没消失、23400 多人的移民搬迁。
文化传承是有基因的。小草恋山,野人怀土,对不得已背井离乡的异地搬迁,民间谚语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文人雅士咬文嚼字,说:“安土重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祖祖辈辈的世居故土,习惯了一方生存环境,迁徙到再好的异地他乡,被迁徙者,无疑也要思量再三,甚至产生撕心裂肺的不舍情结,肯定也是有的。
我的心灵一阵颤抖。为那些即将消逝的村庄,为那些迁徙他乡的移民。
如果一条江,也有前世、今生、未来,金沙江便是。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前,乌蒙山余脉高山峡谷间蜿蜒奔腾的金沙江还没有出世,它的母亲是亘古的汪洋大海——此为前世;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爆发,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猛烈撞击,青藏高原石破天惊蹿高成为世界屋脊,扯瓜连藤,世界屋脊挟持康滇古陆猝不及防伤筋断骨地从海底上升,横断山脉横空出世,云南高原三江并流的世界奇观由此形成,金沙江此其一也——此为今生; 未来也,金沙江下游乌东德水电站大坝2020年截流发电,滔滔江水一旦被截堵倒灌,高峡谷出平湖。金沙江此段的千古村庄,瞬间在库区淹没线以下消失。
回望自然生态史,中华大地两条母亲河,如两条巨龙盘旋南北,奔流千古:黄河在北方咆哮,长江在南方欢笑。两大母亲河两岸,村庄、城镇,龙鳞般生长在母亲河流域。龙的传人依山傍水,繁衍生息。
长江上游,称金沙江。金沙江奔流到四川省宜宾岷江口,出落成浩浩荡荡的长江。“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古代诗人三言两语,道不尽一条大江的前世今生,却文学艺术地表达了中华母亲河的源远流长。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的长江,贯穿中国大地东西两端,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97 千米,天然落差5100 米,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亚马逊河。金沙江水能蕴藏量富集程度居世界之最,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达8891 万千瓦,是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五个国家重点战略的金沙江梯级水电站陆续开工,观音岩、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五座世界级水电站一座一座辉煌诞生。一段一段的高峡出平湖,一组一组的水能发电机组飞速转动,实现从水能到电能的物理转换,“西电东送” 的大国重器,创造了中国大气派、大奇迹。大势所趋,移民搬迁,是水电站建设基础之基础; 搬迁移民,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原住居民搬迁、古老村庄消失、乌东德电站诞生,注定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两岸猿声啼不住,鸡犬相闻互往来的古典生态环境,从此不可逆转地一刀两断。当一江春水不再滔滔东流,当高峡两岸的村庄被平湖淹没,伟大如孔夫子 “逝者如斯乎”的声声感叹,也抵不过 “沉舟侧畔千帆过” 的残酷现实。
二、乘舟采风古道行
此行采风,从金沙江畔的元谋县江边乡龙街渡启程。
江风嗖嗖,热风刮过金沙江两岸的高山与村落。江心酷热,炎热的河谷气流,把江畔两岸的肥沃土地热能,发挥到极致。大自然是最神奇的造物神,在江水泥沙俱下的冲击下,金沙江畔形成一湾又一湾肥田沃土。峡谷深切,高山屏障了这方土地,太阳的光芒热量,日夜储存潜伏在两岸荒山热土,难以被外来冷气流交换。峡谷人家的村庄房里,下半夜刚刚接近的凉气,又被上午的阳光催热。光照长,热量高,田地里的热带庄稼、果木竞相生长,水果、庄稼生长快,成熟也快,甜分更足。肥田沃土庄稼水果簇拥的村庄,土著居民诗意栖居。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封库令下达之前,村民们适彼乐土,安居乐业,早出晚归勤劳耕种,这方山水养活祖祖辈辈的江边生民。童年生长的地方,是人生的天堂。甘蔗、花生、水稻、香蕉、芭蕉、包谷、高粱……海拔高低不同,庄稼们都能找到适宜生长的土地村落。外界一年四季,这里一年似乎只有两季:旱季、雨季。河谷气候的炎热,把寒冷的冬天驱赶到峡谷之外。峡谷热土一年四季热风荡漾,生意盎然,月令季节景色各有风采,从秧苗青青,过度到谷穗金黄;从花生发芽到土下结果,高粱红薯绿肥红瘦,香蕉芭蕉竞相挂果,木瓜甘蔗各领风骚,仿佛世外桃源。民风淳朴,都是些善良人家。哪怕是陌生人,只要到村里息脚,村民肯定酒肉伺候,让你吃饱喝足,还要真心留宿。苦也罢,乐也罢,村民自得其乐,人生山野娱性情。
金沙江南岸的云南乌蒙山区,群山高低阻隔,交通自古艰难,但也不是孤立封闭的桃花源。江水悠悠,古道悠悠,茶马古道、茶盐古道沿江逶迤,往返穿行四川、云南,马蹄声声,融汇于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四川走云南,云南走四川,两个省的船工号子,与马帮的铎铃相映成趣。为生存奔波,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冒险是值得的。一群群纤夫和一群群马帮的身后,故事连着故事,牵连着远方老家的祖父祖母、父母长辈和亲生儿女,牵连着庞大的家庭团队。在险山恶水,航运不通畅的金沙江畔搏命,水上古道,陆上古道,生死或许是眨眼瞬间的事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挑战生存极限的经典表述,只为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费尽移山心力,如愚公移山,一个男子汉,千方百计也要为一家人奠定一个安乐窝。纤夫和脚夫,付出生命赚得血汗钱,是为养活身后家庭的美梦发酵而得来。
金沙江龙街渡码头,乘船顺江而下。江上一叶舟,与江水共同起伏,两岸皆有不同景观,让摄影家、画家的相机镜头兴奋咔咔咔。不久,小三峡的壮观,夺人眼球地展示古老的岁月。江岸古道悠长,挽着岁月的颜色顺江蜿蜒,骡马成群,叮铛叮铛,马蹄声声,人声吆喝,壮观的马帮,来来往往,日夜奔忙,充满着“古道西风瘦马” 的诗意。
古道是人的双脚、马的四蹄走出来的。如此这般悬崖峭壁险象环生,虎豹蛇蝎猖獗当道,气候炎热又多雨的江岸,找个安身立命的喘息之地是必须的。古道蜿蜒,顺江岸排列,以血肉之躯人工开凿,遇山开洞,沿江铺路,落水洞、仙人洞这些天然加以人工修凿的古道景观,就是行走古道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古道上的赶马人、纤夫累了饿了,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天然洞穴,像远古类人猿一样,腰躬爬虾,补充必要的营养,到缓和劳累的饥饿后,又启程出发,赶到另一个神秘莫测的远方。或许,这一去,一条不争气的老命,就死不瞑目的丢弃在异国他乡也未可知。那是古道不断上演的故事,平淡和传奇都随江流远去。一声叹息,古道古人渐行渐远,只剩下古道见证历史沧桑。
如今而后,古道的沧桑也无法见证了。不久之后,仙人洞和茶盐古道,无声无息地藏身江水之下,让游鱼领略人工古迹的相对工整和安全了。鱼群畅游到仙人洞中,或许衔出洞中一对古典爱情男女浪漫爱情结晶的、枯骨上附着的不朽灵魂,说:你看你看,他们相爱得比我们鱼类还深,比我们游荡的江水还深。浪花哈哈大笑,城府很深地消失在风后。
三、古生物天堂和三树成林的哲学隐喻
三树成林,亭亭绿荫,蔚然大观的景象。
金沙江畔 “以进嘎” 傈僳村北面的古道旁,三棵巨大的古树,长成临江的一道生态奇观。
炎热河谷的一道荫凉,是上天赐予江边人家的绝配。
万物生长的奇缘,会聚在金沙江两岸的秘境地带。两亿年前后,独霸一方的恐龙们,群居生命奇特地消亡。一片片恐龙遗体化石,却顺江两岸,排列埋葬。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自然力量,让恐龙集体消亡? 集体死亡的恐龙们,又为何集体面向东方? 这是科学家至今无法解答的万古谜团。科学家们说法不同,热爱恐龙的后生辈,尽可领略不同科学家的归类推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曾经称霸世界的、庞大的恐龙家族,为何成群集队地选择在金沙江两岸悲壮殉葬?
在至今两亿年前左右,金沙江畔数不清的恐龙骨架密集埋葬之后,170 万年前的 “元谋人” 两颗牙齿化石,把元谋科学定位为 “东方人类故乡”。人类准始祖的智猿,进化成东方人类的 “准祖先”,元谋这块土地的神奇,继往开来的远古生物,让精道专家和有识之士感叹不已。
中国诗坛长青树的李瑛,第一次走进元谋,就写下《元谋人》诗句。诗序中,李瑛先生写道:
“1965年,在云南楚雄元谋发现两颗人牙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系距今170万年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定名为 ‘元谋人’,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在此,还发现了距今约四百万和二百一十万年的前‘元谋古猿’ 化石,它们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李瑛先生以他睿智的眼光和深刻的诗思,表达对神奇美丽楚雄的抒怀:
这里是埋藏远祖/脐带的地方/荒原上/渗透着他们的血//云烟紧锁的古代/早已走远,只剩/历史和草根深处的/两颗牙齿/像两颗拂晓的星星/穿透迷雾,静静地/照耀着今天/年轻的世界和年轻的人类/使历史更具有重量和庄严/……无论离他们多远……总听见他们亲昵地又执拗地/召唤,已一百七十万年/我们在风雨中生息繁衍/先是艰难地直立起来/然后用双手创造世界//……过去并没有死去/过去仍活在今天/使我们和浩瀚时空紧紧相连的珠穆一样坚强,一样重的牙齿呵/使我们和苍茫宇宙紧紧相连/黄河波涛一样磅礴、一样恒久的牙齿呵/静静凝视中/我们已变得成熟而深沉。”
《在恐龙故乡》一诗中,李瑛以他深沉的思绪,通过融通古今的诗句,充分表达出来:“第一只恐龙对我说/这里是我的故乡/第一万只恐龙对我说/这里是我的故乡//后羿射下的九团火/已经熄灭/只有它们活着/飞翔于天,爬行于地,或潜游于水//……万古不灭的严酷的法则/一直流到今天的人的泪、汗和血/以及那个开天辟地的盘古/那个翻了翻身又沉沉睡去的盘古。”
杰出的诗人作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者和代言人。当代中国大诗人李瑛,用大气磅礴、思接千古、视通万物的诗句,与楚雄古生物、古人类、古文化深情对话,意象地诠释了走进楚雄彝州,就是走进神奇美丽; 走进彝州楚雄,就是走进深厚的古老文明; 走进史诗和传说; 走进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它所具有的雄浑、质朴、憨厚的品格和神奇、美丽的深刻魅力,始终是引人向往、使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金沙江畔的楚雄彝乡,一不小心,你就会踏上神话般的奇迹一片片。
我惊叹的是,三树成林,活到今天,无言地超越了恐龙和 “元谋人”,无言地活着,不与恐龙和 “元谋人” 争锋,活成自己的一片风景。
金沙江畔的村庄 “以进嘎”,江边三棵树,一棵是榕树,另一棵是榕树,另一棵是攀枝花树。它们仨,都是热带树种,树根深不可测,如恐龙盘旋地下的泥土,生命却昂首苍天。两棵榕树10 多人手拉手围抱的粗壮身材,一点不显得臃肿地青春着,旺盛的树梢,亭亭如巨大华盖,遮蔽了天空、阳光、风雨。两棵得意洋洋的大榕树,或许是得意忘形,或许是浑不留意,欺负一棵与它们百年高龄不相上下的攀枝花树。稍小而无辜的攀枝花树,被挤弯、变形,横生斜长,被压迫到北面的金沙江浪花上,原本直立的身姿,却像画家的构图,横斜江面,为金沙江俯首贴耳。攀枝花不怼,初心淡定,年年初春开花满枝头,映得江花红似火。物竞天择,三棵树相生相克也相亲相爱,鸟去鸟来,风风雨雨,它们仨气息相通,巍然而立。
伫立三棵树下,我特别敬佩那棵相对弱小、横生斜长的攀枝花。它的种籽胚胎是被风吹来的? 被鸟衔来的? 我们不晓得。我们看到并猜想,它的出生,比两棵榕树略晚一些,但肯定小不了几岁。先生后长也是一条命,贵也罢贱也罢,活下去,哪怕被挤压得身躯变形,精神也要保持高昂向上,给点阳光就灿烂,开花、落叶,像榕树一样自自然然,阳光灿烂地过着日月交替,岁月轮转的日子。
问题是,再有两年时光,它们仨,别无选择地将被倒灌的江水淹死。至今埋藏在江畔的恐龙化石,可以抢救性挖掘搬走。像居民搬迁一样,提前采取保护抢救措施,在居民搬迁前后,搬走珍藏。如 “元谋人” 牙齿化石真品,被首都北京珍藏一样,远离家乡故土,却为故乡千古扬名。人挪活之后,也该为故土扬名,我想。
四、丙弄村感怀
春天,枕江的峡谷周围,原野冬眠初醒,两岸的草木,还缓解不了酣眠困倦,遍野的枯黄,只睁开一缝绿色的眼线。
村庄是另一番景象。村民早出晚归,田地里的庄稼被催赶得该开花的开花,该结果的结果。牛羊在野地啃草,鸡鸭在村道刨食,狗的叫声可能是针对一阵热风吹来的汗味……山居田园的恬淡生活,被房顶的炊烟画龙点睛,整个村庄灵动起来。
在一个江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江心漩窝景观之后,一个江湾送走了大江急流,一船人尖叫欢喜着平复刺激后的悬心,船行减速,在一乱石滩上,慢慢停靠稳当。
丙弄村到了。一行人鱼跃登岸。
金沙江两岸,村落隐隐,在一个个江湾急缓间隙之间,肥沃的冲击土地,炎热的气候,让千百年来定居这方的各民族兄弟姊妹,安居乐土。
丙弄村对面的江岸,属四川省会东县。两岸人家,很久很久以后,是可以招招手,大声呼喊交流情感的。即使江涛阻隔,听不见声音,身体语言手势,也可以实现心有灵犀的神交。
丙弄地方,是老祖宗选中的风水宝地。临江的峡谷缓坡地带,土地宽广肥沃,村寨人烟稠密。自古以来,是商旅古道必经的一个大寨子,马帮、纤夫、船工,行走江湖的老大,都要在这方村落吃饱喝足,然后赶路远方,各奔各的目的地。
是故,这方人家淳朴中熏陶了开放,这方姑娘长的靓,这方小伙长得壮,这方的庄稼种得好,这方的菜饭做得好,这方的民歌唱得好。留得住远方来客,留得住心上人,留得住落难人。一句话,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熏染这方土地和人民,这里早已不是桃花源和乌托邦。异乡的文化种籽传递在这里发芽,本土的文化基因辗转在外乡孵化,古道商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熙来攘往,也是人挪活的生活哲学一种。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凝聚几代水电人智慧、心血和汗水,乌东德水电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重点部署下,厚积薄发,成功启动,剪彩奠基。
即将搬迁之际,乡亲们牵肠挂肚,舍不得离开这片村前村后的宽广田野,村后埋葬祖坟山岗,还有村前日夜奔流的大江。带有土地胎记的人,故土永远是人生的另类天堂。丙弄村委会的稠密村庄,搬迁人口多,思想成分多元。但,自给自足的小富即安传统观念,却抵不住迅速崛起的中国那外面世界精彩,比起城镇的繁华富裕,地理环境的边远、交通不便的局限、耪田种庄稼的辛苦劳累和收益微薄,让思想活跃的年青人向往 “好玩,苦得着钱” 的都市,外出打工是政府的大力倡导也是年青人展翅高飞的内生动力,先是亲朋好友相邀作伴出去探水,春节衣锦还乡羡煞了一方村乡; 之后打工人群像雪球越滚越大,翻过乌蒙山、走出金沙江,是年青人的向往,根深蒂固的守护家园观念,在年青人一代开始动摇。
丙弄机会空前,前景也不要十分担忧,村民们只能感叹:不把握机遇,错过搬迁机会,走出金沙江可能沦落为梦想。祖辈居住的环境局限,尽管中老年人思想包袱放不下,青少年的观念,巴不得搬到更好的地方。
多才多艺、能说善唱的女书记,在驻村干部苦口婆心、掏肝掏心的政策宣导下,率领村民服从国家大局,该搬就搬,相信政府的移民政策举措,还有政府体制下的水电集团坚实支撑。
村民们逐渐想通了,移民搬迁的阻力减小了。也有不识时务者的少数钉子户,心想多得些私人利益,怀有这种心理不奇怪。问题是有些贪婪刁钻的人,忘记了祖辈淳朴的初心,连村民都看他不起。
金沙江畔淹没区三棵树,你们还有两年好光景,保重啊。那被迫屈膝,曲生横长的攀枝花,祈祷您像祖先一样开着灿烂的金红色,直到树死花残。三棵树陪葬金沙江,也是另一种荣幸。
五、在黑里村
夕阳降落天幕,日夜不息的江水不知疲倦地欢笑着,奔向前方的长江。黑里村前的江边,不知来自何方、跟随江水奔跑了很久的一大群橙红色石头累了倦了,在江水转弯东去之际,挣扎着爬上江北岸边,安详地躺在了静谧的沙滩,把黑里当做它们永远的老家。这群橙红色的石头们排兵布阵,星落棋布地鲜艳着,宝石般吸引着黑里村傈僳祖先的目光上岸。选中黑里扎根的祖先,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伟大神话人物。连石头都流连忘返的江湾冲击带,青山绿水一块扇形大地,栽棵棒头都能成活的沃土,这个神话般的傈僳祖先决意不再漂泊,决意与这群橙红石头们一起定居下来。黑里,由此诞生。
数百年后。
一群凡夫俗子的采风团队,选择此行最后、也是最精彩的村寨,是仿佛天作之合,走进神话般难逢难遇的黑里。
黑里村一点不黑,白天太阳高照,天空湛蓝得连一丝杂色的白云也无; 夜晚星空灿烂,江边沙滩情人的身影与足印,有雾里看花般美妙。黑里村生态极了,睁眼,清洁得看得见江水里的鱼;闭眼,看得见村庄里的神。
黑里村的男男女女,活得像神仙。我没有看见过神仙,但读过古今中外很多神话故事,走出书本,走进这个神话般的村庄,黑里就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当代神话。此行黑里,于我,可以说是三生有缘。有情众生,一旦邂逅这样的村庄,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感叹再三。
鱼是水里的神,人是岸上的神。岸上与水里的神,各有生存神话。神话,是金沙江畔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构建了真实与虚构的空间,穿越古今,连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长在这方土地的山神,水神,鱼神,土主,统统把黑里村一排排一幢幢壮观的土掌房当做神灵的居所,我也是。
清一色土掌房,是黑里村最明显的胎记。一家一家摩肩接踵的土掌房,依山就势排列方阵,一律两层的夯土建筑,墙体是泥土冲臼脱模,房顶是泥土铺展夯实,取大地本色泥土,创造泥土建筑风骨,牢固的土掌房在风雨浸蚀中屹立百年,改变了自然泥土遇水就软化稀释的特性,智慧家园来自泥土升华。房底是一条条窄窄的村巷相通,房顶是一家家平展的天面相连。房顶天面仿佛大块的铺路石,一家一块连接铺设,比地面巷道更适合走村串寨,是村民的通衢大道; 一家一块的铺路天面,是开放的客厅,更适合赏月纳凉闲话桑麻。房门无锁任意出入,房顶相连走村串寨,朴素的民居美感,被百余家泥土别墅重复又重复,简捷加法递增村落的壮观,最是美术家、摄影家眼中绝美的风采,村民却只认得它是温暖的家。原始朴素的民居,无言地表述远古群居的朴素思维,相互依存的信赖,弥漫着浓浓的家族亲情,彰显着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远古遗风。这样绝美朴素的艺术栖居,黑里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畔第一村。
原先没有想到,我会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乘船到达黑里并且住宿下来。多年文友关系的张炳亮,就出生在这个富有神话传奇的村庄。事先看过他的精彩文章,叙述村居的人生经历与村庄往事,温馨甜蜜又些许忧伤徘徊,如村前橙红的石头,在银白的沙滩迎送江流,不动声色却深情款款,他的追溯,让我们领略了黑里淡定的历史文化积淀,黑里人朴素豁达的高超境界。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张炳亮与其族兄张炳华,就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黑里村杰出子民的代表。
睹物思人。我十分激动的打电话给张炳亮报告说:“到了你们的村庄,老人指给我瞧,那是你家的老房子。村庄有旷古之美,怪不得地灵人杰,好地方来好风光啊!”
不消说,黑里村民的原生态土掌房,凝聚了祖先的智慧,冬暖夏凉的安居,走家串户的坦荡,村民相互依靠,共同发展的村子,肯定是村民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如今,十室九空的现实,更验证了移民搬迁的先兆。明摆着的事实是,即使没有乌东德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搬迁的机遇,交通不便的黑里村,良禽择木而栖的理智选择,一个即将成为空村的历史宿命,已经昭昭然来临了也。既然如此,村庄搬迁势在必行,不搬走不行,有了补偿的村民们,搬迁到其他地方发展,何乐而不为?
我理解年过花甲的老年人的依依不舍。按一个老人的话说:土都埋齐脖子根了还要搬离故土,打死我也不愿走;不走,要被江水淹死,不得不走啊,哪个不想多活两年? 我说:你们搬到更好的地方,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老人茫然,他相信世代居住的土掌房,相信他相依为命大半辈子的一草一木。
不消说,当江水倒灌,黑里村沉沦的时候,原先保存完好的傈僳族土掌房,彻底干净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截流后的水电站淹没库区,在江水淹不倒的土掌房村落中,原先江中的游鱼,穿梭在根基稳固,村民建筑的连排别墅,这方江水鱼类,欢欣畅游,繁殖鱼类的子孙,像村民样繁殖子孙后裔,只是曾经的人窝子村庄,变为鱼窝子天堂。
到那时,水能发电,是鱼子鱼孙眼里的当代神话。
精美的晚餐后,趁着暮色苍茫,相约出发,一行团队,在江边燃起枯树篝火,照亮大江两岸的模糊山峦,以及高低起伏的村寨。江风不甘寂寞,时不时光顾江滩,把江边的野火吹得旺盛彤红,彤红火苗蹿出千万颗红亮星粒,乘风沿江飞散,如夜晚的天女散花,火星的花朵,绽放又熄灭。星火的生命节律是如此迅速,火红的星花瞬间绽放,又瞬间融入亘古的黑暗。这个诗意的夜晚,仿佛让我灵魂出壳,想:一条大江与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也真是天意难测啊。
六、江心岛上捡奇石
黑里村返航,一生在金沙江上行船的老船长,他经历九死一生的故事,像金沙江水一样漫长。老船长被熟悉后的我们称为船老大,极开朗极幽默,他的故事是一部没有问世的长篇小说。此刻,他人性化停船在江心岛屿,说:半小时,赶紧上去淘宝捡石头,运气好,捡得一个好石头,就像抱得美人归。
一群美女登上岛屿,欢喜雀跃去淘宝。一堆堆金沙江宝石,如天穹繁星,大大小小看得人眼花缭乱,难舍难弃。
我心苍凉,步履蹒跚,登上心仪已久的金沙江奇石滩,高处瞭望,原本一条江水,被奇石堆积的江心岛屿一分两条,在江心岛两边迅速流走。无端伤感,为了即将淹死的这个岛屿,我走神了。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我已撕心裂肺,难舍难分这一岛不知多少的金沙江奇石。
再过一年,这个江心岛屿必将被淹死!
从远古活到今天的石头,是大山的精灵。它们都是数十亿年前地质变迁的产物,携带着我们不能破解的远古基因密码。石头们见证过地球生命史的演化,见证过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凶猛撞击和喜马拉雅山的轰然崛起,见识海洋生物生命的大爆发,见识过恐龙的称霸与灭绝,见证过 “元谋人” 的诞生。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沉默不语的远古神话。
年年岁岁,金沙江两岸的丰沛雨水演变为山洪瀑发,在山洪能量的冲击下,山上的含有矿藏成分的巨大石头,翻滚着冲到江里,又被咆哮的江水冲到岸边。自然生态而言,就如树上千万片叶子,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叶子; 世上千万个石头,却难有两个绝对相同的石头。
我怀想:远古时候,山、水、石、人、动物、植物们原本都是在一起生长的共同体。自从人猿揖别的进化历程之后,人们离开天然的石洞。离开石洞,也离不开精美的石头。石头们无所不在,在人类的视野中不离不弃。所以,今天人们赏石、玩石、藏石为主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形成洋洋大观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分支脉流。
“海枯石烂” 是古典爱情的誓言。其实石头们不会乱套,它们没有心计不会自杀,它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地老天荒。大山是它们的老家,即使被峡谷山洪裹胁下山,漂流到江水翻滚的岸边或岛屿搁浅,被外部力量摩擦得失去棱角,却始终本质不变,气节千秋。我想,这或许是真正的石痴石粉,爱石迷石的初心吧。如此想来,像留恋一场古典爱情,我尽情捡拾江心岛上自己中意的石头,坦荡得恨不能搬走所有的爱物,丢三捡四的精挑细选,捡得徒手抱得动的一抱石头,正如船老大所说:抱得美人归。还厚颜无耻地乱想:石头们,你们入了我的家门,总比淹死在江心岛还好。
复登船,回望江心岛上捡之不尽的奇石,心底早已蓄满泪水:江心岛奇石,永别了,我舍不得你们!
七、我看不见自己的泪水
眼眶的咸朦胧成瀑
我看不见自己的泪水
我的泪水
被江鱼看得一清二楚
江鱼为我流泪掀起轩然大波
一圈一圈鱼把伤心浪花吞进江底
电站看不见自己的辉煌
建筑师的汗水泪水
融入日月星辰
安全帽里的汗水泪水可以养鱼
梦想像鱼游翔于万家灯火
移民啊
您看不见自己的泪水
您看得见移民干部的泪水
一腔热忱被你们无数次误解甚至伤害
你们看见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孩
比初生婴儿还不顾赤裸地痛哭流涕
一把泪水甩向大江
大坝看不见她的泪水
一把鼻涕甩向大地
大地心痛的把她消融
千古江水猛然断流
江水看不见自己的泪水
大江歌罢潮回头
挥一挥水袖
大地捧起一座电站
西电东送把万家生活照亮
我看见大江流泪
那是苍天赐予人类的琼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