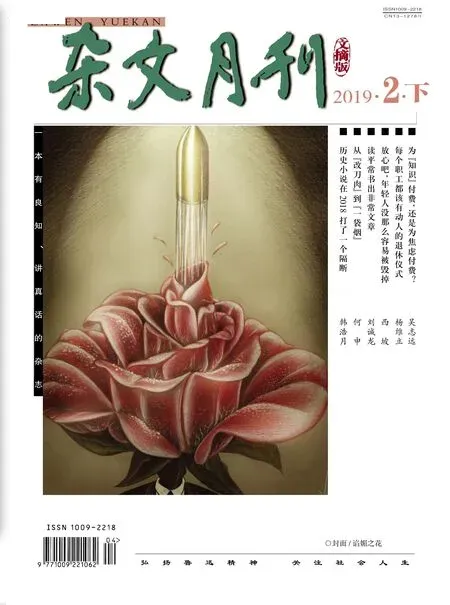人生中那一缕光
□ 李 新
关于我“隔窗偷光”的故事,在母校流传了很多年。
我们那一年先预选10%的人参加高考,意味着90%的同学连高考的门票都拿不到。预选考后,我心里很忐忑,心想这下又输了,彻底输了,前面已经输过两回。我在校园的路上遇到王老师,说:“作文的题目忘记写了。”王老师说:“不要紧。”我这才知道,试卷不是拿到外面批的,命运掌握在自己老师手里。
预选名单公布,我赫然在榜,我的大部分同学则被迫提前毕业了。
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自然非常珍惜这段时间。我是理改文,对于文科的地理、历史,我除了来自初中的那点知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因此,我把几乎所有学习时间都用在了史地上。同学李本红把他白皮的一本地理复习资料送给了我,结果高考有两道大题目出自该书,在全国大多数考生地理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我却考了70 分。沈为宏把他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我,因为他的姑妈在学校做老师,所以使用这间房是他能享受到的特别待遇。他俩预选落选,这样做,等于是合力助推我走向成功。
拥有可以单独使用的房间,有了安心复习的环境,可学校却很快把这房间的电给停了,因为知道我不是沈为宏。教室9 点钟熄灯,我回到黑灯瞎火的房间无法复习。这一个多月里我必须把6 册历史书课后的练习都重做一遍,没了晚上的时间,显然是来不及的。我灵机一动,把桌子移到邻近沈为宏房间的魏老师家厨房的窗户前,就着15 瓦的灯光看书、做习题。一开始,魏老师没有发现他窗户外面有个贫寒学子在用功,10 点钟一到,“啪”地把灯关了。我只好悻悻地回到自己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像阿Q 回到土谷祠,眼巴巴望着空虚的黑暗到天明。后来,魏老师发现了我。老师把灯系在离我书桌较近的窗栏上,等到了晚上11 点钟的时候,过来问:“李新,可以了吗?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这才谢过老师,缩回自己的小屋休息。
我房间的门外有一口井,井边草特别茂盛,齐腰深,蚊子异常兴奋,逮到一个大活人便爱不释口,坐在附近复习,我的双腿常常被咬得麻木,直到像假腿一样失去感觉。老师们都到这里挑水吃,顺便关心我一下,说:“李新,加油,争取今年一定走掉!”中学在乡下,能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都相当不易。
我感激老师们投给我的微弱的那缕光。
这一年,我以超重点大学分数线一个分数段(12 分)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忘不了之前的第二次高考失败后,我自认没有上大学的命,家里祖坟没冒烟,便放弃了。一天,我和母亲在河堤种蒜,当我去河边挑水时,看见有人戴草帽钓鱼,那是王老师。我和母亲央王老师喝水。喝过一碗水后,王老师对母亲说:“这孩子还是让他再复习一年吧,今年只差1 分,不复习可惜了!不过——”王老师转向我,“马老师说过李新适合学文科,不适合学理科。你语文好,可以把历史、地理、政治带动起来。”我还是心里没底,但听老师的话,第二天我又去报到,插在了王老师的班级里。
事实证明,马老师的判断、王老师的提醒都不错。后来我做老师,在指导每一届学生选科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选,不能跟着潮流走。
没有我人生中的光的指引,我是无法走到今天的。
以后我又遇到了很多光,在人生中每一个坎到来时都遇到过,他们给我以温暖和热量,让我充分相信这个世界,也让我始终觉得自己从别人身上获取的多,而给予人的太少。王老师退休不久即患肝癌去世,生前仅托我办一件事——让他的女儿上我当时所在学校的地方中专,可因为户籍问题,我无力办到,心存惭愧。
我想对我的学生好点,再好点。可我能像当年我的乡村老师那样吗?他们的生活是那样清贫,却把身上仅有的光,投射在他们的学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