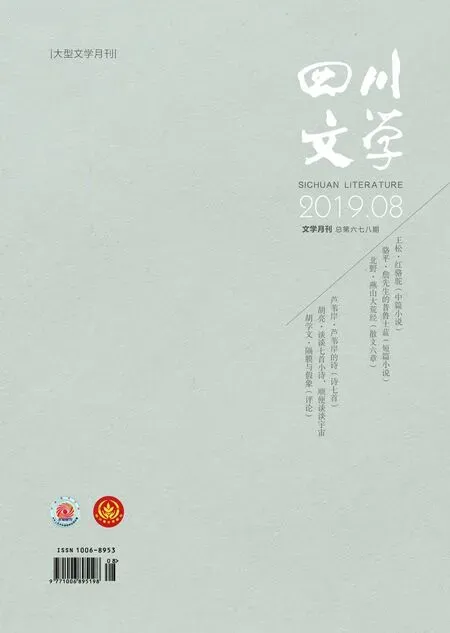别了,我的赵湾
□文/廖清华(教师)
10月20日上午,上完第一节课,我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就听见手机响了,拿起手机一瞧,是父亲廖乾春打来的。近段时间不知是老爷子闲来无事,还是老爷子误认为自己的儿子是这所中学的校长,老爷子一天到晚打电话骚扰我:老家赵湾村三队张三的娃要读高中了,你想办法弄到你的学校来;八队刘五家的娃要分班了,你给他分一个好班;十队张七的娃要填志愿了,你帮他指点一下……他把他自己当成了赵湾村的招办主任,他儿子可没把自己当成是学校的校长。老爷子真把他自己当成一根葱了!
有点怕父亲以及父亲背后的赵湾,心里有些不耐烦,可又不得不接,“老汉儿,又是啥事呀?”电话那边声音有些发颤,“清华,市机床厂将迁到我们赵湾村来。今天,上面来通知,要求我们在月底前把各自的家、祖坟全部搬迁。你星期天还是回来吧,你妈给你点豆花,这将是你在老家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吃完这顿饭,我们就到区上租房子住了。你回家看一看,留个念想。”
愣在当地,竟没有听见第二节课上课的铃声。
坐了几十里的公交车,走了几十里的泥巴路,终于看见自己的家了。
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竹梢上荡来荡去,它们在朝我挥手:廖清华,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大黄狗在屋后的斜坡上,使劲地朝我摇尾巴。小家伙伸出舌头,亲热地舔着我的手,脑袋直往我怀里蹭。摸着大黄狗的头,我不禁有点怜惜这家伙了。明天,到了明天,父亲母亲拿你怎么办呢?城市虽大,恐怕也容不下你这条土狗。明天离开赵湾,它是不知道的。它同往日一样,衔着我的裤脚,拉着我径直往厨房走去。我知道,它是乐意做这个工作的,它知道它的小主人想他的妈了。
柴烟很大,厨房里不时传来母亲的咳嗽声。“妈,你的清华回来了。”我叫了一声,进了厨房。只见母亲在柴灶前正用筲箕扎豆花儿,母亲头也不抬,“你回来得倒是时候,去喊你老汉儿回来吃饭了。”“老汉儿去哪里了?”“他去看你死了三十年的爷爷了。”
父亲坐在爷爷的坟前,闷闷地吸着纸烟。“老汉儿,豆花儿都点好了,妈叫你回家。”父亲呆呆的,也不搭话,嘴里吐出一个个烟圈,烟圈飘上爷爷的坟头,散了开去。父亲用手拍了拍旁边的泥土,示意我坐下。我挨着父亲坐了,问道:“我们将把爷爷搬到哪里去呢?”“都给你胡姨商谈好了,将把你爷爷搬到虾坝村胡姨那里去。”一边是冒着烟的父亲,一边是冒着杂草的“爷爷”,我开始胡言乱语:“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八岁,我都记不清爷爷的模样了。一晃都过去三十年了,挖开坟包,恐怕爷爷的棺材都腐烂掉了,爷爷的骨头都没了,不搬也罢!”“你说啥呢!书是白读了!”父亲把烟头扔进眼前的干田子里,眼睛瞪着我,嗓门特别大,也许他想让他的父亲也能听清,“你爷爷在那边好着呢。他老人家一直都看着我们,否则你能考上大学?”我吐了吐舌头,闭了嘴。
一阵秋风穿过竹林,越过坟头,飘入田里,化成了满目的悲凉。十月,是秋收之后的季节。秋收之后,村民们又做了一次拉网式的清野。庄稼没了,稻草垛没了,桑树、桉树也没了。村民们想把一切进行清理,想把一切搬进城里。可笑的赵湾村民,恨不得早日逃离生他养他的赵湾。赵湾一阵冷笑,它在笑自己的孩子们:头顶这片天脚下这块地你们能够搬走吗?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足迹你们能清理掉吗?你们真的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面对空荡荡的田野,我心里空落落的。我知道,我的赵湾心里在流泪。土里、田间是别样的荒芜。荒芜的还有我干涸的心。我干涸的心在哭泣,它找不到回家的路。赵湾,我的赵湾沉沦了。
沉默良久,父亲叹了口气:“清华,哪天我不在了,你和二娃将把我埋在何地呢?!”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老汉儿,你说啥呢!你身体好着呢!我还要跨上你的肩头骑马马呢!”拍着父亲的肩膀,我的脸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小心。“爷爷走了,有你和叔伯们把他埋掉,这是儿子知道的;若有一天,你和妈妈若离开我们先走了,我和二弟会把你们埋掉,这是儿子知道的;可若有一天,你的儿子走了,谁会把你的儿子埋掉呢?这是儿子不知道的。”抚摸着赵湾的泥土,鼻子酸酸的:“父母不在了,自己不在了,兄弟不在了,我们都不能回到赵湾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越山无黄叶,客子自悲秋”……穿过历史长河,这一天,我终于读懂了先秦宋玉笔下苍凉的秋,读懂了杜甫、晁说之笔下孤独怀人的秋……傍着年迈的父亲,坐在爷爷的坟前,看着踩过千百次的土地,想着明日的别离,真是“天凉好过秋”啊!既然相思、怀远、漂泊、伤逝、失意是秋的近亲,那么秋天就不仅仅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实,它也属于你和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一天,是注定令人难忘了。
“大爸好!我和奶奶等你和爷爷回来吃饭耶。”坝子旁边,侄女廖馨媛正在龙眼树上晃荡。十月,龙眼树仍然枝繁叶茂。树上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红色衣服,欢快地摇动着龙眼。望着红女孩,不知不觉的,我眼镜上布满了泪滴。二十年前,自己亲手栽下了这棵树。二十年,由少年到青年,由青年而中年,皱纹爬上额头,杂草长满内心,世俗的内心又哪有这棵龙眼的位置。二十年,龙眼树默默地成长,自顾自地,在阳光下,在风雨中,在父母沧桑的身影里,它长成了一棵能承载小女孩的参天大树。《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是幸运的,他所栽柳树毕竟活了百年千年。而我可怜的龙眼树呢,明天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下,该流泪的是我!
“廖馨媛,你使劲摇,把龙眼摇死了大爸给你买糖吃。”小孩认为她大爸生气了,伸出舌头朝我做了个鬼脸,极不情愿地滑下了树。
少年不知愁滋味,可这个小女孩连少年也算不上!
干枯的葡萄架下,房檐下的柴堆中,厨房里的灶台前,不见了鸡的踪影,大黄狗失去了它的伙伴。猪圈里空荡荡的,连一点猪屎都没有。这还是我的家吗?我心里发慌,一个迷路的人置身于茫茫的荒野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父亲佝偻着腰,站在石磨前,用手抚摸着磨盘,神情有些沮丧。“廖乾春,你就守着那块石头过日子哈,我们吃饭了,不等你了。”母亲有点不耐烦,“你昏了头了,难不成你要把这副石磨抬进城里?”父亲轻声地嘟囔道:“这个磨子还是我当年亲手打的呢!清华和二娃都喜欢吃它磨的豆花。”
一块滚烫的豆花滚进喉咙,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母亲端起酒杯:“清华,别难过,喝酒!三百年前湖广填四川时,我们钟家不知从哪个旮旯迁到了四川富顺。你们廖家也不知从哪个旮旯迁到了四川富顺。然后,我嫁到赵湾,嫁到你们廖家,从此,给你们父子三人做牛做马。搬走了,妈不伤心。”
母亲不喜喝酒,我也不善喝酒。可每次回赵湾,我们母子二人都要喝两杯。母亲端起酒杯,脸就红红的,话就多起来。我知道,母亲想和她的儿子说话。不胜酒力的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就醉倒在母亲的唠叨声里。
“妈,明天就搬走了,你当真放得下?”我擦了擦泪痕,问我妈。
“有啥放不下的,你妈我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临到大半截入土了,居然要进城当一回居民。”
“你和爸离开了,推土机把赵湾推掉了,我将回到哪里去呢?”
“回哪里?你妈去哪里你就回哪里!你妈不在了,也就管不到你去哪里了”母亲脸色通红,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清华,吃了饭,陪妈到外面走一走。”
黄狗可不管人世间的伤心事,它在桌子下面钻来钻去,享受着主人提供给它的食物。瞧它那个高兴劲儿,它可不知这是“最后的午餐”。
“妈,家里怎么安排大黄狗呢?”摸着大黄狗的头,我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爱意。
“这几天,我们都忙着搬迁的事情,它差点被偷狗人偷走。它见了生人就咬,又不能把它带进城里去。我们准备把它送到你舅舅家去。它年纪大了,恐怕也活不了几年了。”
教我们读书识字的村小是赵湾村的大脑,哺育了村民的蜿蜒曲折的水库是赵湾村的心脏,那起伏于山坡的土地是赵湾村的脊背,冲里的水田是赵湾的胸膛……村小拆了,水库填了,土地推了,我的赵湾也就死了。我陪着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视”赵湾,看着矮胖的母亲,我想:一个乡下妇女,其足迹不超过方圆四十里。她的领地小得可怜,可她把她的力气、青春、喜怒哀乐全部献给了赵湾。她心里能放得下赵湾?
我是放不下赵湾的!放不下她的头她的眼她的腰她的躯干,我想把她的头她的眼她的腰她的躯干折叠好统统放进心里,把她带走,让她伴我一生。三十年前,为了逃离赵湾的贫穷,十一岁的我,背了一个竹背篼,斜挂着一个泛黄的书包,提了一个网袋,里面兜着一个饭盒,弯着腰,踩过一根根田坎,越过一溜溜小土包,到几十里外的中学念书。我逃离赵湾,想忘掉我的赵湾,去寻找新的故乡。
而现在,赵湾静静地站在我眼前,我认认真真地打量着、读着她的每一个细节,心里有无尽的忏悔与遗憾。“宇宙此身元是客,不须怅望家何许。但中秋、时节好溪山,皆吾土。”这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词句,大意是说,人本来就是宇宙的过客,此身只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天地之间而已。既然此身如寄,则天地之间到处是吾乡,何必为望不到家乡而惆怅?还是好好欣赏这美丽的溪山吧。范老先生是乐观旷达的,人只不过是天地间一匆匆过客而已,又何必分故乡与他乡。可是,小气的我不知天地辽阔、宇宙茫茫,只知赵湾是承载我的唯一“星球”。别了,我的赵湾。亲爱的,请告诉我,从此,我的心魂归于何处?
站在田埂上,我和母亲默然无语。父亲站在坝子里,呆呆地望着我们,吧嗒吧嗒地吸着烟。
秋风习习,酒意弥漫在秋日的空气里,化为说不出的乡愁。